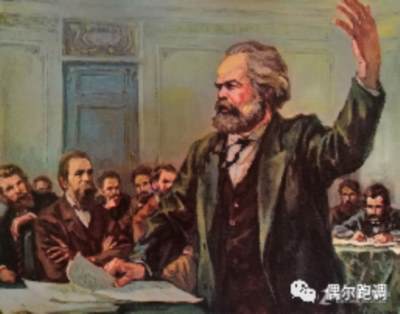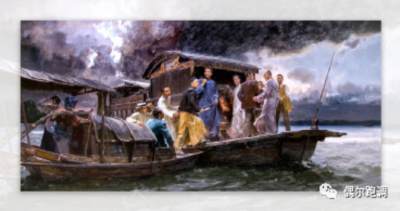今天,一個朋友在看了電視劇《底線》后問我:法院的書記員是整個法院級別最低的崗位,而書記卻是級別最高的崗位,二者只有一字之差,為什么現(xiàn)實中會有如此大的差距呢?
我回答他說,其實書記和書記員,其實本來就是一個意思,字面意思就是負(fù)責(zé)書面記錄的人員,與秘書、文員、辦事員意思差不多,英語中的“secretary”,本身就是秘書,干事,文書的意思。
那么今天,“書記”又是如何變成很多組織的最高級別領(lǐng)導(dǎo)的呢?這就要從兩位導(dǎo)師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年代說起了。
19世紀(jì)中葉的歐洲,盡管資本主義已經(jīng)得到了很大的發(fā)展,有了很多現(xiàn)代化的企業(yè)和工廠,但企業(yè)內(nèi)部的封建等級制依然深入人心,而當(dāng)時負(fù)責(zé)文字工作的書記就是當(dāng)時地位最低的職位。
而共產(chǎn)主義者是講究人人平等的,所以理論上每個人都沒有職高低的區(qū)別。
但是任何組織總需要一個負(fù)責(zé)人,負(fù)責(zé)大家的組織與聯(lián)絡(luò),于是在討論這位負(fù)責(zé)人的職位稱呼時,馬克思建議采用舊時代職位和地位最低的“書記”作為新組織的負(fù)責(zé)人和聯(lián)絡(luò)人,一來表達自己同舊時代徹底割裂的決心,二來也可顯示為民做事、不作官僚的決心。
大家都同意馬克思的意見,于是書記便成為了各國共產(chǎn)主義政黨負(fù)責(zé)人的正式稱號。
1921年,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和浙江嘉興召開,初具雛形的中國共產(chǎn)黨為了表示與舊社會決裂、為人民謀利益的決心,矢志決不當(dāng)官僚、決不做欺壓百姓的“官老爺”,所以選擇最小的“書記”,來稱呼黨的各級領(lǐng)導(dǎo)乃至最高領(lǐng)導(dǎo)。決定繼承馬恩兩位導(dǎo)師的想法,將剛剛成立的中國共產(chǎn)黨的總負(fù)責(zé)人稱為“書記”,陳獨秀也就成為了中國共產(chǎn)黨歷史上的第一位書記。
后來隨著中國共產(chǎn)黨的不斷發(fā)展壯大,各級黨組織都選出了自己的書記,于是中國共產(chǎn)黨的最高負(fù)責(zé)人就被稱為“總書記”了,直到今天。
馬克思選擇“書記”作為名稱的說法并沒有留下官方的正式資料,所以也有人認(rèn)為“書記”這一稱呼是中國共產(chǎn)黨人的自創(chuàng),不過無論哪一種說法是真的,他們所表達的意思都是沒有區(qū)別的,那就是表示與舊社會決裂、為人民謀利益,矢志決不當(dāng)官僚、決不做欺壓百姓的“官老爺”的決心。
所以理論上,書記和普通成員沒有任何區(qū)別,都是組織內(nèi)的最低崗位,只是負(fù)責(zé)成員的組織和聯(lián)絡(luò)工作罷了。
反觀當(dāng)時國民黨的最高領(lǐng)導(dǎo)被稱為“總裁”,中國共產(chǎn)黨“書記”的稱呼無疑更加接近群眾,從此,中國共產(chǎn)黨正式與舊官僚和軍閥有了質(zhì)的區(qū)別。
但是隨著時代的發(fā)展,一切似乎已經(jīng)在悄然間發(fā)生了變化。
前些年,我在出租車和一位黨務(wù)工作者朋友通話,我稱呼他為“X書記”,但他實際只是最基層的黨組織書記,外加私交比較好,所以我和他說話時也非常隨便。于是旁邊的出租車司機對我的說話語氣非常驚訝,因為在他印象中,只要被稱為“書記”的,一定都是個“大官”。
原本在舊時代級別和地位最低的“書記”,成為了今天老百姓心中高高在上的“大官”,不知道這是幸運還是悲哀。
而隨著中國共產(chǎn)黨的發(fā)展壯大,很多黨組織的書記已經(jīng)成為了專職人員,不再有其他的崗位和身份,自然也不需要去做文字記錄的工作。當(dāng)然,隨著中國共產(chǎn)黨的發(fā)展壯大,很多黨組織的書記也不可能有時間和精力親自去做文字記錄的工作了。
但是這些工作還是需要有人來做的,于是法院那些真正做這些工作的人員就被稱為“書記員”了。
于是才有了我朋友的那個疑問,為什么只多了一個“員”字,地位就會有天壤之別。
而在今天,“員”基本是最低級最基礎(chǔ)最辛苦工作的代名詞,政府機關(guān)最低的級別叫“科員級”,技術(shù)職稱中最低的級別叫“技術(shù)員”,企業(yè)中最低的級別一般同樣被稱為“員”,只要崗位以“員”結(jié)尾,那么對方就一定不會高看你一眼,以至于很多企業(yè)把級別最低的崗位也稱為“經(jīng)理”,以至于經(jīng)理成群。
所以書記加個“員”就變成了級別最低的崗位,似乎也可以理解。
但事實上,“員”這個詞的地位,同樣經(jīng)歷了一個變化的過程,而這個變化和“書記”則是完全相反的。
“員”本身就是“成員”“人員”的簡稱,每一位組織內(nèi)的成員都可以被稱為“員”。
比如說司令的全稱就叫“司令員”,政委的全稱就是“政治委員”,就連黨和政府的最高決策機構(gòu)“常委會”成員的全稱也是“常務(wù)委員”。
當(dāng)年,我的一位同事找領(lǐng)導(dǎo)要求提崗,領(lǐng)導(dǎo)回復(fù)說你的崗位“測量員”名字就是員,所以只能定“員”級。
很明顯,這位領(lǐng)導(dǎo)對黨的歷史和規(guī)章制度都不是很熟悉。
這時,我們就不得不再次提到革命導(dǎo)師毛主席了。
當(dāng)年紅軍剛上井岡山的時候,毛主席就提出紅軍的部隊要人人平等,而過去的“官兵”“將士”等稱呼,則明顯將所有人分成了兩個不同的層級。所以部隊上下一律稱“指戰(zhàn)員”,其中就包含指揮員和戰(zhàn)斗員。
不管你是軍長師長團長連排長,干部一律一個標(biāo)準(zhǔn)稱謂一一“指揮員”,而非指揮員者都是戰(zhàn)斗員。但是所有指揮員在特殊的時間,也都是戰(zhàn)斗員,比如在人員傷亡慘重時,大家每個人都是戰(zhàn)斗員。
在“員”之稱謂下,上下平等,聽著親切,沒有尊卑之別,絕無貴賤之分,指揮員戰(zhàn)斗員,都是親密的戰(zhàn)友和同志。
還有其他的如馬夫改為飼養(yǎng)員,伙夫改為炊事員,其他職位根據(jù)需要改稱勤務(wù)員,通信員,司號員,警衛(wèi)員等。
他們和指導(dǎo)員教導(dǎo)員乃至司令員政治委員一樣,等等都是人民的“員”,所以有了廣大指戰(zhàn)員的說法。
如今你翻開毛選四卷,凡對部隊稱謂都是指戰(zhàn)員相稱。毛主席發(fā)布的向全國進軍的命令、打過長江去的作戰(zhàn)命令,開頭第一句話就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全體指戰(zhàn)員同志們,中央軍委命令你們,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聽起來激情澎湃,上下同心。毛主席給志愿軍的作戰(zhàn)命令從來沒有過什么官兵之稱,都是“彭德懷司令員并全體志愿軍指戰(zhàn)員同志們”。
在毛主席的著作中,從來沒有出現(xiàn)過“官兵”“將士”這樣的詞,而是將其統(tǒng)稱為“指戰(zhàn)員”。
雖然這只是一個用詞上的細(xì)微區(qū)別,對我們的日常生活似乎沒有任何影響,但事實上這是一個重要的標(biāo)志:共產(chǎn)黨的隊伍中,人和人之間第一次在“標(biāo)簽”上展示了等級的高低。
人和人之間有了等級上的差別,就不可避免的出現(xiàn)了等級上的互相攀比,就會大大削弱組織的凝聚力和戰(zhàn)斗力。
人和人之前有了等級上的差別,就必然導(dǎo)致上下級之間相互疏遠(yuǎn),最終必將滋生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官僚主義作風(fēng)。
我相信今天很多體制內(nèi)和大企業(yè)的讀者都深受“流程多”“會議多”“報表多”“檢查多”的困擾,這正是官僚主義在我們身邊最直接的展現(xiàn)。
因為官僚主義必將盡力延長自身權(quán)力的展現(xiàn)時間,以為自己謀取更多的利益,所以官僚主義最終一定會異化成形式主義。這這幾多正是形式主義的最直接展現(xiàn)。
所以從毛主席到習(xí)總書記,歷屆黨和國家領(lǐng)導(dǎo)人都把反對官僚主義作為一項重要的工作,從建國初期的“三反運動”到十八大以來的反腐高潮,都是這一系列工作之一。
當(dāng)然,從效果來看,這項工作依然任重道遠(yuǎn)。自1953年,毛主席第一次提出整頓各級機關(guān)的五多問題以來,至今已接近70年,但這些現(xiàn)象卻又愈演愈烈之勢。
這時我想起了去年上映的電視劇《大決戰(zhàn)》,里邊的稱呼已經(jīng)改為了“全體將士”,而在1990年的電影版《大決戰(zhàn)》中,稱呼還是“全體指戰(zhàn)員”。不知道這是編劇和導(dǎo)演的失誤還是有意為之。
這讓我想起了前段時間那篇著名的獲獎文章《我的縣長父親》,當(dāng)獲獎消息第一次登上微博時,引來了無數(shù)網(wǎng)友的謾罵,導(dǎo)致文章被刪除。
事實上,如果我們認(rèn)真讀了文章都會知道這篇文章獲獎是實至名歸,但是很多網(wǎng)友根本就沒有看文章內(nèi)容,而是想當(dāng)然的認(rèn)為沈騰電影《夏洛特?zé)馈返臉蚨纬霈F(xiàn)在了現(xiàn)實中。
借用一句經(jīng)典的話,微博上的這出鬧劇和“書記”“員”社會地位變化的歷程一樣,仿佛是對一個逝去時代的悼詞。
那個屬于理想主義者的時代
「 支持烏有之鄉(xiāng)!」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wǎng)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wǎng)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xiāng)網(wǎng)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