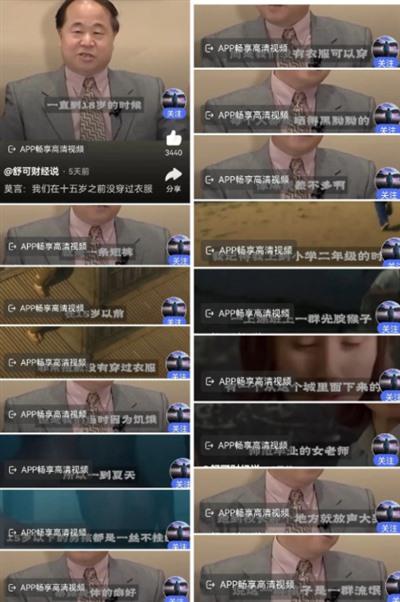最近,很多網(wǎng)友在討論莫言的一段談話視頻。
視頻里莫言講到自己兒時的經(jīng)歷說:
“一直到18歲的時候就是一條短褲……在15歲以前,非常抱歉沒有穿過衣服。當時因為饑餓,一到夏天的男孩都是一絲不掛。不是因為有暴露身體的癖好,而是我們沒有衣服可以穿。每個人都曬得黑黝黝的,像煤炭差不多。”
莫言一直被主流媒體和知識精英塑造為“敢言”的形象,這段話的確令不知情的網(wǎng)友非常吃驚,似乎一下子知道了毛時代的某些“真相”。
為了厘清真正的“真相”,筆者就把之前被莫言投訴刪除的文章,整理重發(fā)一下吧。評論性的內(nèi)容就不講了,免得莫言又投訴筆者污蔑他,本文僅圍繞事實進行敘述。
其實類似上面視頻里的話,莫言在香港公開演講時也說過:
“8歲——窮得光著身子到處跑,狗一樣把任何能吃的東西塞進嘴里,十歲前不知道啥是照相……”
然而,現(xiàn)實中卻存在著一張莫言在1962年春天拍攝的照片:
照片中的小女孩是莫言的堂姐。
從這張照片看,我們很難將照片中穿著并不光鮮卻很得體、胖乎乎的小男孩和小女孩形象,與莫言“15歲以前沒穿過衣服”、“十歲前不知道啥是照相”的話語聯(lián)系在一起。
莫言在他的散文《從照相說起》中,親自講述了童年時拍這張照片的過程和經(jīng)歷:
那時我正讀小學二年級,課間休息時,就聽到有同學喊叫:照相的來了!大家就一窩蜂地竄出教室……這時我堂姐走到照相師傅面前,從口袋里摸出三角錢,說:我要照相……我堂姐昂著神氣的小頭,端端正正地站在照相機前,等待著照相師傅發(fā)號施令。這時,好像是有人從后邊推了一把似的,我一個箭步竄到照相機前,與堂姐站在一起……
可見,這次照相機會是莫言“蹭”到的,不可能是刻意的擺拍,也不是因為知道照相,在上學出門前就“借”到了衣服來拍照。
莫言出生于1955年,拍攝照片時剛剛7歲,正處于被莫言等人反復(fù)控訴的最困難時期,很難想象8-10歲的莫言還能比這時過得更慘。
莫言在散文里簡單交代了堂姐的命運:
她已于十幾年前離開人世,似乎也沒有什么大病,肚子痛,用小車往醫(yī)院推,走到半道上,脖子一歪就老了。照相的事,盡管過去了將近四十年,但當時的情景還歷歷在目。
這篇散文發(fā)表于1999年第5期的《小說界》。按照時間推算,莫言的堂姐死于“十幾年前”的八十年代。她沒有莫言那么幸運——當兵、上大學、進城,死的似乎也比較“冤”:“似乎也沒有什么大病,肚子痛,用小車往醫(yī)院推,走到半道上,脖子一歪就老了。”
(“老”是山東方言“死”的意思,莫言前幾年寫過一篇文章《毛主席老那天》,抒發(fā)自己對毛主席“老”的幸災(zāi)樂禍和嘲諷指責。)
看來,如果當時莫言的老家還有衛(wèi)生站或者下鄉(xiāng)醫(yī)生的話,莫言的堂姐完全可以不死的。
莫言在《<豐乳肥臀>解》中也講過他母親生病的事:
從我記事起,就記得她每年冬春都要犯胃病,沒錢買藥,只有苦挨著,蜂蜜一樣的汗珠排滿她的臉,其實分不清哪是汗哪是淚……因為頻繁的生育和饑餓,我母親那個年齡的女人幾乎都是疾病纏身。我小時候,夜晚行走在大街上,聽到家家戶戶的女人都在痛苦地呻吟……
不過,比較幸運的是,后來莫言母親病危時得到了及時有效的救治:
那次母親生命垂危了,我們只能哭泣,家里沒有錢,有錢也不舍得花在兒媳身上。幸虧來了省里的巡回醫(yī)療隊,很高明的省城的大夫為母親做了手術(shù)。手術(shù)就在母親生我們的炕頭上進行,我們躲在墻根,聽著母親的呻吟,聽著刀剪的聲響,看著護士把一盆盆的血水端出來。
后來又生過一個碗口大的毒瘡,在腰上,一直挺著干活,實在不行了才躺倒,疼痛難忍,咬緊牙關(guān)不呻吟,生怕讓公婆妯娌聽到心煩,瘦得只剩下一把骨頭,我跟姐姐在她身邊哭,她叫著我的乳名,說:我不行了,你們姐弟怎么活呀?幸虧縣里的醫(yī)療隊下來巡診,義務(wù)看病,不要錢。記得是個中午,來了一群醫(yī)生,都穿著白大褂,脖子上掛著聽診器,還拿著刀子剪子什么的,說是給母親動手術(shù),不讓我們進去看。聽到母親在屋里哭叫,肯定是痛得受不了了才哭叫。一會兒工夫,一個醫(yī)生端出來一大盆膿血,一會兒又端出一盆。漸漸地好起來,能扶著墻下地了……
莫言的母親能夠得到救治,先是“省里的巡回醫(yī)療隊”,后來又是“縣里的醫(yī)療隊”,而且是“義務(wù)看病,不要錢”。
描述這段經(jīng)歷時,莫言故意撇開了對宏觀歷史背景的交代,他那篇《<豐乳肥臀>解》主旨也并非講母親被救,而是講時代和封建觀念帶給母親的苦難;但對于研究歷史的人而言,這段歷史不應(yīng)該陌生:
1965年,毛主席接到衛(wèi)生部關(guān)于農(nóng)村醫(yī)療現(xiàn)狀的報告,這個報告顯示:1965年,中國有140多萬名衛(wèi)生技術(shù)人員,高級醫(yī)務(wù)人員8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縣城,只有10%在農(nóng)村,醫(yī)療經(jīng)費的使用農(nóng)村只占25%,城市則占了75%。看過這份報告,毛主席生氣地將衛(wèi)生部稱為“城市老爺衛(wèi)生部”,并在6月26日發(fā)出了應(yīng)當“把醫(yī)療衛(wèi)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nóng)村去”的指示,這就是著名的“6·26”指示。
毛主席的這份指示發(fā)出后,廣大醫(yī)務(wù)工作者熱烈響應(yīng),在組織巡回醫(yī)療隊下鄉(xiāng)巡診的同時,半農(nóng)半醫(yī)衛(wèi)生員的培訓工作也在各地相繼展開。到毛主席逝世,五六百萬人的赤腳醫(yī)生隊伍建立起來了,農(nóng)民不出門就可以看病,而且是通過合作醫(yī)療免費看病!
可以說,正是毛主席救了莫言母親的病;反倒是莫言堂姐在后來赤腳醫(yī)生制度被廢棄以后,遭遇的“意外之死”;而莫言母親的“最后十年”(1984年-1994年),因為農(nóng)村醫(yī)療資源重歸貧乏,還要倚賴已經(jīng)成為大作家的莫言每次“探家”帶她去縣城甚至省城醫(yī)院看病:
在她最后的十年歲月里,我每次探家,幾乎都要陪母親進醫(yī)院,她老人家在死亡線上掙扎了十年。母親的許多病都是在月子里種下的病根。1994年1月29日,我的母親因肺心綜合征去世。
然而,這樣的真實歷史,卻被莫言用“歲月史書”這個道具在他的作品里完全顛倒過來了,以至于他自己可能有時都分不清“虛構(gòu)”與“真實”了,進而在談個人兒時經(jīng)歷時滿嘴跑火車。
孔慶東老師針對這樣的現(xiàn)象有過一段犀利的點評:“文學虛構(gòu)可以改變真實記憶,甚至作家也會迷失真我。”
「 支持烏有之鄉(xiāng)!」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wǎng)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wǎng)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xiāng)網(wǎng)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