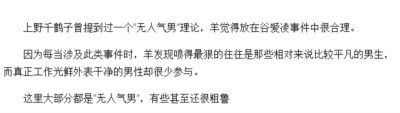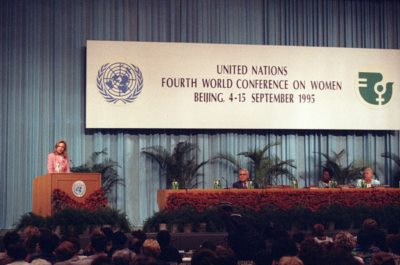2月20日,日本著名“女權主義學者”上野千鶴子與北京大學教授戴錦華舉行了一場對談。由于二位老師都堪稱兩國女性主義問題研究的執牛耳者,組織方在宣發上用的噱頭便是“一份‘女性主義者’的邀請”。
不過這份女性主義者的邀請有些昂貴,要賣99元人民幣,烏鴉便不克參加了。
雖然未能躬逢其盛,但因為上野千鶴子老師最近為推廣自己的新書,在中國非常活躍,烏鴉還是聽到了一些她老人家的言論。
日前,上野千鶴子老師參加了某大熱up主的節目。在這檔節目中,三位中國最頂級高校畢業、身家千萬的女up主,用自己結婚生子的經歷與上野千鶴子做女權方面的探討,過程中完全雞同鴨講,莫名其妙。
比如這三位女性成功人士問上野千鶴子不結婚是不是被男人傷害過?又說自己結婚生子但同時也是女權主義者。但上野千鶴子當年就曾經說過,關于已婚女權主義者,她是不信的,“我無法想象進入一種自愿放棄性自由的契約關系”……
中文互聯網圈的輿論幾乎一致抨擊這三位某大畢業的up主,可以說從破除學歷崇拜的角度來講,這個節目相當成功(手動狗頭)。
還有論者表示,這可真是上野千鶴子受罪的半個小時。看完視頻,烏鴉也無法否認這個觀點。
但烏鴉想說,上野千鶴子老師受罪這件事,是她活該,甚至她本應該在中文輿論圈受更大的罪,她還沒受那種罪,純屬她走運。
1
為什么這么說呢?
讓咱們從上野千鶴子的人生經歷說起吧。
出生于1948年的上野千鶴子在一個富裕的家庭長大,父親曾在偽滿擔任醫生,母親是全職家庭主婦。1967年4月,上野千鶴子考入京都大學。
那個年代的日本正是火紅的斗爭年代,大學生最重要的事就是參與學生運動,上野千鶴子也沒有免俗。
1967年秋天,她就參加了京都大學的抗議運動,那是為同年10月8日在羽田斗爭中犧牲的京都大學學生山崎博昭舉行的悼念游行。
1969年,京都大學全共斗與日本防暴警察浴血奮戰,上野千鶴子與同志們一起頂著鎮壓的恐懼堅守在街壘中。
然而,防暴警察畢竟是專業鎮壓工具,最終京都大學全共斗的街壘被攻破。上野千鶴子感到非常失望,休學一年。
1970年代,日本學生的左翼運動全面退潮,那些曾經激情的學生運動家們迅速適應了歷史進程,轉身投入了大企業,搭上了日本社會高速發展的列車,紛紛當上了體面日子人。
更有甚者直接轉向右翼。信州大學全共斗領袖豬瀨直樹曾是革共同中核派成員,70年代轉向成為保守派學者,后加入小泉純一郎內閣。2012年當選東京都知事。如今,他成為了右派政黨維新會的參議員。
曾參加東大全共斗的鹽崎恭久,畢業后就職于日本銀行,1990年代參加自民黨。2005年擔任小泉內閣外務副大臣,2006年9月26日擔任安倍晉三的內閣官房長官。安倍二次拜相后,他擔任厚生勞動大臣。
再提起當年在全共斗的燃情歲月,變節分子如豬瀨、鹽崎者就只會羞答答地提一句:“那會兒年輕,參加左翼是鬧著玩的,別當真。”
這一代在60年代參加過學生運動的日本人被稱為“團塊世代”或“企業世代”,他們在左翼浪潮消亡后,吃到了經濟發展的時代紅利,成為了各種各樣的既得利益者。
公平地說,上野千鶴子老師倒沒有像這些昔日同志那樣,轉而到右翼的陣營。但整個日本社會都在右轉,她也不可能獨自前進。
上野千鶴子在70、80年代轉入了女性主義研究領域,她以運用文化人類學、符號學、文化表征論等方法,探討當代消費社會下的女權主義而為人所知。
回憶起當年參加全共斗的經歷,上野千鶴子似乎忘記了階級斗爭的存在,總是著重講當時運動圈內部的性別歧視問題。
她表示,盡管大家喊著“解體天皇制”和“破壞家族帝國主義”,但在學生組織內部,男運動家對女生的歧視依舊存在:“白天出門時,是共產主義者,晚上回家后,當大老爺。”
誠然,革命誕生于階級社會當中,本身總會有各種各樣的問題,性別歧視在革命運動中的存在,是舊階級關系的殘留。這個世界上沒有只解放一半勞動人口的階級革命,因為當一半人口還處于壓迫之中,就不能說這是一場解放所有人的運動。換言之,階級革命跟性別平權是同向的事。
但上野千鶴子老師似乎并不認同,在她看來,女性的解放與勞動階級的解放是相互平行的,并沒有什么關聯:“如果連勞動階級都解放了,那么對所有女性的剝削也會終結,這種說法不過是男性的武斷結論而已。”
上野自稱為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者,但重點在“女性主義”,而不是女性“馬克思主義”。在她看來,只有敢于從女性主義的視角侵犯馬克思原著的領域,向馬克思主義發起挑戰,不懼怕對其理論進行修改的人們,才能被稱作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者。
上野因此批判馬克思主義論者對“性別的視而不見”,從女性主義的視角對馬克思主義理論進行了重新解讀。
資本主義當然不會平等地壓迫所有人,女性在階級社會中承擔了更多的剝削是不爭的事實。在上野千鶴子的《父權制與資本制》一書中,闡明近現代父權制與資本制的辯證關系,剖析其對女性雙重壓迫的運作機制,避免了從單一的階級范疇來理解女性問題。
也就是說上野認為,社會主義革命追求的無產階級的解放不過是無產階級“男性”的解放,社會主義婦女解放論因而陷入了困境。
可上野千鶴子沒能說明的是,如何在避免單一階級理論的背景下保證階級批判和性別批判的同一性。
這話可能說著拗口,說白了,上野千鶴子的理論無疑是將女性勞動者的斗爭與全體勞動者的斗爭割裂了開來。
其實,作為一個從革命馬克思主義者退化而成的女性主義者,上野千鶴子老師這種分裂女性斗爭與階級斗爭的理論非常正常。無非是經歷斗爭結束的幻滅,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退潮,自覺階級革命永遠不會到來,那么就在革命的陣線上退卻,試圖以女性主義為基礎構建一條新的陣線。
但這條陣線能守住什么?在這個陣地上呼喊著上野千鶴子的名字,與她一起投入戰斗的又都是些什么人呢?
當性別與階級被割裂,甚至將性別問題擺在階級問題前面,女性權利便自然被成功女性的權利所代言,不過女性成功者的權利與廣大女性勞動者的權利是否一致,可就難說嘍。這也是上野千鶴子從革命的陣線退卻下來時,必然要到達的結局。
這不就是活該嗎?
2
至于烏鴉為什么說上野千鶴子還應該受更大的罪,也得從她的退卻說起。
我們都知道工人運動在上個世紀后期遭遇了兵敗如山倒,在這一過程中退卻者眾,而且他們的退卻不是一步一步退的,而是大踏步地退,甚至是跑步撤退。
上野千鶴子老師也不例外,你以為她只是從革命馬克思主義上退卻了嗎?不,她在其他方面也要退卻。
比如,在反思日本殖民侵略罪行方面,她的退卻也令人吃驚。
1991年12月,曾經的慰安婦受害者金學順老奶奶對日本政府就戰爭賠償提起集體訴訟。
金學順的父母原本住在平壤市,但由于不滿日本統治,他們前往中國定居。金學順也于此時出生。
金學順的生父是民族獨立活動家,在她三個月大的時候就去世了。父親去世后,金學順和母親一起回到了平壤。
1941年,金學順的養父征得金學順生母的同意后準備把她賣到中國去,于是金學順的養父把她帶到了北平。他們抵達北平后在一家飯店吃飯時,一名日本士兵發現金學順的養父是朝鮮人并且懷疑他是間諜,于是將他們逮捕。金學順隨后被投入慰安所,成為了一名慰安婦。
朝鮮半島南北分治后的1946年,金學順和她的家人前往韓國并定居。
戰爭結束后的四十多年里,很少有人聽說過慰安婦。因為許多女性在慰安所中喪生,還有許多女性在戰后自殺,還有一些女性礙于面子,不愿意提及她們的慰安婦經歷。
1991年8月14日,金學順首次對二戰時期的日軍作出指控,她也就此成為第一位公開身份的韓國慰安婦婦女。
金學順的指控掀起了日本社會的慰安婦問題大討論。作為女性主義者權威的上野千鶴子自然加入其中,成為了反思過去的聲音。在這種氣氛下,日本政府在1993年發表了河野談話,1995年又發表了村山談話。
但日本現代的歷史進程是退卻的進程,在這樣的大潮下,個人那點兒游泳能力不值一提。隨著蘇東劇變,社會主義陣營受到重挫,日本革新陣營的核心總評系工會與社會黨也隨之解體,日本右翼的大反撲開始了。
“如果戰爭是邪惡的,那我們死在戰場上的祖先,都是死狗嗎?”這種右翼情緒奏效了。
日本革新陣營在右翼的進攻下一敗涂地,無法提出什么像樣的論述進行抗衡,只能隨著社會一起退卻。上野千鶴子老師也是如此。
1995年,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在北京召開,上野老師在會議上提出了一個今天聽來匪夷所思的觀點,她表示擔心慰安婦問題有可能成為日韓國家利益談判的工具,并敦促日韓女性主義者跨越國界。
在受害者未能獲得正義,加害者尚未道歉的情況下, 受害者卻要主動跨越國界?與會的一位韓裔美國人憤怒地回應:“我們的國家被你們國家的士兵入侵了,你不能簡單地要求我們跨越民族國家!”
上野千鶴子在慰安婦問題上的離譜發言不止于此。
90年代,一群被派往韓國進行友好訪問的日本青年正在參加一個儀式,作為活動的一部分,他們聽了慰安婦的故事。講述過程中,一個身材結實的日本青年突然站起來,開始哭泣,并說:“我甚至不知道發生了這樣的事,請原諒我們。”
按理說這是一個有正常情感樸素正義感的人做出的正常行為,但上野千鶴子老師聽說后居然大為不滿,她還說這事“在我心中注入了一種恐懼感”,“國家和自我竟可以如此輕易地等同起來。我們需要找到一個渠道來表達這個年輕人可能受到的真正傷害,而不是去認同國家”。
上野甚至還說:“當一個年輕的日本人突然挑起日本政府的重擔,開始為慰安婦問題哭泣和道歉時,這是一種可怕的民族主義。”
道歉居然是一種可怕的民族主義,看來我們對于民族主義這個詞的理解與上野千鶴子老師不太一樣。況且,日本政府壓根也沒想過承擔什么“重擔”,這您老不恐懼;倒是一個日本青年愿意表達一點歉意讓您“恐懼”了……
上野千鶴子的這種言論終于激怒了曾尊敬她的韓國女權主義者,當上野千鶴子將慰安婦問題說成“這是人的悲劇”時,韓國女權主義者質問:“這是什么人的悲劇?”
不知道是不是受到了韓國女權主義者的刺激,上野千鶴子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愈加魔怔,把反對韓國“反日民族主義”擺在了實現慰安婦正義的前面。
自1992年1月起,韓國挺身隊問題對策協議會(挺隊協)等團體每星期三(水曜日)會在日本駐韓大使館門前舉行示威活動,要求解決日本政府自建交以來未解決的“慰安婦”問題,稱為水曜示威。
挺隊協一直希望在日本大使館門前樹立一座雕像,作為抗議的象征。2011年12月14日,此一構想終于實現,一座銅像永久豎立在大使館對面。
雕像由藝術家金運成和金曙炅夫妻共同制作,是一尊短發、身著赤古里裙(近代韓服)的少女坐在椅子上,緊握雙拳,凝注日本大使館的高130厘米銅像。紀念碑上寫著慰安婦受害者吉元玉奶奶寫的和平碑文字,紀念在此舉行水曜示威1000次的崇高精神和歷史。
結果此事又引來了上野千鶴子的不滿,認為女孩雕像“不能代表慰安婦”“踐踏日本人民的心靈”,還發出了什么此雕像“歧視日本妓女”等奇談怪論,并將原因歸于韓國“反日民族主義”情緒作祟。
終于,上野千鶴子在反思殖民侵略戰爭上的退卻到了夸張的地步。一位韓國親日學者寫了一本名叫《反日種族主義》的書,將韓日關系交惡的責任完全歸于韓國一邊,認為是韓國的反日情緒傷害了日本人的感情。
而且這本書體現了全世界逆民主義者的一貫手法,那就是它的韓文版和日文版存在明顯翻譯差異。
結果這么一篇滿紙屁話的玩意兒,居然得到了上野千鶴子老師的大力推薦與支持……
對此,上野千鶴子的說法是:我無法接受被壓迫民族的民族主義的先天合法性。
這不就相當于說:“既然我們搞不定日本右翼,沒法兒讓他們跨越國家、放下民族主義來反思侵略戰爭,不如你們受害國先跨越國界、放下民族主義來原諒日本吧!如果你們不這么做,就應該反思自己是不是‘狹隘的民族主義’了!”
必須要說明的是,哪怕是我們這些來自受害國家的后輩,也沒有權力代替真正的受害者說出“原諒”的話,我們所能做的只有銘記這段歷史。何況上野千鶴子您是一位來自加害國家的大儒,您有什么權力說出“原諒”這種話?
更深一層思考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上野千鶴子的思想進入中國、韓國之后,被女權主義者奉為圭臬,啟蒙了無數新時代的女權主義者,讓上野千鶴子實質上代言了東亞女權。
但這種代言本身就是日本通過殖民侵略獲得的亞洲文化中心權力的泛化,是一種核心到邊緣的意識形態擴張。
當韓國女權主義者被上野退卻性的言論激怒,反對上野千鶴子時,我國的女權主義者卻仍然無條件擁抱她的主張,尊她為“女權教母”,甚至到了言必稱上野的地步,不得不說這是一種悲劇…
在這里,烏鴉要借用韓國女權主義者的一句口號,“打倒上野千鶴子,打倒一切上野千鶴子!”
「 支持烏有之鄉!」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