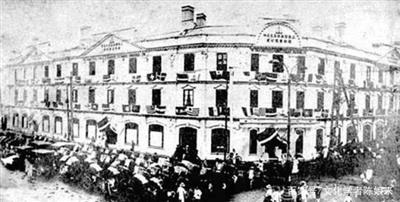01
上個(gè)世紀(jì)九十年代,上海經(jīng)歷了一個(gè)高速發(fā)展的階段,令外灘的“老歐洲”相形見(jiàn)絀的陸家嘴“新美洲”風(fēng)貌,大體上就是在這一時(shí)期形成的。
如今,近三十年過(guò)去,如何解釋上海這一新鍍金時(shí)代的成因?
學(xué)術(shù)界一直有各種各樣的說(shuō)法。
人口紅利說(shuō)、西方產(chǎn)業(yè)轉(zhuǎn)移說(shuō)、經(jīng)營(yíng)城市說(shuō)……,諸如此類(lèi),不一而足。
《繁花》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相關(guān)話(huà)題不斷沖上熱搜,原因就在于,它實(shí)際上對(duì)上海的新鍍金時(shí)代,提出了自己的解釋。
法國(guó)哲學(xué)家福柯有一句高頻名言:重要的不是神話(huà)講述的年代,而是講述神話(huà)的年代。
人們?yōu)槭裁礋嶂杂跔?zhēng)奪歷史的解釋權(quán)?
原因就在于,誰(shuí)掌握了歷史解釋權(quán),誰(shuí)就掌握了對(duì)國(guó)家未來(lái)走向的話(huà)語(yǔ)權(quán),甚至主導(dǎo)權(quán)。
02
在《繁花》中,游本昌飾演的爺叔,是一位至關(guān)重要的人物,他是胡歌飾演的寶總生意上的導(dǎo)師,精神上的教父,也是他的堅(jiān)強(qiáng)后盾。
爺叔非常神秘,就像武俠小說(shuō)里隱身民間的武林大俠一樣,身世不凡。
胡歌在1987年第一次向他求教的時(shí)候,爺叔剛從提籃橋監(jiān)獄出來(lái)。
提籃橋監(jiān)獄在上海赫赫有名,二十世紀(jì)初,由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興建,號(hào)稱(chēng)“遠(yuǎn)東第一監(jiān)獄”。
提籃橋監(jiān)獄建成后,曾經(jīng)關(guān)押過(guò)許多著名的革命者,如章太炎、鄒容,新中國(guó)成立后,又關(guān)押過(guò)許多漢奸,如汪精衛(wèi)妻子陳璧君等。
爺叔是因?yàn)槭裁丛虮魂P(guān)進(jìn)提籃橋監(jiān)獄的?投機(jī)倒把?還是“歷史反革命”?他對(duì)此諱莫如深。
但無(wú)論如何,爺叔和八十年代以前的新中國(guó)歷史格格不入,則是可以肯定的。
八十年代,是一個(gè)大平反,許多案件被“一風(fēng)吹”的年代,爺叔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離開(kāi)了提籃橋,而胡歌的來(lái)訪,令他看到了重溫舊夢(mèng)的可能性。
他首先指點(diǎn)胡歌,在外灘著名的標(biāo)志性建筑“和平飯店”里租一套“長(zhǎng)包房”,如此才能被人看得起,有派頭。
胡歌很驚訝,這樣一個(gè)看起來(lái)相當(dāng)落魄的老頭,何以對(duì)飯店內(nèi)部如此熟悉?
爺叔黯然道,這以前是我的長(zhǎng)包房。
考慮到八十年代以前,爺叔的常住地是提籃橋監(jiān)獄,那么他擁有長(zhǎng)包房的日子,一定是解放前了。
說(shuō)起來(lái),和平飯店也是一處不同凡響,令人浮想聯(lián)翩的所在。
和平飯店的前身,叫“沙遜大廈”,為舊上海首富,英籍猶太人維克多·沙遜所建。
1923年,沙遜來(lái)到上海,靠販賣(mài)鴉片、軍火發(fā)了大財(cái)。二十年代末,他修建了這座高達(dá)77米,號(hào)稱(chēng)“遠(yuǎn)東第一樓”的大廈。
在當(dāng)年的外灘,這座大廈顯得霸氣側(cè)漏,睥睨群雄。其19米高的墨綠色金字塔形銅頂多年來(lái)一直是英國(guó)在上海殖民勢(shì)力的象征,也是上海作為冒險(xiǎn)家樂(lè)園的象征,沙遜自己就住在金字塔下的大套間里。
1934年,國(guó)民政府的“中國(guó)銀行”,為了顯示實(shí)力,決定在旁邊建一座遠(yuǎn)高于沙遜大廈的中國(guó)銀行大樓。
沙遜聞聽(tīng)醋意大發(fā),以大樓靠近英租界,中國(guó)人施工質(zhì)量不行為由,蠻橫要求中國(guó)銀行大樓不得高于沙遜大廈。
在洋人面前從來(lái)直不起腰來(lái)的國(guó)民黨政府,不敢違逆帝國(guó)主義的“游戲規(guī)則”,把官司打到倫敦,還是被迫讓步,將原設(shè)計(jì)的34層大樓砍去一半,比沙遜大廈的金字塔尖頂?shù)土?0公分。
沙遜大廈與一路之隔但矮了一頭的中國(guó)銀行大廈比肩而立,形象地詮釋了什么叫半殖民地。
接著,爺叔又帶著胡歌去做西裝。
按照原汁原味的三十年代“西崽”的形象,把胡歌油頭粉面地打扮起來(lái)之后,爺叔望著胡歌,眼睛居然有些濕潤(rùn)了,他是看到了年輕時(shí)的自己?jiǎn)幔?/strong>
03
前面所做的一切,還不過(guò)是準(zhǔn)備。
準(zhǔn)備妥當(dāng),包裝完畢后,爺叔引領(lǐng)胡歌所做的生意,是股票投機(jī),和蔣介石發(fā)跡之前,在上海灘所做的“搶帽子”生意如出一轍。
什么是搶帽子呢?就是看到價(jià)格要漲,便搶先買(mǎi)進(jìn),然后賣(mài)出;看到價(jià)格要跌,便提前賣(mài)出,然后回補(bǔ)。
這種交易不需要本金,萬(wàn)一看錯(cuò),也不過(guò)蝕去差額,不漲不跌,則要倒賠交易所的手續(xù)費(fèi),所有買(mǎi)賣(mài)必須當(dāng)場(chǎng)了結(jié),不能拖到第二天,這就叫搶帽子。
概括來(lái)說(shuō),就是買(mǎi)空賣(mài)空,投機(jī)取利。
其實(shí),在二十至四十年代的上海灘,還有另外一種傳統(tǒng),即以榮毅仁為代表的民族資本家的實(shí)業(yè)救國(guó)傳統(tǒng)。
《繁花》原著曾獲茅盾文學(xué)獎(jiǎng),但茅盾的名著《子夜》,大概也不入他們的法眼。
《子夜》的主人公吳蓀甫,很想把民族企業(yè)做大做強(qiáng),但在同買(mǎi)辦資產(chǎn)階級(jí)的代表、帝國(guó)主義的掮客趙伯韜的對(duì)壘中破產(chǎn)了。
《繁花》要用三十年代舊上海的精神,解釋九十年代上海的繁榮,不要榮毅仁、吳蓀甫的傳統(tǒng),而精心選擇了投機(jī)交易的傳統(tǒng),實(shí)際上也是“拆白黨”的傳統(tǒng)。
“拆白黨”是上海俚語(yǔ),一開(kāi)始專(zhuān)指那些以色相引誘富婆,白飲白食騙財(cái)騙色的“小白臉”,后來(lái)泛指那些空手套白狼的投機(jī)客。
即便是在舊上海,拆白黨也是被人看不起的。在1948年轟動(dòng)一時(shí)的電影《一江春水向東流》中,張忠良在從重慶出發(fā)去上海“劫收”前,就對(duì)太太王麗珍賭咒發(fā)誓說(shuō),“我現(xiàn)在是個(gè)事業(yè)家,又不是拆白黨。”
爺叔無(wú)疑是一位資深拆白黨,在他的引領(lǐng)下,胡歌——現(xiàn)在應(yīng)該稱(chēng)寶總了——成了新一代拆白黨。
在半殖民地的象征沙遜大廈里,打扮成十里洋場(chǎng)的西崽模樣,在九十年代續(xù)寫(xiě)半殖民地拆白黨的新傳奇——這就是《繁花》。
04
順便說(shuō)一句。
1957年,上海出了一篇很有影響的報(bào)告,獲得過(guò)毛主席的稱(chēng)贊,這份報(bào)告的標(biāo)題為《乘風(fēng)破浪,加速建設(shè)社會(huì)主義新上海》。
“社會(huì)主義新上海”的提法,至今令人神往!
「 支持烏有之鄉(xiāng)!」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wǎng)站日常運(yùn)行與維護(hù)。
幫助我們辦好網(wǎng)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xiāng)網(wǎng)刊微信公眾號(hà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