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2023年10月21日晚,著名作家劉繼明長篇小說《黑與白》線上分享會成功舉行,劉繼明老師現(xiàn)場回答了網(wǎng)友的提問,現(xiàn)發(fā)布于此,以饗讀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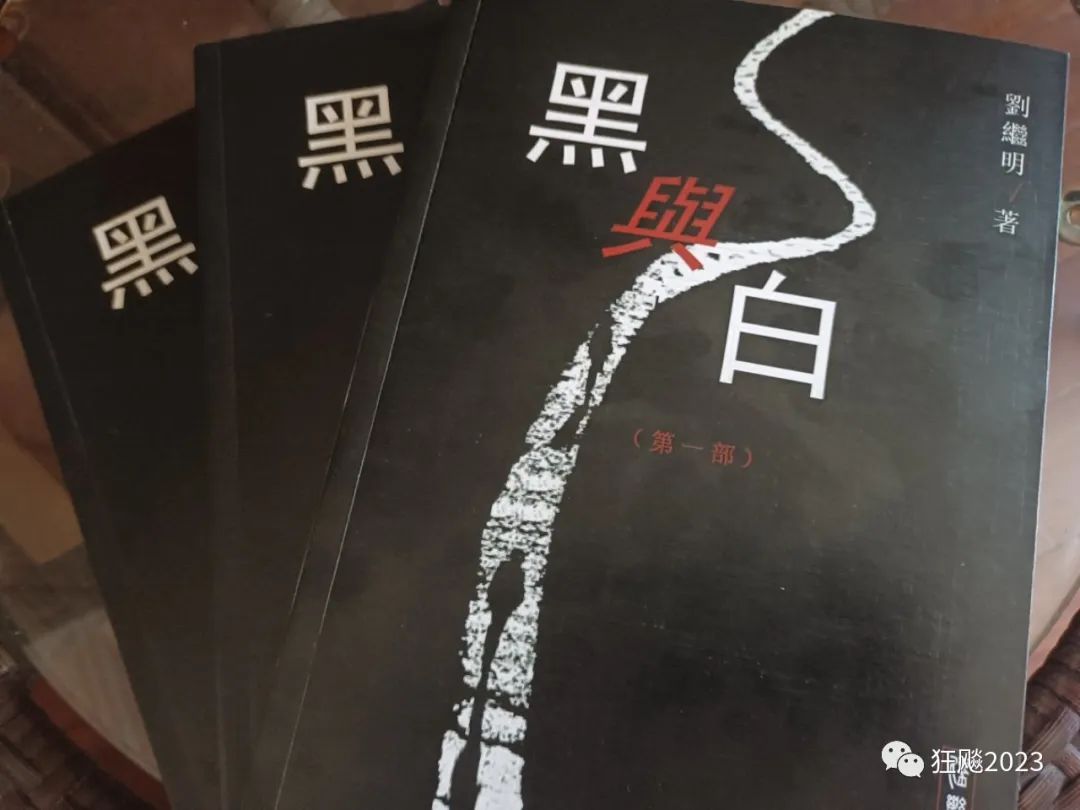
?
網(wǎng)友:劉老師,您作為當(dāng)代中國著名作家,在多年的創(chuàng)作之路上讀過哪些反中國、反社會主義、反文g、反毛澤東時代的作品或者右翼思想的作品?閱讀這些作品,對您的創(chuàng)作有過哪些影響、作用?對于有志于寫作并接受左翼思想的讀者、中國人,如何把握閱讀上述作品,或者干脆就不用讀?謝謝!
劉繼明:我從少年時代起,讀過許多作品,各種各樣的,五花八門,左翼的,右翼的,或者說如你所說的“反中國、反社會主義、反文g、反毛澤東時代”的作品都看過。一個人在成長或成熟過程中,不可能只看一種傾向的作品,就像一個人來到這個世界上,不可能只吃一種糧食,要吃五谷雜糧一樣。至于會從中受到哪些影響,這很難說清楚。因為一個人世界觀的形成,除了閱讀,很大程度上還取決于他所處的地位和階級,正如馬克思說的那樣,人是一切社會關(guān)系的總和,無處不打上社會的烙印。只有當(dāng)你從本階級的立場出發(fā),建立起自己的階級自覺后,才可能對你接觸到的一切書籍包括文學(xué)作品做出情感和審美上的判斷與選擇,才有能力決定讀與不讀,才可能成為一個具有鮮明立場而不是隨波逐流的寫作者。
網(wǎng)友:多年前我閱讀過劉老師的《人境》,內(nèi)心產(chǎn)生過很大的震撼。小說的主人公馬垃作為一名知識分子,在經(jīng)過了一系列社會的閱歷和人生的波折后,選擇了親近土地、回歸土地,具有非常鮮明的理想主義色彩,具有強(qiáng)大和堅定的精神力量。相對于馬垃,《黑與白》中的王晟則在思想上顯得更加猶疑,似乎缺少那種堅定的理想主義。我想請問劉老師的是,您為什么沒有將王晟塑造成類似于馬垃的那種具有鮮明理想主義色彩的人物,這里的主要的考慮是什么,謝謝!
劉繼明:有不少讀者將《黑與白》和《人境》比較。這兩部作品在人物塑造上,在對現(xiàn)實的批判和社會主義的召喚上,的確有某種相似之處。但它們又是兩部很不相同的小說。其中一點就包括你提到的“為什么沒有將王晟塑造成類似與馬垃那樣的具有鮮明理想主義色彩的人物”。這里面的原因很復(fù)雜,主要有兩點,第一點是在《人境》中,馬垃出場時已經(jīng)是一個經(jīng)過生活摔打和內(nèi)心的迷惘、彷徨之后的中年人,對人生有了成熟的見解和追求,而在《黑與白》中,王晟的經(jīng)歷貫穿了他從少年一直到中年的全過程。他性格的變化、世界觀的形成和生活經(jīng)歷,同時代的碰撞,都使他處在一種矛盾的漩渦之中,從而使他的人生觀和思想的形成顯得比較艱難。《人境》也寫了馬垃成長中的內(nèi)心矛盾,但那只是作為一種敘述的背景,比較簡略,在《黑與白》中,則是以一種“現(xiàn)在式”的方式,寫了王晟精神深處的每一步猶豫、彷徨、掙扎和痛苦。第二點,還跟作者寫這兩部作品時的個人環(huán)境和心境有關(guān)。寫《人境》時,我的寫作雖然開始擺脫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控制,但還處于萌芽狀態(tài),對體制以及精英知識界還葆有某種希望,這一點在慕容秋身上體現(xiàn)得比較充分,這也是我為什么花了近一半的篇幅寫這個人物的原因,跟馬垃一樣,我在慕容秋身上投注了一種強(qiáng)烈的理想主義情懷。而到了寫《黑與白》時,我以前比較單純封閉的那種生活狀態(tài)突然被打破了,置身于一種完全打開的狀態(tài),這使我得以同過去很難體會和經(jīng)歷到的錯綜復(fù)雜的人和事“正面相遇”,使我從一位時代生活的“旁觀者”一下子變成了“當(dāng)事人”,用我在一個訪談中的話說,是“觸摸到了時代的底部”。因此,我在寫王晟這個人物時,無法像以前寫馬垃那樣,將他放到“神皇州”那樣一個近似世外桃源的地方,實踐自己的社會主義理想,而是讓他處在各種復(fù)雜的人際關(guān)系乃至危機(jī)中。《人境》問世后,曾經(jīng)有評論家認(rèn)為馬垃太理想化了,以至不像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人。而《黑與白》中的王晟則完全是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產(chǎn)兒”。我曾經(jīng)說過,直到小說結(jié)束,王晟也尚未真正找到自己,成為一個自覺自為的“人民知識分子”。但他已經(jīng)在覺醒的過程中,他和武伯仲杜威的斗爭已經(jīng)證明了這一點。實際上,在我看來,王晟和馬垃是同一個人。在《黑與白》結(jié)尾,王晟走出了服刑三年的勞改農(nóng)場,而在《人境》開始,馬垃也剛剛刑滿釋放,回到闊別多年的家鄉(xiāng)神皇州。這一出一回,正好將馬垃和王晟連接在了一起。從某種意義上說,《黑與白》中的王晟是青年時代的馬垃,《人境》中的馬垃是中年時代的王晟。
網(wǎng)友:老校長是一個樸素的、全家為了新中國付出犧牲的千千萬萬個普通的革命者之一,他最后在鳳凰島烈士陵園守墓的小石屋里伏在一本翻閱批注無數(shù)次的《共產(chǎn)黨宣言》上死去,是小說中對我沖擊最大、印象最深刻的一幕。我甚至認(rèn)為這是改開中國社會的現(xiàn)實寫照,是《黑與白》批判現(xiàn)實主義意義的一個代表人物和典型場景,同時他也是小說中希望的微光——田青青的培育者、言傳身教者,最大影響者,這個人物在各種評述文章中好像被嚴(yán)重低估。我想請劉老師講一講的是,老校長這一形象塑造在《黑與白》最初的構(gòu)思中是怎樣的定位?謝謝。
劉繼明:《黑與白》中寫到的有名有姓的人物近百位,但主要人物不到10位。“老校長”也許算不上是主要人物,但這并不意味著他不重要。在他和駱正、王勝利等人身上,寄托著我對共產(chǎn)主義的信念和對老一輩共產(chǎn)黨人的敬仰之情,我在寫到老校長臨死前讀《共產(chǎn)黨宣言》這個情節(jié)時,眼睛都潮濕了。我很少為自己作品中的人物這樣感動過。我剛才說,田青青、梁天等青年一代使我對未來沒有喪失信心,那么,作為作者,我從老校長和駱正、王勝利這些剛正不阿、正義凜然的老共產(chǎn)黨人身上,同樣獲得了一種對未來的信心。他們是作品中的光和鹽。在《黑與白》中,如果只有王晟、顧箏,而沒有老校長、駱正、王勝利,沒有田青青和梁天這些人物,很可能只是一部普通的成長小說、改革小說、反腐小說或批判現(xiàn)實主義小說。
網(wǎng)友:讀《黑與白》注定不會是輕松的,與麻痹我們神經(jīng)的主流文學(xué)不同,《黑與白》把社會的兩面都寫給讀者看,讓人壓抑的情節(jié)映照著失去地位也失去聲音的底層的現(xiàn)狀,而在這片黑夜中,梁天和田青青在“馬會”的相識如同點點星光給人希望。請問劉老師,觀照今天現(xiàn)實,指引我們青年的星光是什么?我們青年又該做些什么去創(chuàng)造打破黑夜的曙光?
劉繼明:曾經(jīng)有讀者說,《黑與白》描寫的生活過于灰暗、低沉,讓人壓抑,看不到希望。這當(dāng)然跟作品揭露了比較多的社會黑暗有關(guān)。你提到的梁天、田青青等青年一代,的確可以看作是作品中讓人感到希望的“星光”,也是我對未來沒有完全喪失信心的原因。至于你問“指引我們星光的是什么,我們青年又該做些什么去創(chuàng)造打破黑夜的曙光”,我覺得《黑與白》中的田青青、梁天已經(jīng)給今天的青年做出了表率,那就是:到人民中間去,從生活的點滴做起。像《國際歌》唱的那樣,要為真理而斗爭,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會實現(xiàn)!
(來源:曹征路-劉繼明研究中心)
「 支持烏有之鄉(xiāng)!」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wǎng)站日常運(yùn)行與維護(hù)。
幫助我們辦好網(wǎng)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xiāng)網(wǎng)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