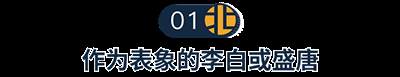應當承認,《長安三萬里》是一部制作精良的動畫片。無論從視效風格、鏡頭設計,還是人物塑造和文化鋪排上,《長安三萬里》都達到了較高的水準。尤其當我們熱衷放大類型電影前的“國產(chǎn)”二字時,它的這些優(yōu)點就變得熠熠生輝。豆瓣開分8.0,雖然有點驚訝,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不難看出,追光在這部動畫片上投入了大量成本和心血,人物動作的調(diào)度華麗,大場面畫面十分精美,動畫制作可以說是又一個國內(nèi)頂級的工業(yè)標準。更難得可貴的是,影片以唐代詩人為主要角色,插入了大量的基本史實和文化細節(jié),以盛唐的氣勢恢宏為刻畫對象,在近三個小時的篇幅里,不遺余力地呈現(xiàn)壯麗繁盛的文化圖景、暗流涌動的歷史變遷,以及人物命運的顛沛起伏。而李白,這個被視為盛唐文化標志的詩人,在片子里呈現(xiàn)出超出課本認知,更為立體、多面的形象。
這樣看來,我們不應懷疑影片制作的初衷和野心。但在這些團隊制作、工業(yè)流程的優(yōu)勢外,卻暴露出更多的罅隙蠹弊和捉襟見肘。
我們繼續(xù)從李白說起。
在《長安三萬里》里,我們能看到一個復雜的李白形象。他生性豪放,喜愛游歷交友,才華橫溢,揮金如土;同時又汲汲于功名,因自己是商人之子,無法科舉考制,便四處投詩,為自己舉薦,寫了大量歌詠權(quán)貴的詩作。他擁有自己的詩歌風格,卻又欣賞全唐的詩歌佳作,倒背如流。他逢人就覺得有才,但聞知黃鶴樓上崔顥的詩篇及其出身,又露出雄競不得的表情。他終身熱衷宦海,但在真正入幕后,卻表現(xiàn)出政治幼稚的弊病(電影中將李白投靠永王璘作如此表現(xiàn))。
這些矛盾的細節(jié)都部分真實地存在于歷史人物李白身上。可以相信,《長安三萬里》對這位中國歷史上最功名卓著的詩人抱有野心。它想還原一個全面、真實的李白形象,又不提供任何負面見解,保留對人物性情、詩才的充分肯定。于是,電影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如何把這些矛盾、復雜的面向整合在一起。
它采取的方法是符號化。
影片找到了一個巧妙的視角講述故事。宦官找到劍南節(jié)度使高適,詢問他與李白的交往。高適在胡人進犯的當口,回憶起自己顛沛流離的生涯。雖然高適是主人公和講述者,但他的生平遭際始終圍繞李白及其周圍的圈子展開,高自己的升遷貶謫變成了背景色。于是,整個盛唐的文化圈,尤其是它的核心李白,通過高適的視角和敘述呈現(xiàn)在銀幕上。
這種處理方法的便捷之處是,編劇無需再想辦法去彌合、縫補李白形象的裂隙和矛盾。高適和李白的相逢被敘述成一場傳奇的遭遇,敘述者意外地撞到了這個與自己迥然不同的人,他的談吐,他的作風,他浮夸華麗、無法理喻、時而可笑、又令人憧憬的形象,成為一種景觀,遭受高適和觀眾的觀看。我們看到了李白的多種面相,就像欣賞幾處名勝風景,至于景區(qū)之間的關聯(lián)是無需理解的。影片沒有告訴我們李白為何呈現(xiàn)出這些不同的面向,高適也不理解。因為這個人無論性格還是出身,都與他太過不同,更重要的是,他們沒有時刻都呆在一起。
于是,我們看到了高適與李白一次次碎片化的相逢,借此也看到李白一場場碎片化的表演。他在樓上喝酒,在船上扔錢給女人,他到了這個地方又到了那個地方,似乎不怎么費勁就得到了許多聲明,和達官貴人呼朋喚友。
有一場戲讓人印象深刻。李白到長安后逐漸發(fā)跡,官任翰林,寫信讓高適來京城找他,幫他謀職。結(jié)果高適跟著杜甫找到酒樓,發(fā)現(xiàn)李白正和幾位朋友一起喝得爛醉,忘卻了自己的許諾。
這是一個讓人無法忘卻的橋段。幾個不同官階的人坐在一張酒桌上,李白依次向高適引薦,大聲念出他們的title。這些中年男性應和點頭,互相吹噓彼此的才華和功名。他們走到空中的木板上,玩對詩游戲,命令樓下的胡姬把舞跳得快些。
這個場景在影片中被刻畫得極其油膩。他們的市儈、庸俗,彼此間惺惺作態(tài)地吹捧,對官本位膜拜,并且物化女性。似乎我們今天司空見慣的酒桌文化,早在一千多年前的開元天寶就已經(jīng)達到了成熟形態(tài)。
這樣的細節(jié)在片中大量出現(xiàn):李白在船上丟錢給歌女;文人們賣弄才華討好玉真公主,乞求一點官爵;以及大量空洞的吹噓,廉價的笑容,斷章取義缺乏語境的詩章。
在這里,影片借由高適的視角試圖掩蓋的裂隙再次被撕裂。一方面是高適視角下感到不適、想要離開的李白及其圈子;另一方面,是作為表象的詩歌和盛唐。二者間存在巨大的鴻溝,我們無法知曉影片的立意是想別出心裁地批判李白等人“隔江猶唱后庭花”,沒有現(xiàn)實報復和政治能力,空求功名;還是想說,高適,這個不姓李的外省男孩,沒落貴族家庭,無法融入京城文化圈,你看長安的文化何其偉大。
這種斷裂的產(chǎn)生不是因為影片想要提供一個立體的李白形象,而是在這個野心的基礎上,片子不敢對那個舊有的李白符號和文化崇拜造成絲毫沖擊。
事實上,李白在長安酒樓放浪形骸有史可稽。走終南捷徑的日子里,李白寫過歌詠唐玄宗的《明堂賦》和《大獵賦》,歌詠玉真公主(一說及其丈夫)的《玉真仙人詞》和《玉真公主別館》。在賀知章和玉真公主的幫助下,他見到唐玄宗,大談自己的理想抱負,卻只得到陪皇帝寫詩作樂的御用文人職位。
李白愁苦于自己的抱負無法實現(xiàn),也礙于京城官場讒言,便破罐破摔,“始縱酒以自穢”。最終被皇帝賜金放還,入了道門。與影片中那場油膩的酒桌戲不同,我們可以想見現(xiàn)實的李白在京城文化圈里的愁苦憤懣,對官僚集團牢騷滿腹。
在這里,我們需要清楚兩點。
第一,這種斷裂并不是要還原歷史真實。且不說一切還原歷史的企圖,都會為其所用語言的當代性破滅,歷史本身也是不可考的,我們永遠無法回到第一歷史,而只存在對歷史的敘述,在這個意義上,所有的史學都是文學,而所有的歷史演繹,都無可避免地加入了創(chuàng)作者當下的情感取向和政治意識。
事實上,《長安三萬里》雖然建立在基本的史實之上,卻并沒有顯示更多還原歷史的企圖。以開篇高適和李白的結(jié)識為例。電影里,李白丟了一批棕色的馬和行囊,卻錯把高適的白馬當成自己的,二人展開一番武藝較量,發(fā)現(xiàn)誤會后,共同打敗敵人。自此,作為才華代表的李白一直鼓勵、提攜高適,后者則表現(xiàn)出才華匱乏、勤能補拙的形象。
但在歷史上,李白是在與杜甫的共同漫游中,遇到了插草賣劍的高適。并且杜甫先于李白,曾與高適見過面,在相國寺前認出了高適。此時李白已經(jīng)獲得顯赫聲明,并且聽過高適作的《燕歌行》。
兩相對比,可以發(fā)現(xiàn),《長安三萬里》更多是基于電影工業(yè)的標準進行改編,制造偶遇巧合,突出李白和高適交往的主要線索,并放大唐代詩人習武的說法,融入大量動作戲。與敘述歷史的野心相比,更多的是工業(yè)流程和票房展望。
第二,這種斷裂也并非浪漫主義。文學史上,我們樂于把李白和杜甫的不同風格作“浪漫主義”和“現(xiàn)實主義”的區(qū)分。但這種命名是西方文論話語流入后,后見追溯的結(jié)果。在恩格斯看來,所謂“浪漫主義”來自對啟蒙思想所許諾的理性社會的失望和諷刺。浪漫派文學不僅僅是只夸張華麗的語言,它們往往具備革命性力量:在法國是法國大革命,在英國是哀婉鄉(xiāng)村破敗,發(fā)出對現(xiàn)代工業(yè)城市的詛咒,在德國則是“狂飆突進”。但《長安三萬里》所表現(xiàn)的,卻罕有革命的痕跡,更多是對“才華”符號本身的頌揚,是作為本體論的盛唐,所謂“浪漫”,更多是對詩人主體及其背后政治體制的頌揚。
于是,《長安三萬里》割裂了“浪漫”與歷史語境,我們看不到這些表象的成因和深度,只是借由高適的眼睛,走馬觀花地瀏覽一番作為表象的圖景。這些去語境化的圖景孤立地聳立在文本中,成為諸多景觀。它們喪失了真實的個性與所指,變得像那些遭到亂用的詩歌一樣,油膩地包裹住整部影片。當我們看到李白投奔高適,對著窗戶背誦《靜夜思》時,有誰不想對這份做作和自戀說一句惡心呢。
與李白及其圈子不同,敘事者高適作為一個異質(zhì)者融入這個故事中。他皮膚較黑,目光呆滯,年輕時口舌笨拙,直言直語,空有一身武藝,腳踏實地,沒有半點奢望。他與李白及其圈子形成鮮明的對比,在酒樓上看到京城文人嬉戲,他轉(zhuǎn)身就走。雖然影片的斷裂沒有說明,但這個轉(zhuǎn)身為我們提出了另一種想象空間,一種迥乎不同的批判尺度。似乎高適意識到他們的油膩,想要踏踏實實地做點實事。然而,高適的故事提供的是什么呢。
在電影開篇,宦官拿著圣旨來到高適營帳,高即表現(xiàn)出高度的忠君愛國熱情。在他的敘述里,他與李白汲汲功名的價值尺度是一致的,不同的在于路徑。盡管一生顛沛流離,屢遭現(xiàn)實打壓,但他始終沒有放棄自己的政治野心。在高適對自己仕途和時局的敘述中,我們可以看出,他與當局的高度一致。
歷史上,“安史之亂”發(fā)生后,高適官拜左拾遺,轉(zhuǎn)監(jiān)察御史。后隨玄宗出逃,馬嵬兵變后,玄宗懷疑兒子李亨是主謀,父子分道揚鑣,高適隨玄宗前往成都,擢諫議大夫。但李亨稱帝后,高適投奔李亨,即唐肅宗。李亨的弟弟李璘心懷不滿,招募重兵,想要效法東晉。在李亨看來這是叛亂,于是任高適為淮南節(jié)度使,討伐永王璘。
事實上李璘并沒有那么壞,至少在李白看來,他的軍隊紀律嚴明,秋毫無犯;李白也把自己投奔永王的行為視為某種愛國主義(《永王東巡歌》)。而在肅宗死后,兒子代宗李豫也為李璘平反(762年)。
但在影片中高適敘述里,玄宗與肅宗的裂隙被懸置了,盡管先后得到過父子二人的提拔,他卻自覺地站在了勝利者肅宗的立場上,把永王璘稱為謀反。而對于肅宗寵幸的李輔國和張皇后,他也再次站在了后繼者代宗的立場上,稱他們?yōu)榧樨瑓s從未涉及對任何一位掌權(quán)者的批評。
在這里,影片刻畫了一個高度體制化的社會——就連太監(jiān)也是要看師門的——并通過高適的講述話語,樹立了唐朝歷史敘述的權(quán)威。他嚴格遵照官方的立場要求,淡化一切歷史的模糊點,將自己的利益歸屬描述為皇帝不可撼動的地位,并把與自己站在不同利益集團的李白塑造成一個政治幼稚的形象。其背后是一套成王敗寇的價值觀,以及對前朝弊病避而不談、牢牢把握自己當下既得利益的實用主義智慧。在這個層面上,老年的高官高適走向了另一種油膩。
在高適和李白之外,我們還看到杜甫、張旭、王昌齡、裴旻、崔宗之等眾多唐朝文化名人。但和那些亂用的詩句一樣,他們的出現(xiàn)基本都是違背史實的,只是作為彩蛋添加在影片中。當一個熟悉的詩句和人名出現(xiàn)時,我們會敏銳地捕捉到那個符號:噢!是這個,我知道!這就是大唐啊!后排的孩子還會樂此不疲地背出詩歌后句。但是僅此而已,他們僅僅是符號。
《長安三萬里》中出現(xiàn)的多數(shù)詩句都是義務教育階段要求背誦的。無論高中選了文科還是理科,無論大學學了什么專業(yè),或因為地區(qū)教育的不平等,文化水平僅僅停留在某個階段,我們都會知道,就像我們都會買電影票一樣。
然而,義務教育階段的老師不僅僅教我們背《靜夜思》,他們還教授了一些價值判斷的標準。無論是否以身作則,沒有人會教孩子去油膩。這正是《長安三萬里》的悖論,也是它的聰明所在。它兜售給我們作為表象的中國文化,以一些耳熟能詳?shù)脑娋洌雌鹑藗兊挠H切感,但同時卻抽空了文化和教育的內(nèi)核,代之以世俗成人世界的耳熟能詳。
《長安三萬里》找到了當下文化產(chǎn)業(yè)的銷售秘訣:符合世俗的平均取向,讓觀眾自滿,不要出現(xiàn)一丁點驚世駭俗的痕跡,不要讓人不適。這或許是一種國產(chǎn)動畫片艱難成長的曲折路線,是文化自信的起步方法。但我們更需要那些艱深、晦澀、具有沖撞力量和顛覆野心的電影。文化和歷史從來不曾是油光水滑的。市場的宗旨是服務顧客,但藝術的目的應該是讓世界變好。
「 支持烏有之鄉(xiāng)!」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wǎng)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wǎng)站,宣傳紅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