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案:1930年代的上海在今天的影視劇總是被塑造成一個“紙醉金迷、靡靡之音”的十里洋場。然而,曾經的上海卻也是“人民電影”的誕生地,中國的左翼電影人在這里創造了中國電影的第一個“黃金時代”,將新誕生不久的中國電影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第25屆上海國際電影節期間,華東師范大學國際漢語文化學院教授,作家、著名影評人毛尖做客觀察者網,暢談了中國電影的“左翼傳統”已經當今影視圈的種種新涌現的現象與潮流。
【采訪/觀察者網 新之】
觀察者網:毛尖老師您好,上海是中國電影第一個“黃金時代”的誕生地,然而促成中國電影達到很高藝術高度的左翼電影的光榮歷史似乎已經不被很多人熟知了。
毛尖:我很高興你提到左翼,中國電影剛起步的時候是“鴛鴦蝴蝶派”,很多題材都是男男女女、神神怪怪的比較多,好像沒有受到什么新文化的影響。而左翼運動進入電影界之后培養了很多演員,這些演員受左翼運動的影響,覺得自己不再是“戲子”了,整體的精神面貌都得到了很大提升,當時中國新生的影視文化圈也開始健康化,變得更加有活力、更加有尊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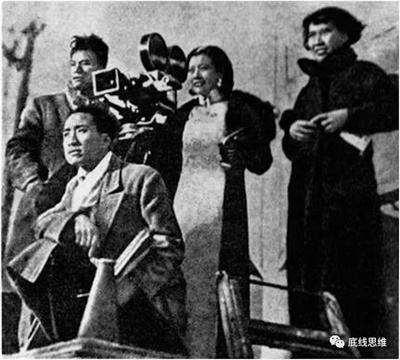
左翼文化給初生不久的中國電影帶來了新氣象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認為現在我們的影視圈應該再有一場“左翼運動”來刷新一下當代影星的精神面貌。別的不說,有時候我恨不得給現在的明星辦一個“寫字班”,幫助他們加固一下九年義務教育的成果——現在影視劇里的男女主的一手字有時候看著確是很鬧心,而劇中人物還要在旁邊夸“你的字真漂亮”。
(點擊圖看原文視頻)
在當時,洪深、歐陽予倩、田漢等等左翼藝術家進入電影創作,他們將社會現實帶到了電影中來,不僅讓電影的藝術得到了提升,而且將中國電影發展成為不僅是藝術的,而且也是政治的,這一點我覺得無論如何強調都是不為過的。程步高的《狂流》,蔡楚生的《漁光曲》,沈西林的《十字街頭》,袁牧之的《馬路天使》,這些電影都有非常強烈的政治感和當代感,而電影院也就成為了普羅接受時代信息的地方。
中國的政治因為電影變成了時尚的話題,包括40年代后期,像史東山的《八千里路云和月》,像蔡楚生鄭君里的《一江春水向東流》,包括《萬家燈火》,《小城之春》,對戰時戰后的社會矛盾文化環境都有生動的刻畫,我覺得在這個意義上,在當時中國人的政治感就是放眼全球都是第一位的,這和左翼電影的傳播關系非常大。

國歌《義勇軍進行曲》出自電影《風云兒女》
不僅如此,進步電影人還為當時的中國電影帶來了世界電影的先進文化,包括好萊塢的制作模式、意大利的新現實主義,當時的中國電影圈在左翼電影人的影響下學習了非常多國外優秀電影的藝術風格,電影界的理論水平也得到了提高,也誕生了《神女》、《新女性》、《麗人行》這樣的具有女性主義意義的電影文本。
我們今天談及中國電影在上海30年代的輝煌時刻的時候,有一點不應該忘記,包括我認為對今天的影視創作也是一個巨大的遺產,那就是當時的電影對于普通人的表達是非常好的。今天我們都在講如何拍好“主旋律”,大家都在往主旋律靠,很多人覺得去拍革命題材才是主旋律,但我認為人民生活就是主旋律,主旋律不僅是大事記,當我們用自己的價值觀來展望未來的時候,我們價值觀如何“落地”,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人民的衣食住行。
觀察者網:您剛才提到的這些老電影似乎和今天我們在影視作品中所描繪的東西相對照,我們能感受到一種很強的“割裂感”。
毛尖:在優秀傳統的傳承上,雖然我們沒有辦法完全斷絕這種關系,但是你提到的割裂感也是沒有辦法的。
比如說我自己在學校里上當代文學課,我讓學生看金庸,我想金庸這么好看,我想學生應該是像當年的讀者那樣不舍晝夜地去看,但是他們其實沒有那么高的熱情了,在他們的眼中好像金庸小說已經是“古典文學”了。
比如說老電影中的“劉三姐”形象,現在的影視劇熱衷于塑造“大女主”形象,但是今天的“大女主”們再也無法復刻劉三姐那種“移山移海”的能力和氣場。

電影《劉三姐》劇照
再比如說新中國之前的電影中上海往往是以“夜上海”的形象出現的,電影總是以夜上海的靡靡之音開場,新中國以后就我們的電影中有白天的上海了,像《大李小李老李》、《今天我休息》,都是以白天的上海開場的,一下子好像上海換了天地的感覺。但你看現在我們又好像回到夜上海的位置上去了,無論是那種音樂的感覺還是服裝、排場,骨子里又回到了那種更“軟”的位置上去了。
觀察者網:您如何看待當下中國影視強調“文化輸出”的潮流?
毛尖:強調輸出一方面當然是好事,說明我們有了國際視野,但是另一方面太在乎這種輸出有時候會變成一種假大空的榮譽感。或者說“輸入輸出”不應該成為電影的一種元認知,否則就會阻擋我們發展的主要路徑。
比如印度電影一直發展得很蓬勃,他們并不擔心輸出,黃金時代的香港電影也不擔心輸出的問題。
我覺得中國電影一方面要兩頭克服:一方面克服“啃洋”,一方面克服“啃老”。啃洋很好理解,我們大量的電影從海外進來難免會對本土工業有所抑制,或者說我們的電影人過于強調模仿外國電影的套路。而啃老則是自己不努力,覺得拿傳統經驗就可以包打天下。當然我們有關部門的一些導向是有問題的,現在我們特別喜歡說“向傳統文化要ABC”,但真正的百家齊放是需要創造新的文化的。
與其過分焦慮輸出,我們其實應該從更大的視野中考慮中國電影的發展結構,未來中國電影的發展方向應該接軌當代文化的新樣態。我們應該借鑒阿根廷或者巴西足球的經驗,一邊要專業化、一邊要業余化,這樣說雖然看上去很矛盾,但實際上就像最近很火熱的村超——國家隊有國家隊的經驗,大街小巷也要有自己的位置。
未來的中國電影要允許有能力的人都加入到電影創作中來,努力去扶植像“村超”那樣的中小企業。而不是過于強調所謂“大視野”,缺少頂層設計同時也沒有基層建設,搞得“爛片”成為了“恒溫層”,院線都被所謂的大片所占據,電視劇時長成為了大戶們的天下,對于流量的過分推崇擠壓了中小公司的生存和見光率……這讓我這個職業的電視劇觀眾往往看劇是“驚”大于“喜”。
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要做好“輸出”,走群眾路線是必須的。只要我們自己做的好,別人自然會來拿,不用我們自己去擔心輸出的問題。《甄嬛傳》和《三體》就是很好的例子。同時我們也不能光盯著美國的認可,輸出同時意味著我們要向第三世界、南方國家輸出,不要好像只有甄嬛講起了英文才算是輸出。
觀察者網:剛才我們聊了中國影視劇“走出去”,同時我們看到近幾年好萊塢也在“看過來”,從之前的《摘金奇緣》《花木蘭》到今年奧斯卡獲獎的《瞬息全宇宙》再到《三體》,中國題材十分火熱,但似乎中國本土的觀眾不是很買賬。
毛尖:這其中很明顯的原因是中國觀眾的整體水平起來了。其實我們中國觀眾的影視閱讀視野是全球最廣的,不信你去美國的錄像店去看一看,他們銷售的片種遠遠不如中國觀眾在網上能看到的全球的片種。現在確實已經不是好萊塢包打天下的時代了,觀眾會用一種相對平視的眼光來看美國的電影電視劇文本。
另一方面,美國這些年在面對中國觀眾時做得確實不夠好。美國電影表現中國形象經歷了非常漫長的演變,從當年非常妖魔化的傅滿洲形象到后來《花木蘭》、《功夫熊貓》《碟中諜》,慢慢面對中國觀眾要票房時,開始為中國市場定制一些情節等等,好萊塢其實在中國的表現上看上去表達出好像更“正常”的中國人形象,但其實他們因為受制于自己非常明確的商業目標,表現上反而有點窄化和單一化了,中國觀眾面對在看了這么多文本以后,當然會對此有不滿意。
就像這次美版《三體》的一些人物造型,中國觀眾會不滿意,覺得葉文潔“不像”等等,因為我們有了自己的《三體》了,美國人拍出來的東西不再作為“最高標準”了,我們在美學上逐漸獲得了新的發言權了,這是完全不一樣的。

美版《三體》中的葉文潔形象
我記得王安憶老師和我們說過一個挺有意思的事情,因為她的書在國外有譯本,她到法國去法國攝影師給她拍照時經常讓她擺一些很奇怪的造型。她后來想這個造型是怎么回事,后來發現其實法國攝影師讓她擺的是當年拍30年代明星的時候那種具有貶義色彩,帶有東方主義概念的造型,后來王安憶說我沒有辦法拍這個姿勢。
總之,當我們自己建立足夠的文化自信的時候,我們就要進入這個場域,把我們自己的美學帶進去。
觀察者網:說到中國自己的審美崛起,最近一段時間,我們的電視劇市場也涌現了一批藝術價值和口碑俱佳的作品,比如《漫長的季節》,這部作品給您印象最深的部分是什么?
毛尖:《漫長的季節》這部劇我覺得可能是不僅今年“封神”,可能未來幾年也都很難超越了。
我自己看《漫長的季節》的時候會特別喜歡工廠改制前的段落,這里面有我自己少年時代尾聲那種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交織的東西,讓我重新回到了那個又浪費時間、同時時間又像黃金一樣的少年時代,仿佛很多過去的東西在我們身上復活,現在的東西又賦予了過去一些新的能量,我覺得好贊。
這部劇最打動我的是那種矛盾性,從主人公王響和兒子王陽對于詩歌的爭論中就可以看出來,導演辛爽對那個年代有著非常濃重的鄉愁,你會感覺到他在情感上很依戀那個時代,但是在美學上又有點俯視那個時代:
比如說在那首統籌全劇的詩歌中,“打個響指吧……”,我們看第一次這首詩歌出來的時候,范偉飾演的王響看到兒子的這首詩,然后他就教訓兒子,他說詩歌要講究合轍押韻,他說打個響指后面就應該是“吹起小喇叭打滴答滴答”。第一次我們看到這里的時候,我們在美學上是站在王陽這邊的,覺得王響很好笑,但看到最后我們因為愛上了王響這個人物,我們就會特別希望如果整個劇是以王響的視角寫一首詩該有多好。我在中文系的創意寫作課上讓全班同學站在王響的視角接著滴答寫下去,學生也都寫了,但是你就會覺得這確實是個現代主義時代了,而不再是一個浪漫主義的時代了。

《漫長的季節》中范偉飾演的主人公王響
所以我覺得整部劇統籌了現實主義、浪漫主義和現代主義,又把這種具有矛盾感和曖昧性的東西留在了文本中。再比如說,從任何意義上說沈默這個人物都是個殺人犯,照理說應該是個很壞的人,但是我們看電影的時候會覺得沈棟梁更壞;說傅衛軍這個人剛出場的時候看上去是個很殘暴的人,但是隨著劇情的發展我們都很喜歡他、很同情他,包括那個港商他死得很慘,即使他罪不至死是個受害者,但是他死的時候沒有人特別去同情他。
最后那場雪飄下來的時候,就好像是一場“法外的雪”,在這里面辛爽重新建立了壞和好的秩序,重新建立了這個時代的一個道德感和美學感。

《漫長的季節》劇照
從這個意義上我覺得辛爽給了當下這個非常庸俗的時代一個耳光。我有的時候真的會覺得這個時代其實蠻無聊的,像成都太古里街拍、大S的床墊這樣的事可以在網上發酵一個星期——我們在這些無聊的事情上浪費了特別多的自己的內心生活。我們的生活留給文藝的空間實在太小了,但是另一方面總有一些事情是要交給文藝的。我覺得辛爽完成的最好的事情是他從法律那里把有些人的審判權握到自己手中,我們對里面的那些罪人重新有一個新的審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覺得辛爽重新為全民為藝術圈拿回了法外之地的說話的權利,這是特別令人振奮的。
觀察者網:漫長的季節給我們另一個很不一樣的地方是,和《鋼的琴》一樣,它強調了共和國工人身上和藝術的緊密聯系,比如說王響這個工人家庭的兩個兒子都有很強的藝術天賦,比如繪畫、音樂、詩歌……而不是刻板印象中和藝術毫不相干的工人形象。
毛尖:是的,這個也是我覺得漫長的季節挺好的一點。我們現在很多人往往在文化上會俯視工人,但其實在在我們自己成長年代,工人的才藝往往是非常突出的,我自己的叔叔是一個工人,他用今天的眼光來看的話,仿佛他肯定是社會底層了,因為他是一個鉗工,但當年他是個8級鉗工,他是擁有非常高的尊嚴的,
而且他彈得一手好琴唱的一首好歌,喝酒的時候旁邊有人會給你倒酒——這是我們當年那個時期工人所擁有的尊嚴感,尤其是文化上的尊嚴感,但現在我們沒有了。我覺得辛爽為我們做的很好的一點,他用藝術的方式又把那個時代工人的尊嚴感召喚回來了。
包括《漫長的季節》里的工廠的那種樣貌,你會發現同樣是工廠的表達,社會主義的工廠和卓別林《摩登時代》里那樣的法西斯工廠有根本上的不同。社會主義的工廠里有王響這樣的工人,這些人有才藝,有主人翁意識,比如王響回去管亂翻垃圾的老太婆,廠里出了什么事要第一時間去做“積極分子”,作為先進工作者要主動參與處理案件……這些工人當年所具有的文化上的優越感是漫長的季節中為我們拿回來的,我覺得這也是特別好的一點。
觀察者網:您在互聯網上有一句流傳很廣的話:“中國最封建的地方在影視劇里”,確實我們在很多網絡文學、影視劇正在重返某種被年輕人想象出來的“秩序”又一次流行起來,比如對于“嫡庶”的推崇,您對此怎么看?
毛尖:說實在的,當年我說這個話的時候把問題都歸在了“封建”上,現在看來所謂的重返封建秩序,其實是重返到套路上去,歸根結底還是創作者的懶惰。我們的影視劇的發明性太弱了,畢竟套路最簡單嘛。
最近又看了一部劇叫做《長月燼明》,里面又是魔神,又是三生三世,又是嫡出庶出,你看,搞“嫡出庶出”馬上就有兩條線了,一個三生三世就是有“三次”了,十集的劇情就變成了三十集了,本質上還是一種套路。
包括女性題材上我們看到那種話題的封閉和無聊,意識形態上的低幼,不說是“令人發指”,至少也是“嘆為觀止”了,比如說現在影視劇為了突出所謂的“女性向”的那種反轉,女人可以在家里打老公,女在外男在內唯唯諾諾,表面上是要取悅女性了,但其實骨子里又是更落后,只不過是用了一個倒轉的位置而已。
觀察者網:不知道您是否注意到近幾年來的一個潮流,相比于層出不窮的新劇,年輕人更愛看“老劇”,不僅反復挖掘細節,而且積極進行短視頻“二創”,您認為這是年輕人對當今新作品平庸的逆反,還是說因為大家都熟悉的劇情更適合短視頻二創呢?
毛尖:你說的兩個原因都很對,我補充一點,老劇對于人物和劇情的塑造是非常非常豐富和去二元化的,老劇寫得很扎實,很好看。更重要的是老劇的尺度要比現在的劇大很多。
很多年輕人對于老劇的二次創作,其實截出的內容恰恰是今天的影視劇里沒有的尺度。比如說《大明宮詞》里對于古代男同性戀的表現,是很美很光明正大的,而不是今天很多耽美劇中羞羞答答打擦邊球的“社會主義兄弟情”。包括當年的海巖劇,都入侵了很多灰色地帶——老劇的價值觀沒有那么單調,人家不拿去做二次元才怪。這樣的創作是對影視劇豐富性的一種填補,表達了觀眾的一種愿望,是一次次很好的翻唱。
當然,短視頻有自己的問題,比如把80集的劇變成8分鐘,導演肯定要吐血了,但是我認為短視頻是這個時代的一種形式,而且年輕人在做短視頻的時候,他們總是能非常敏銳地看到,無論是新拍的爛劇還是過去的好劇中,他們能指認出一些非常鮮活的形象來,比如甄嬛傳里的“賤人就是矯情”的華妃,和完全不一樣的太監形象蘇培盛,這個時代的影視劇沒有提供那么多英雄,他們就從過去的作品中去撈英雄,或者說指認出他們自己的英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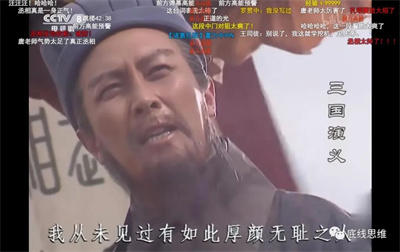
老劇在網絡“二次元”的創作下又煥發了生機
另外一方面就是說短視頻也為最底層的創作提供了像“村超”那樣的舞臺,因為長視頻沒有提供那么多的時代的新的東西,你沒有發明自己,于是短視頻出來了,是一個好現象。短視頻把很多過去時代的文本變成了現在時代的東西,它把過去的東西變成現在時了,尤其是他把過去很多好的文本又變成現代時代的文本了,甚至比如說甄嬛的傳播度會超過現在正在播放的劇,我們看到短視頻活生生的把經典變成我們當代時代的東西了,這是功不可沒的。
「 支持烏有之鄉!」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