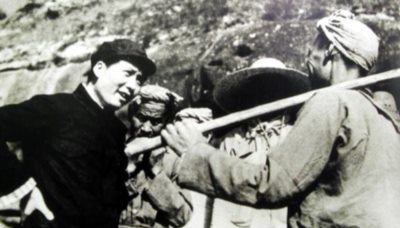按:這些天,郭松民老師一邊閱讀一邊在微博上點評劉慈欣的小說《三體》,盡管筆者對其中的個別看法并不完全認(rèn)同,但總體立場和觀點筆者是基本贊同的。
伴隨著電影版《流浪地球》以及電視劇版《三體》的上映,圍繞劉慈欣小說所展現(xiàn)的世界觀、價值觀的討論,無疑已經(jīng)成了一個現(xiàn)象級的輿論事件。所以,郭松民老師的點評、討論是非常有意義的。
遺憾的是,某些已經(jīng)“魔怔”的“《三體》粉”聽不得不同意見,還反過來給郭松民老師扣上了“魔怔”的帽子。茲將筆者此前文章的一部分整理發(fā)出,供讀者參考。
————————
作家劉慈欣與導(dǎo)演姜文存在著某種相似之處,那就是“情感上的左翼,理性上的右翼”(筆者朋友語)。
一方面,劉慈欣的作品蘊(yùn)含著強(qiáng)烈的英雄主義式的濟(jì)世情懷與悲天憫人,如他的《贍養(yǎng)人類》用近乎直白的隱喻表達(dá)對私有制和資本主義的厭惡,他的《全頻帶阻塞干擾》等作品又隱含著濃烈的反帝及愛國主義色彩;另一方面,劉慈欣的作品又經(jīng)常刻畫群眾“短視愚昧”,而“遠(yuǎn)見卓識”的精英常常不被理解,甚至被多數(shù)人的“B政”票決而死,這在小說《三體》和《流浪地球》原著中,表現(xiàn)得其實都很明顯。
小說《流浪地球》的這種價值取向不僅表現(xiàn)在結(jié)局的“堅持真理的人都死了,暴民卻活了下來”,更在于犧牲2/3的人以延續(xù)人類文明、投票決定誰死的,這種近乎社會達(dá)爾文主義的政策,竟然能被人類一致通過而推行下來。
不過,在電影版的《流浪地球》里我們不僅僅看到了對英雄主義犧牲精神的歌頌,更有對集體主義、群眾偉力(飽和式救援)和愚公精神的歌頌,其價值取向?qū)υ嫘≌f幾乎是掉了個“個兒”。作為前傳的《流浪地球2》明線主旨其實仍在講述“傳承”以及歌頌愚公精神,“抽簽決定50%的人進(jìn)入地下城”的政策被全球其他國家一致通過之后,電影里也有一句臺詞,大意是中國持保留意見,不贊同這種做法。
筆者不知道這樣的價值觀“翻轉(zhuǎn)”,主要是導(dǎo)演郭帆以及編劇龔格爾等人的因素,還是參與監(jiān)制的劉慈欣的“醒悟”。
或許正是電影《流浪地球》的這種好評,讓很多左翼“小清新”對劉慈欣以往所有的作品都抱著強(qiáng)烈的好感,當(dāng)然也包括數(shù)年前已經(jīng)名聲大噪、卻“社會達(dá)爾文氣息”爆棚、右得不能再右的《三體》。
作為一部完全虛構(gòu)的科幻小說,劉慈欣自己數(shù)次講過《三體》是一場思想實驗。既然是實驗,實驗所用的材料、環(huán)境條件都是劉慈欣人為設(shè)定的。小說的世界觀是極其黑暗的,(如很多人所分析的,這可能與劉慈欣創(chuàng)作《三體》時所供職的國企正面臨改制、下崗分流,他以及他周邊的人都處于焦慮、迷茫,競爭留崗過程所表現(xiàn)出的種種叢林法則、人性黑暗有關(guān)吧);小說在情節(jié)設(shè)定上又是極端精英主義的,群眾被設(shè)定成愚昧、自私、貪圖享樂的“群氓”,救世的希望被寄托在少數(shù)忍辱負(fù)重、有遠(yuǎn)見的精英身上……羅輯的故事正是基于這樣的設(shè)定展開的。
在此前“共存”與“清零”的爭論中,“清零派”將自己以及“清零”的執(zhí)行者與羅輯對號入座,而在此之前則是將羅輯與遭受后世之人詆毀的毛主席進(jìn)行對應(yīng)——這樣的強(qiáng)行“雙向奔赴”,顯然是對毛主席和劉慈欣的雙向誤讀。
小說的虛構(gòu)設(shè)定本來就與現(xiàn)實世界無關(guān)。即便要強(qiáng)行對應(yīng),我們不妨把三體人對地球的進(jìn)攻,與已經(jīng)工業(yè)化的日本帝國主義對還處于落后農(nóng)業(yè)國地位的中國的侵略進(jìn)行對比。
《三體》中,“救世”的希望被寄托在作為執(zhí)劍人(引力波威懾控制者)的羅輯一個人身上,所謂群眾其實只需要服從、跟隨就行了。遺憾的是,“不知死活”的群眾還把羅輯視作“B君”。
而現(xiàn)實世界的抗日戰(zhàn)爭中,毛主席及他所領(lǐng)導(dǎo)的革命隊伍所做的主要努力就是充分地發(fā)動群眾,動員起全民的抗日力量。
即便是毛主席晚年,也絕不是他拍腦門決定的“社會實驗”,不過是階級斗爭的延續(xù),至于其失敗的更本質(zhì)的原因,主要不在于群眾“不理解”,而在于階級斗爭的復(fù)雜性、反復(fù)性、長期性,以及階級力量的對比——這個對比不能局限于一國之內(nèi)看,而應(yīng)放眼整個世界范圍,敵人不僅僅是新生資產(chǎn)階級,也包括帝國主義和國際資產(chǎn)階級,以及內(nèi)部殘留和外部不斷輸入的舊勢力、舊觀念、舊習(xí)慣的力量的影響。
將《三體》中的精英主義與毛主席的群眾路線進(jìn)行強(qiáng)行縫合,這是很怪異的!
順著“人類從不感謝羅輯”的精英主義邏輯,此前的防疫爭論中,有些人又搬出“群眾跳火坑”的說法,并且羅列出毛主席從秋收起義、井岡山、古田會議到遵義會議的遭遇,來強(qiáng)行解釋“防疫轉(zhuǎn)向”。意思就是毛主席一直是“少數(shù)派”,不被“群眾”理解,“群眾”一次又一次要跳火坑,然后毛主席被迫一次又一次跟著跳進(jìn)去,然后在革命事業(yè)遭遇巨大挫折時候,覺醒了群眾、扭轉(zhuǎn)了乾坤……這樣的解讀完全是對歷史、對毛主席的巨大誤讀。
或許在“左”右傾機(jī)會主義者和紅軍高級領(lǐng)導(dǎo)那里,毛主席是少數(shù)派;但在紅軍基層將領(lǐng)和士兵、在蘇區(qū)群眾那里,毛主席從來都不是少數(shù)派,否則僅僅一個“士兵委員會”也不會獲得那么多紅軍將士的支持、取得那么好的效果,成為克敵制勝的重要法寶之一。要跳火坑的恰恰不是已經(jīng)組織起來的人民群眾,而是少數(shù)自以為高明的精英;真實的歷史斗爭過程,恰恰是群眾路線、無產(chǎn)階級民主,同精英主義、官僚主義、命令主義以及紅軍高層“左”右傾機(jī)會主義的斗爭。
毛主席在這個過程中所做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深入群眾開展調(diào)查研究、廣泛聽取群眾意見,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廣泛發(fā)動人民群眾,充分依靠人民群眾……(這些我們在“清零”執(zhí)行過程中是看不到的)
在小說《三體》中,羅輯從來沒想過走群眾路線,把三體人埋葬于“人民戰(zhàn)爭的汪洋大海中”(電視劇里的臺詞完全是對人民戰(zhàn)爭的蔑視與嘲諷);而小說的設(shè)定(面壁計劃)也根本不可能允許羅輯去向群眾解釋道理、發(fā)動群眾——正如筆者上面所說,這個虛構(gòu)設(shè)定本來就是劉慈欣“人為設(shè)定”的,并不是真實世界所遭遇的“應(yīng)然”局面;設(shè)定出來的“應(yīng)然”,恰恰是劉慈欣自身強(qiáng)烈的“精英主義”色彩的主觀故意……
即便我們要將“面壁計劃”與現(xiàn)實世界強(qiáng)行對應(yīng),不妨看看共產(chǎn)黨人在白區(qū)斗爭的歷史,當(dāng)時同樣存在兩條路線的分歧:
一條是精英主義式的,如現(xiàn)在的影視劇所渲染的頻頻出現(xiàn)“槍戰(zhàn)”和武打,把地下工作者表現(xiàn)為武林高手,少數(shù)英雄人物借助色誘、暗殺等手段與敵人斗智斗勇;
而另一條則是在毛主席提出的“隱蔽精干、長期埋伏、積蓄力量、等待時機(jī)”方針指導(dǎo)下,開展廣泛而細(xì)致的群眾工作,建立據(jù)點,建立關(guān)系,深入社會,爭取了包括工農(nóng)群眾、手工業(yè)者、小商人、知識分子在內(nèi)的社會各階層同情革命事業(yè),為解放戰(zhàn)爭的勝利奠定了重要基礎(chǔ)。
前一條路線在是被批判的,而后一條路線才是隱蔽戰(zhàn)線斗爭的主流,這才是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真實歷史。
「 支持烏有之鄉(xiāng)!」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wǎng)站日常運行與維護(hù)。
幫助我們辦好網(wǎng)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xiāng)網(wǎng)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