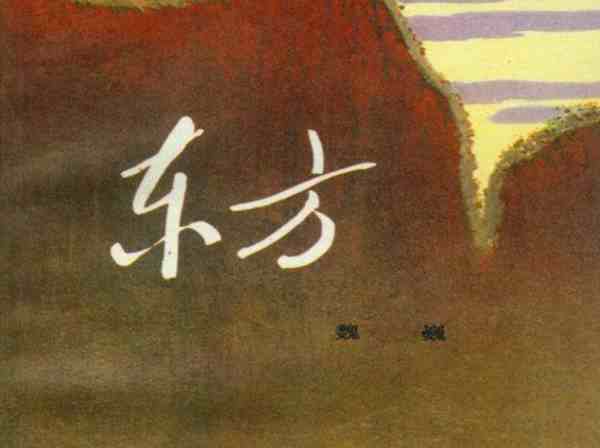“影片注重細節是沒有問題的,但一個重要原則是,細節應該為主題服務,不能為細節而細節。”
很多朋友希望我聊聊正在熱播的網絡大電影《特級英雄黃繼光》,我昨天專門看了,今天就和大家聊一聊。
首先,我覺得這部電影的主創人員是有誠意的,影片本身在近幾年抗美援朝題材的電影中,也是比較好的。
創作一個好的革命歷史題材影片,“誠意”非常重要,這其中的關鍵是要對革命歷史和革命英烈有發自內心的敬仰。
誠意,是創作一部好作品的必要條件。有誠意,不一定能拍出好電影。但只要有誠意,善于總結經驗教訓,再加上其他條件,假以時日,就一定能拍出好電影。
反之,如果沒有誠意,不管導演的名氣有多么大,鏡頭如何花哨,也只能拍出垃圾。
《特級英雄黃繼光》的另一個優點是扮演黃繼光的演員選得好,眼睛里有光,有一種單純、堅毅的氣質,不油滑,沒有江湖氣,這很難得,因為《亮劍》大行其道以來,江湖氣、匪氣在影視作品中幾乎被等同于英雄氣。
其實,在戰爭年代,我們的革命戰士,絕大多數都是淳樸的農家子弟,如魏巍在《誰是最可愛的人》一文中形容的那樣,“像秋天田野里一株紅高粱那樣的淳樸可愛”,江湖氣很少,匪氣就更沒有了。
02
—
但是,《特級英雄黃繼光》仍然提高的空間,我提出這樣幾點意見:
第一,還是沒有拍出我志愿軍雄赳赳氣昂昂的氣勢,整個調子太壓抑了;
毛主席總結偉大抗美援朝戰爭勝利的經驗,其中之一就是美軍“鋼多氣少”,我軍“鋼少氣多”。這種“氣”,就是“壓倒一切敵人而絕不被敵人所屈服”的英雄氣概,是堅信正義事業必勝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
沒有這種“氣”,很難想象在新中國成立之初百廢待興的形勢下,志愿軍就能夠在朝鮮半島上給武裝到牙齒的美帝國主義以迎頭痛擊,實現了近代以來無數仁人志士渴望卻不能實現的“御敵于國門之外”的夢想。
但遺憾的是,影片沒有傳遞出這種精神,幾乎沒有讓人感到樂觀、振奮的場面,人物表情始終都是凝重、憂郁和悲傷的。
第二,過度渲染了美軍炮火;
影片一開始,就是“黃繼光”(是影片中的黃繼光而不是歷史上真實存在過的英雄黃繼光)像一頭受驚的小鹿那樣在美軍劈頭蓋臉的炮火中閃轉騰挪,給觀眾的印象是,他完全“被美軍炮火壓得抬不起頭來”。
在后面的情節中,還有這樣的鏡頭:被美軍炮火蹂躪過的山谷,到處都是志愿軍烈士的尸體,隱蔽部里,也全都是尸體,只有一個重傷員用哭泣一般的聲音喃喃地說,“都死了,全都死了……”
不可否認,美軍炮火是猛烈的。但是,如何在影視作品中表現這種“猛烈”,如何表現志愿軍戰士對美軍炮火的態度,對編導來說,仍然是一個考驗。
在經典抗美援朝影片《英雄兒女》中,有這樣一組令人印象深刻的鏡頭:文工團組成戰地宣傳隊開赴前線,前方連續不斷的美軍炮火構成了一道壯麗的景觀,隊員們輕輕地唱著“為什么戰旗美如畫……”,從容地、甚至輕松地迎著炮火向前線開進。
這里并不是說美軍炮火沒有殺傷力,也不是說隊員們毫無戰場經驗,而是說,作為經歷過戰火考驗的老戰士,他們深知在炮火面前恐慌、戰栗沒有任何用處,他們也有避彈、防炮的經驗,知道美軍的炮擊是有規律、有死角的,掌握這種規律,就可以最大限度地減少美軍炮擊所造成的傷害。
實際上,美軍在戰場上為了壯膽,經常不看目標胡亂射擊,無論炮火還是機槍火力,射擊精度并不高,并不像話影片渲染的那么可怕。
總的感覺是,現在很多戰爭題材影片受《西線無戰事》《現代啟示錄》等歐美反戰電影的影響太大,經常有意無意地渲染戰爭恐怖論;
第三,黃繼光從一個普通農家孩子,在參軍后迅速成長為特級英雄,這個轉變過程在影片中表現得也不夠流暢。
《特級英雄黃繼光》,也可以說是黃繼光的“成長故事”,那么,他成長的轉折點在哪里?影片沒有對這個至關重要的問題給予清晰的回答。
在《英雄兒女》中,王芳成長的轉折點是王政委一番語重心長的談話,她意識到沉浸在哥哥犧牲的悲傷中是不對的,應該努力像哥哥那樣去戰斗才是正確的。
在電影《董存瑞》中,對董存瑞的成長,也有令人信服的表現。
甚至在美國主旋律電影《壯志凌云》中,湯姆·克魯斯也有一個成長的故事,他的轉折點在于他發現在越戰中“失蹤”的父親其實是一位掩護了同伴的英雄。
但《特級英雄黃繼光》中,對黃繼光成長的過程,只有平鋪直敘,流水賬似得表現,缺乏令人印象深刻的轉折點。
第四,過度遷就軍迷,糾纏槍炮型號等細節,陷入繁瑣哲學。
影片注重細節是沒有問題的,但一個重要原則是,細節應該為主題服務,不能為細節而細節。
通過刻意追求細節,給觀眾制造一個“專業高深”的印象,以此來掩飾思想的蒼白和靈魂缺位,是當代影視作品的通病。
如果把并無必要的細刻槍械、火炮型號的精力,用在深入挖掘黃繼光的精神世界上,影片效果可能會好得多。
另外,有些該考究的細節,編導似乎又沒有注意。
比如在最后的反攻中,我軍炮兵開始對美軍占據的山頭進行火力準備,從軍事常識的角度來看,為了避免誤傷自己人,一線步兵應該等到我軍炮火延伸后再發起沖鋒,但在影片中,我軍炮火還沒有延伸,步兵就急不可待地沖鋒了。
一些稱呼也似有錯訛。如影片中的“教導員”,真實身份是新兵連的軍事教員。“教導員”是我軍營級政治主官的稱呼,編導顯然沒有細究“教員”和“教導員”這兩個稱呼的區別。
有一些細節,則可能會讓觀眾陷入凌亂。
比如,黃繼光在一個被他打死的美軍士兵鋼盔中,發現了一張照片,上面是一個年輕女子(無疑是這位美軍士兵的妻子)和一個孩子的合影。黃繼光撿起這張照片,若有所思,神情凄然。
這張照片想傳遞什么暗示呢?我們正在進行的抗美援朝戰爭打錯了嗎?抑或我們應該同情正在瘋狂向我進攻的美軍士兵?
在魏巍全景式反映抗美援朝的長篇小說《東方》中,也有這樣一個類似的細節:我軍從被擊斃的美軍飛行員皮夾克的口袋里搜出了一張照片,照片上是這位美國大兵抱著一個全身赤裸的日本女人,還有一張當天晚上東京大戲院的門票。
白天充當殺人機器,晚上尋歡作樂,這就是美國大兵放蕩而罪惡的生活。
這兩個不同的細節,所傳遞出的不同暗示,相信大家都不會誤解。
第五,最后高潮沒有上去。
文藝作品先抑后揚,高潮一定上去,音樂、畫面結合起來,形成噴發的感覺,否則觀眾就不會盡興,積累的情緒就無法得到釋放。
比如,我軍最后反擊,奪回上甘嶺表面陣地,火力準備要猛烈,要酣暢淋漓、排山倒海,但影片等于是淺嘗輒止,炮聲剛響就停下來了。從接受心理的角度來看,這就會讓觀眾很不爽。
事實上,在上甘嶺戰役中,由于準備充分,我軍已經從戰爭初期的“鋼少氣多”,變成了“氣多鋼也多”,共向美軍陣地傾瀉了40多萬發炮彈,甚至形成了局部炮火優勢。
有人說,劇組沒錢,不能表現這些大場面。
其實,沒錢不要緊,可以用一些資料鏡頭,這樣還可以增強影片的真實感。
黃繼光犧牲后,我軍終于站在了敵人的陣地上,這個時候調子應該從悲壯轉向激昂,但突然就出字幕了,觀眾的情緒也被打斷了。
03
—
影片所以會出現這些問題,我想主要還是違背了生活是創作的唯一源泉原則。
今天的主創人員,在沒有長期體驗生活的情況下,只能把人物詮釋成自己熟悉的樣子,正如《隱入塵煙》中的馬有鐵、曹貴英不是農民而是小資一樣,在屏蔽了特級英雄黃繼光身上政治性內涵——革命英雄主義、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之后,影片所塑造的黃繼光(不是歷史上的英雄黃繼光)也只能是一個當代打工者的形象。
還是毛主席說得透徹,“在階級社會中,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
「 支持烏有之鄉!」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