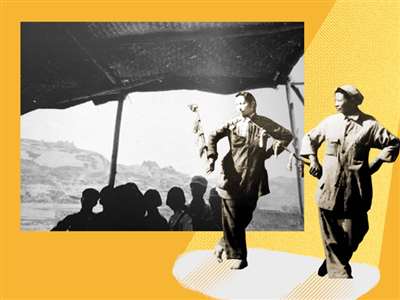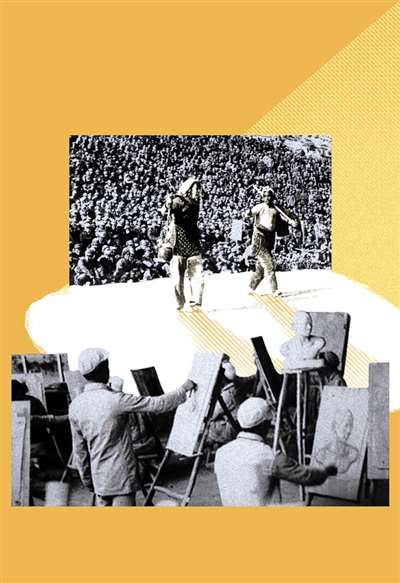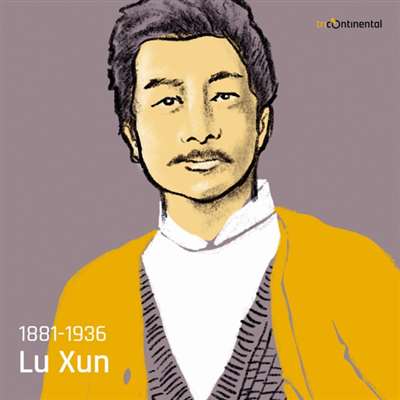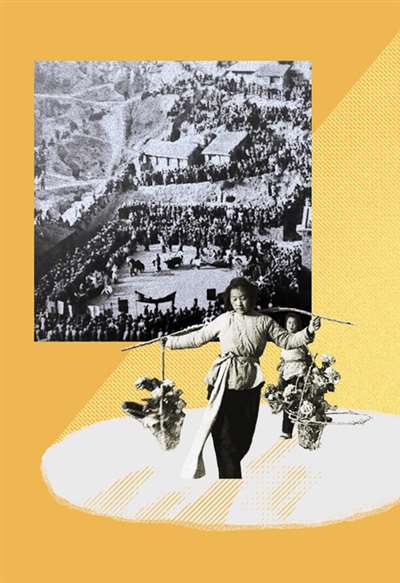親愛的朋友們:
三大洲社會研究所向您問好。
2022年5月11日,巴勒斯坦資深記者希琳·阿布·阿克利赫被一名以色列狙擊手擊中頭部,當時她正在報道以色列對杰寧(巴勒斯坦被占領土)難民營的軍事襲擊。狙擊手還向她身旁的記者開火,阻止他們幫助她。最終抵達伊本·西納醫院時,醫生宣布她不治身亡。
阿布·阿克利赫死后,以色列軍方襲擊了她在東耶路撒冷占領區的家,沒收巴勒斯坦國旗,并阻撓哀悼者播放巴勒斯坦歌曲。5月13日的葬禮上,以色列國防軍襲擊了大批到場的家屬及支持者,護柩者也沒有放過,還搶走了游行隊伍手中的巴勒斯坦國旗。阿布·阿克利赫自1997年起便擔任半島電視臺記者,備受敬重。她的遇害和以色列軍方在葬禮上的暴行,加深了以色列占領巴勒斯坦的種族隔離色彩。巴勒斯坦領導人哈南·阿什拉維博士在推特上寫道,攻擊巴勒斯坦國旗、海報、標語暴露了“壓迫者的惶惶不安”。她還解釋道,對這些文化符號的攻擊表明以色列人“懼怕我們的標志,懼怕我們的悲憤,懼怕我們的存在。”
阿布·阿克利赫遇害時報道的襲擊發生在杰寧,巴勒斯坦著名的自由劇院便位于此。2011年4月4日,劇院創始人朱利亞諾·梅爾·哈米斯在離阿布·阿克利赫遇害地不遠處遭到槍殺。梅爾·哈米斯曾說:“以色列正在摧毀巴勒斯坦社會的神經系統。這個神經系統包括文化、身份、交流......我們必須振作起來。我們正在卑躬屈膝地生活。”
前:京劇團演員在練功 后:魯迅藝術學院戲劇系學生在自建的席棚排練戲劇(圖源:延安紅云平臺)
80年前,來自上海等城市的數百名中國知識分子、藝術家齊聚中國共產黨的紅色根據地延安。1942年,一場嚴肅的討論在延安的窯洞內外展開,主題是在腐朽的封建制度、萬惡的西方帝國主義、殘暴的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三重壓迫下,中國文化陷入停滯。文藝工作者必須直面歷史現實及其提出的歷史任務。延安的這場爭論圍繞一個令人困惑的論斷展開,即藝術家可以脫離重大時代歷史背景開展工作。試想一下,若能擺脫以色列種族隔離的束縛,當代巴勒斯坦藝術家的創作將是怎樣。
受中共宣傳部代部長凱豐之邀,眾多藝術家在黨中央辦公室就革命戰爭時期的文藝現狀展開了為期三周的討論。毛澤東主席聽取了大家的發言,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并于次年出版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2022年5月的第52期匯編《到延安去:文化與民族解放》(Go to Yan’an: Culture and National Liberation)就延安的討論及其對當今時代的啟示發表看法。本期匯編由三大洲社會研究所藝術部供圖,回顧延安討論,以闡明現狀,并強調文藝工作對當前運動的關鍵作用。
上:歌舞團表演秧歌劇《兄妹開荒》 下:美術系學員在上素描課(圖源:延安文藝紀念館、延安紅云平臺)
藝術家的創造力源于生活經驗。在杰寧自由劇院上演的劇目不會反映特拉維夫或紐約咖啡館的生活,而是深入被占領的巴勒斯坦地區的想象。匯編解釋道:在延安,“城市知識分子必須進行自我改造,以縮小與農民群眾的差距。這種改造是延安座談會的核心,足以凝結成一股強大的政治力量。”
1942年5月23日,毛澤東在延安座談會上發表講話,向從上海等城市深入內地的藝術家、知識分子作了總結性發言。毛澤東說,這里正在形成新的生活方式,使人民挺直脊梁的新的動力,催生新的社會風氣。他說:“到了革命根據地,就是到了中國歷史幾千年來空前未有的人民大眾當權的時代……過去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此言意為,必須展開想象力,為站起來的中國新人民講述他們的故事。延安的知識分子堅信,文藝工作要與重大歷史事件緊密相關。
毛澤東還引用作家魯迅(1881-1936)的詩表明觀點。魯迅對這些變化洞若觀火,并寫進了詩中:
橫眉冷對千夫指,
俯首甘為孺子牛。
毛澤東把吸血的帝國主義、吃人的封建地主稱為“千夫所指”的敵人。“孺子”則指工人階級、農民、人民大眾。他解釋道,魯迅的詩句表明,作為“孺子牛”的藝術家絕不能屈服于壓迫,必須同人民一道為爭取自由而斗爭。
這場斗爭讓人民群眾敢于挺身而出,拒不向數百年來目睹其勞動被權貴用于斂財的屈辱低頭。藝術實踐和思想活動應反映這種廣闊的變化,中國消除絕對貧困的群眾運動,印度農民拒絕被優步模式支配生活的反抗,南非棚戶區居民堅決反對政治迫害的無畏精神,巴勒斯坦民眾在希琳·阿布·阿克利赫葬禮上的大游行,無不是變化的具體表現。
1943年春節,秧歌隊表演鬧秧歌(圖源:延安紅云平臺、中國青年報)
延安的這場爭論為文學藝術家開啟激烈的文化活動、向文化領域傳播新思想,將日常交流上升至新高度、開辟新的政治土壤、開啟新的歷史階段掃清了道路。文藝工作呼吁知識分子、藝術家著眼于未來,不再僅關心“藝術至上”的個性氣質,要為新目標而奮斗,開創新的人類社會。文藝工作并非就此淪為政治任務,因為這將削弱其擺脫當前困境的能力。藝術家、知識分子要支持各類運動,同時也要捍衛藝術空間,催生熱烈社會氣氛,助推新的文化。
毛澤東在延安的整風清楚地表明,文藝活動本身并不能改造世界。藝術家和知識分子反映現實,引發對具體問題的關注,并提出個人見解。但僅憑藝術無力解決所有問題。因此,我們有必要借助改造新社會的組織和運動的力量。一旦承載政治理論與實踐的重負,藝術形式往往會被削弱。藝術應當吸納工人階級、農民的情感,提出新的文化主張。在人類反抗壓迫的浪潮中,藝術將帶領我們開辟新的天地。
《與和平鴿飛向天堂前的最后一幕》馬拉克·馬塔爾(巴勒斯坦)作于2019年
曾參加自由劇院夏令營的小女孩阿斯瑪·納格納吉耶如此描述文藝工作的魅力:“在劇院的一次排練中,我扮演一只鳥,它飛過我居住的社區,又飛過杰寧,然后飛到海面上。如夢一般。”對未來的憧憬使我們在當下不懈奮斗著。
熱忱的
Vijay
「 支持烏有之鄉!」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