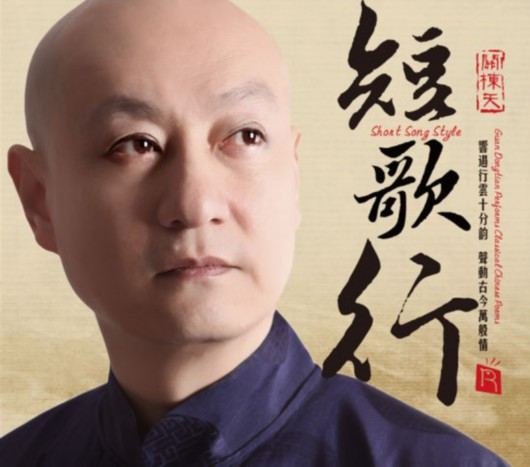
形容詞已經用光了。甚至,語言下面,已經失去了真意。越是價值崩盤無法言說,越是有無數登峰造極的用語滿天飛舞。而這眾多閃著光的、拚著命的、到了頂的、無所不用其極的詞匯的意義,等于零,沒人信,只徒增了這自由世界的苦惱和空虛。
還要怎么說話?還能怎么說話?這是2010年代的難題。
關棟天2012年的專輯《短歌行》,面臨著這種難以言說的尷尬。顯然,它是一個極致,但要說清楚這個極致,有著這時空之中的不可能。
中國歌唱藝術,從19世紀下半葉開始,有了一個轉折。當時,只是在極其局部的領域,發生了一些事,比如,洋務運動中,袁世凱的北洋軍歌《勸兵歌》,音樂部分取自普魯士《德皇威廉練兵曲》,四四拍的節奏,進行曲的唱法,都是中國音樂里沒有的;新文化運動中,自由體詩歌顛覆了舊體詩,順帶著,把舊體詩詞的吟誦、詞牌、曲譜、歌唱部分,也一并瓦解。
這些局部的東西,在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愿景中,漸漸匯成現代化的大潮,浩浩蕩蕩一百多年。到如今,它成了全局的東西,而中國傳統的歌唱,成了局部的東西。
中國的音樂和歌唱藝術,有一部分還存在著,甚至依然有廣泛的受眾,這就是它的民樂、民歌、戲曲。但也有一部分,消失得近乎無影無蹤——屬于文人的,與詩歌、文學、雅文化連成一體的歌唱,從生活中徹底斷了流。上世紀30年代之后,再說到歌曲,我們指的是完全西方體系的那種東西。
從民歌轉化而來的現代歌曲,包括來源廣泛的多民族民歌,在學院派音樂家的改造下,妥貼地植入了西方音樂體系,成為中國歌曲的主體。這其中,也有少數音樂家,在1949年之后,主要來自民族音樂、民族聲樂陣營,試圖以民間—學院、傳統—現代、東方—西方的融合手段,重新勾連起中國古典詩詞的歌唱藝術。比如,中央民族樂團的男高音姜嘉鏘,曾潛心鉆研古典詩詞的演唱;中央音樂學院教授黎英海,以漢族調式及其和聲,譜寫了一批古詩詞歌曲。
但這一方向的實踐,非常零散,不成體統,就創作者而言,從未有過要接續千年古音、重塑中國傳統文人歌唱的擔當。姜嘉鏘最為多產、更為突出的聲樂表現,是在現代發聲—民族韻味的民歌演唱方面,是一種古典民族美聲;而黎英海的成就,最顯赫的是民族鋼琴曲創作,他聲樂上的巔峰之作,比如《楓橋夜泊》,雖然運用了吟誦性旋律,卻更屬于民族藝術歌曲的范疇。——都是在西方音樂體系的框架內,澆鑄些許民族個性。
那個千年以來的文人歌唱還有沒有呢?有。靠著機緣巧合,在21世紀的錄音制品中,你或許會發現這些被沖刷到生活大河兩岸的砂粒,在無人問津中兀自存在。陜西師范大學曲云教授,發掘西安鼓樂曲譜,借鑒昆曲,在古譜基礎上以古箏伴唱唐宋詩詞,2004年出了一輯《山居秋暝》。同樣是這一年,遠在海之一角的香港,中國古典文學學者古兆申、張麗真、蘇思棣、劉楚華,以“宋音”唱姜夔詞,錄制了《姜白石詞擬唱》12首。青海古琴演奏家馬常勝2012年專輯《油菜花開的季節》,也應該算作這一個領域的事物,雖然他的背景是藏傳佛教,唱的是梵唄經文,但他以古琴輕托起詩咒的吟唱,如此自在曠遠,接通了那一縷來歷悠久的文人古意。……
關棟天《短歌行》,來歷奇特,細究構成這十首詩詞歌曲的諸種源流、動因,甚至堪稱稀奇古怪。但各種意外碰到一起,成就了這片蕭疏風景中最炫目的一個風景。
2008 年,作曲家孟慶華以串通戲曲、依字行腔、詩文吟唱的方式,創造了“伶歌”這種形式。一開始,伶歌最突出的面目是,戲曲名嗓、唱古詩詞、錄Hi-Fi唱片。這不同于戲曲,而是戲歌。而經典詩詞、名嗓、高保真、極致的國樂配器這一系列配套,使它不再是普通的戲歌,而是有著雅樂品質的音色輝煌的中國文人歌曲。當金石裂帛般的聲音從發燒級喇叭傳出,燒友們被震了。2008年,唱片《伶歌》問世,那是發燒片領域的一場傳奇。
《伶歌》中,關棟天擔綱開篇曲《將進酒》(李白詩)、壓臺歌《滿江紅》(岳飛詞)。2010年,《伶歌2》再發,關棟天再次擔綱開篇曲,以蘇軾詞譜曲的《念奴嬌·赤壁懷古》。這三首歌,均屬“伶歌”重炮、全片最強音,文案上稱之為“半歌半嘯”。
嘯,是很古的說法。讀古書,我們常看到文人墨客、壯士豪俠,縱酒賦詩,為歌、為吟、為嘯。何以嘯?何為嘯?在關棟天這里,我們算是找到真章了,那真氣充沛的高音如沖天一柱,直上九霄,已斷流百余年的東西,竟似無來由地再現了。
2012年的“伶歌集”《短歌行》,關棟天不再是唱一首兩首,而是足足唱滿十首詩詞,匯集成一張專輯。對他的宣傳詞匯,也進化了,不只是“半歌半嘯”,還有——“中國戲曲男高音”,“士大夫第一代言人”。
開篇即是曹操《短歌行》:“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篳篥,來自北地的吹管,發出罕見的獰厲之音。歌唱,吟誦,男低音合唱,古琴,蕭瑟又壯烈的心情,鼓群陣陣,鐘聲隱隱……在心境幽暗的低回、徘徊、情緒蓄積之后,唱到“山不厭高,海不厭深”,關棟天的聲音達到了中國戲曲男聲所能達到的最高音,仿佛帶著天地間的至高能量,石破天驚,砰然炸響,令人戰栗。這也是世界上的男高音所能達到的極致,可你從未領略現在這種,它完全是中國的發聲方法、中國的吐字行腔、中國的聲音味道、中國的共鳴。
關棟天出自京劇老生行當。遍觀歷史上的著名老生,馬連良、周信芳、楊寶森、高慶奎、余叔巖、李少春、言菊朋、譚富英,從沒有誰,有過這種東西。從師承上看,關棟天師從關正明,又從余派、楊派聲腔汲取了營養。這一脈唱腔藝術中,前輩大師余叔巖,在《烏盆計》中曾有過技壓群雄的嘹亮高音,但遠不如關棟天這般輝煌;而那種磅礴氣象,也部分來自大音量的音響美學和高保真錄音技術的輔助,傳統京劇藝術不可想象。
京劇老生行當,是京劇所有行當中唯一始終用真嗓的,這是關棟天能成為“戲曲男高音”的條件。但老生行當并非都是男高音,眾多老生前輩大師,主要的都不是男高音。關棟天能修煉成如今這樣, 是他自己的造化,靠的是得天獨厚的天賦,屬于意外。
一枚肉嗓,錚錚如金石之聲,竟有如此能量。中國古文字中,對男子歌唱最不可思議的形容,出自《列子·湯問》,說那歌手“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云”。現在聽關棟天《短歌行》,始信其有,不完全是虛構。
本來,“伶歌”這種方式是頗有些油滑的,遠不及古譜和律學研究的道路純正。但幸運的是,中國各地戲曲,確實是一個多樣又一體的整體,與古代文人雅士的歌唱也有著密切聯系,而且它們活著,代代傳承,至今還在民間延續著。當將近百人的精英團隊,操持著彈撥樂、拉弦樂、吹奏樂、打擊樂,以古典美、雅致國樂為傾向,而歌唱,以詩詞為詞,以依字行腔為聲,以中國聲樂、咬字吐音為人聲的美學,——這中國文人的樂與聲,竟得以集聚、升華、復現。中國古典傳統歌唱之美,從匠氣沉沉之中,在某些意外的片斷,來歷奇詭,卻重獲閃亮,有了一次較完整的美學表達。
文人歌唱,中國的詩歌吟誦,恍惚如是。一百多年了,它又一次來了。
唐朝詩人杜牧詩云:“獨坐幽篁里,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令人神往。或許,此途可期。
2012年11月12日星期一
相關文章
「 支持烏有之鄉!」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