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6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小說《日本沉沒》的中譯本,譯者為李德純。當時出版該書的目的,是為了對其進行批判,該書只印了1萬冊。書首,發表了編者所寫的評論《偉大的日本人民永遠沉沒不了!——評反動小說〈日本沉沒〉》,以下為該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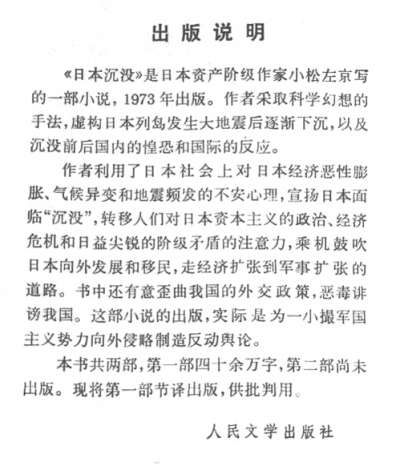
偉大的日本人民永遠沉沒不了!
——評反動小說《日本沉沒》
一九七三年,一個名叫小松左京的人,在日本文壇上拋出了一部書名聳人聽聞的長篇小說《日本沉沒》。他采取所謂科學幻想的手法,挖空心思虛構了這樣一個離奇的故事,說什么日本列島發生了一系列大地震,人們面臨“末日”,惶恐不安,紛紛轉移資產,逃往國外。日本內閣在策劃著“飛向世界”,引起了國際上的種種強烈反響。故事的最后,日本列島終于沉沒在太平洋的波濤洶涌中。
此書一出版,立即博得壟斷資產階級的重視。在資產階級報刊鼓吹之下,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此書重版一百余次,發行近四百萬冊,打破了日本近幾年“暢銷書”的記錄。資產階級又把它改編成廣播劇,搬上銀幕,竭力把日本社會的注意力引向日本是否“沉沒”這個問題上。
壟斷資產階級為什么這樣看中它呢?一家資產階級報刊說,因為它“準確地抓住了日本的社會現象”。現在,我們不妨剖析一下,“日本的社會現象”究竟是什么,作品又是如何看待這些“社會現象”的。
人所共知,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在美帝扶植下,日本經濟走向惡性膨脹和畸形發展。特別是進入七十年代以來,日本經濟危機迭起,壟斷資本的固有矛盾更趨激烈,尤其是擴大生產力同國內資源貧乏和市場狹窄的矛盾更為突出。資產階級報刊趁機極力散布“無資源國日本正陷于危急存亡之中”的論調。處在十字路口的日本經濟往何處去?這是日本各階級都在探索的問題。當然,不同的階級會得出不同的答案。陷入這種深刻矛盾的日本壟斷資本采取轉嫁危機的手段,在加強榨取本國勞動人民的同時,正瘋狂地向外輸出龐大的過剩資本,尋找市場和掠奪資源,來維持其貪得無厭的資本積累和高額利潤。僅海外投資一項,到1974年3月為止,已達一百億美元。其中1971年以后的海外投資,占戰后海外投資總數的近三分之二。這就表明,七十年代以來,日本壟斷資本更野心勃勃地要進一步加緊對外經濟擴張。正是在這種社會背景下,小說《日本沉沒》應運而生,鼓吹日本經濟“只呆在國內將一籌莫展”,“不同海外聯系就無法維持”,必須“探索新的出路”,“飛向世界”,“飛向海外”等等,甚至為壟斷資本出謀獻策,建議把這些作為“國家方針”,“從各方面強有力地推動”。
小說的作者要探索的是一條什么“新的出路”?擺在日本眼前的有兩條出路:一條是獨立、和平、民主的道路;另一條是從經濟大國到軍事大國、復活軍國主義的道路。除此之外,別無他途。廣大日本人民是堅決走前一條道路的。近年來,要求獨立的傾向在日本有了發展,資產階級中的某些人也愿意和平,不愿戰爭。但也有一小部分人,卻頑固地堅持要走后一條道路,即掠奪、擴張、侵略的戰爭道路。小說要“探索”的,就是后一條路。用它的話說,就是要日本壟斷資本“往發展中的國家實行‘遷廠’和‘對外投資’,同美國、歐洲共同競爭”;就是要日本“作為‘亞洲工廠’……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其實,這并不是一條什么“新”路。日本壟斷資本不論過去還是現在,一向把亞洲發展中國家看成它攫取資源、銷售商品和輸出資本的重要地區。但在他們眼里,“日本經濟仍然是以東南亞為中心”。從三四十年代的“大東亞共榮圈”到今天青嵐會的“亞洲大洋洲圈”,叫法雖然不同,但貨色卻是一樣的。他們妄圖在東南亞建立一個以日本為盟主,同“美元經濟圈”和“歐洲共同體”相抗衡的“日元經濟圈”,進而建立“亞洲太平洋共同體”,并把它看作是向全世界擴張的必由之路。小說大肆鼓吹所謂“新的出路”,也正是這樣一條路。
為了實現這樣一條“新”路,作者在作品里露骨地說什么要“為了日本的利益”、“日本民族的健全發展”、“對日本民族承擔責任”、“即使引起一些沖突也在所不惜”。他還費盡心機,安排了一個“對日本目前政治中樞仍具有一定影響力”的渡老人出場,聲嘶力竭地叫嚷“日本民族氣數沒有到頭”、“還有相當大的沖勁”,日本“沉沒”,將會給“日本民族提供一個鍛煉成人的機會”等等。這就說明,為了掩蓋軍國主義的傾向,作者只好再一次打起了沙文主義這桿破旗。他不厭其煩地玩弄“民族”這個字眼,鼓吹日本工農大眾在日本“末日”面前,同壟斷資產階級有著“共同的命運”。但是,事實是無情的。幾千年的文明史,就是一部階級斗爭的歷史。無論做這如何巧妙地耍弄他那支筆,也是掩飾不了日本社會尖銳的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的事實。資產階級時代,卻有一個特點:它使階級對立簡單化了。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打的丟的陣營,分裂為兩大相互直接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日本歷史的發展沒有超越這個總的規律。今天的日本社會同樣是由不同的階級構成的。只要資本主義在日本存在一天,日本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就要進行不可調和的、你死我活的階級斗爭,這還有什么“共同的命運”可言?然而,正像歷史上的社會沙文主義者為了實行資產階級政策,要求無產階級為了“保衛祖國”,即保衛“大”國掠奪殖民地和壓迫異族的“權利”而放棄階級斗爭一樣,《日本沉沒》的作者也硬要日本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為了“民族生存”同壟斷資產階級同舟共濟,把兩者放在“民族”關系之中,企圖造成一種假象,仿佛兩者有著“共同的命運”,這簡直是在制造騙人的幻想。
反動小說《日本沉沒》還大肆宣傳過去日本軍國主義“剝削有功”、“侵略有理”,來為今天的“飛向世界”披上合法的外衣。書中左一句“我們同時代的人是奮斗過來的,日本也因此變好了,日子順溜了”,又一句“從戰時到戰后,……花費了半輩子工夫,披荊斬棘,創造了所有財富,好容易才建立起來(今天)的生活”,等等。作者妄想用這些動聽的謊言,來掩蓋當年日本帝國主義對內對外血淋淋的掠奪和剝削的實質。但就以“戰時到戰后”來說吧,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和東南亞國家,給我國人民和亞洲人民以及日本廣大勞動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日本經濟急劇膨脹,一躍而為資本主義世界的僅次于美國的“經濟大國”,也完全是靠美帝的侵朝戰爭和侵越戰爭的滋養,靠對日本勞動人民和第三世界的剝削和掠奪造成的。這種戰爭橫財,不僅喂肥了日本壟斷資本家,而且促進了日本以軍需工業為基礎的重工業和化學工業的發展,給他們提供了剝削勞動人民更多的剩余價值和榨取更大的超額利潤的基礎。因此,壟斷資本家“變好”的日子,“順溜”的日子,完全是靠榨取日本和第三世界億萬勞動人民的血汗建立起來的。日本千萬勞動人民的日子并沒有變好。他們在失業增加,物價飛漲的沉重打擊下,生活更加惡化,還是處在生活毫無保障的困境。今天在日本全國有2500萬左右的貧民,也正如恩格斯所說的那樣:“每一個大城市都有一個或幾個擠滿了工人階級的貧民窟”、“他們必須在比較幸福的階級所看不到的地方盡力掙扎著活下去。”哪里能談得上什么“順溜”呢?
以偽裝的科學遮掩反動的政治傾向,是小說《日本沉沒》的突出的特點。作者捏造了一種地震決定社會發展,地震決定政治的“理論”,同樣是為日本帝國主義過去的罪惡行徑粉飾,為他們現在的意圖辯護,書中竟然說:“第一次關東大地震是造成這個國家走向法西斯的原因。”
按照唯物辯證法的觀點,社會的發展,主要地不是由于外因而是由于內因。許多國家在差不多一樣的地理和氣候的條件下,它們發展的差異性和不平衡性,非常之大。同一個國家吧,在地理和氣候并沒有變化的情形下,社會的變化卻是最大的。
日本歷史的發展,也充分證明了這一點。1868年日本明治維新,進行了一次不徹底的資產階級革命,但仍保留著嚴重的封建殘余。與此同時,世界資本主義迅速進入壟斷階段。在這種國內外條件下,一個帶軍事封建性的帝國主義的日本迅速發展起來。它對外不斷進行侵略擴張,對內加強法西斯專政。在這個時期,封建的閉關鎖國的日本變為帝國主義的日本,這些國家的地理和氣候并沒有變化。歷史事實雄辯地證明,社會變化,主要是由于社會內部矛盾的發展。一個國家的對內對外政策,主要的是決定于社會的政治、經濟制度,而不是地理條件。很明顯,作者制造這樣一個反動的“地震決定論”,是企圖要論證地理環境本身決定日本要求奪取“生活空間”,使壟斷資本的對外擴張政策合法化。至于關東大地震,它之所以造成重大人命和財產的損失,完全是反動統治階級的罪惡剝削,人為地加深了地震時出現的災禍所造成的。它曾一度加深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日本的經濟危機,這使階級矛盾更加尖銳,革命形勢日益成熟,直接威脅著帝國主義制度的存在。它倒確實曾被統治階級利用,作為實行白色恐怖的借口,大規模鎮壓和屠殺工人階級和革命人民。
因為,無論在理論上和現實中,小說作者炮制的“地震決定論”都是根本站不住腳的。它只不過是從法西斯主義的武器庫揀來的破爛,是希特勒、墨索里尼和老牌日本軍國主義所兜售過的“地震政治論”的變種。尤其是小說出籠于1973年,正好是關東大地震五十周年,日本壟斷資本借機動員宣傳機器,大肆渲染“第二次‘關東大地震’即將來臨”,還投入大批人力物力,煞有介事地進行所謂“防震災演習”,把已經因為日本經濟惡性發展、氣候異常和地震頻發而深感憂郁的人們,弄得更加惶惶不安。作者正在此時制造出這個“地震決定論”,并不是偶然的巧合。他以假的地震科學為論據,以藝術描寫為手法,制造荒唐離奇的景象,從而轉移人們對日本資本主義危機的注意力,掩蓋日本社會尖銳的階級矛盾,妄圖把人們動員到侵略和戰爭的道路上去。
作者憑著反動階級的本能,在書中描繪了“日本沉沒”前后,所謂各國對日本的態度。書中從各方面歪曲和攻擊我國的對外政策和路線,并污蔑我國乘日本“大變動”之危,“要在東南亞插一手”,同美蘇保持“均衡”,進行“交易”,這是明目張膽地進行。
中國是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一向根據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建立和發展同各國之間的友好關系,一向支持第三世界國家和人民爭取和維護民族獨立,發展民族經濟,反對殖民主義、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斗爭。中國同第三世界不僅在政治上互相支持,在經濟上也是互相幫助,以完全平等的原則,同這些國家發展經濟合作關系,這已經成為國際間經濟合作的典范。我國的國際影響日益擴大。在作者的心目中,這就成了對他鼓吹的經濟擴張和侵略政策的一個巨大對抗力量。因為,作者的狂叫,是同他的小說里的整個擴張主義的主題密切相關的,其目的就在于要挑撥東南亞國家同中國日益發展的友好關系,破壞亞洲人民的團結,包括中日兩國人民的團結。但是,東南亞各國是決不會忘記帝國主義,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殘酷教訓的,《日本沉沒》的作者的一切挑撥終究是白費氣力的。
小說《日本沉沒》是一本很好的反面教材。它又一次告訴人們,決不能忽視日本軍國主義勢力的存在,決不能忽視當前日本的反動文學如何為復活軍國主義效勞。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空前覺醒的日本人民,是決不會允許一小撮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再次把他們推入侵略戰爭的苦難深淵的。日本人民反對復活軍國主義、爭取民族獨立、和平、民主的斗爭,正在蓬勃發展,盡管斗爭的道路是曲折的,但是日本人民的前途是光明的。在日本人民斗爭的波濤洶涌面前,沉沒的只能是一小撮腐朽沒落的壟斷資產階級,只能是人剝削人的舊世界!偉大的日本人民,是永遠也沉沒不了的!
附:
遭逢“文革”的《日本沉沒》
來源:《 青年參考 》( 2011年04月15日 06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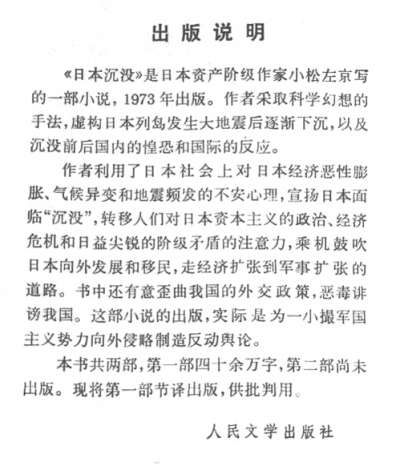 |
|
小說《日本沉沒》中文版的出版說明 |
1975年6月,尚處在“文革”階段,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小說《日本沉沒》的中譯本,譯者為李德純。當時出版該書的目的,是為了對其進行“批判”,該書只印了1萬冊。書首,發表了編者所寫的評論《偉大的日本人民永遠沉沒不了!——評反動小說〈日本沉沒〉》,該文帶有那個年代的鮮明烙印,以下為該文摘錄:
1973年,一個名叫小松左京的人,在日本文壇上拋出了一部書名聳人聽聞的長篇小說《日本沉沒》……
此書一出版,立即博得壟斷資產階級的重視。在資產階級報刊鼓吹之下,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此書重版100余次,發行近400萬冊,打破了日本近幾年“暢銷書”的記錄。資產階級又把它改編成廣播劇,搬上銀幕,竭力把日本社會的注意力引向日本是否“沉沒”這個問題上。……
反動小說《日本沉沒》還大肆宣傳過去日本軍國主義“剝削有功”、“侵略有理”,來為今天的“飛向世界”披上合法的外衣。……
以偽裝的科學遮掩反動的政治傾向,是小說《日本沉沒》突出的特點。作者捏造了一種地震決定社會發展、地震決定政治的“理論”,同樣是為日本帝國主義過去的罪惡行徑粉飾,為他們現在的意圖辯護,書中竟然說:“第一次關東大地震是造成這個國家走向法西斯的原因。”……
小說出籠于1973年,正好是關東大地震50周年,日本壟斷資本借機動員宣傳機器,大肆渲染“第二次‘關東大地震’即將來臨”,還投入大批人力物力,煞有介事地進行所謂“防震災演習”,……作者正在此時制造出這個“地震決定論”,并不是偶然的巧合。他以假的地震科學為論據,以藝術描寫為手法,制造荒唐離奇的景象,從而轉移人們對日本資本主義危機的注意力,掩蓋日本社會尖銳的階級矛盾,妄圖把人們動員到侵略和戰爭的道路上去。……
小說《日本沉沒》是一本很好的反面教材。它又一次告訴人們,決不能忽視日本軍國主義勢力的存在,決不能忽視當前日本的反動文學如何為復活軍國主義效勞。……在日本人民斗爭的波濤洶涌面前,沉沒的只能是一小撮腐朽沒落的壟斷資產階級,只能是人剝削人的舊世界!偉大的日本人民,是永遠也沉沒不了的!
相關文章
「 支持烏有之鄉!」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