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體象與工具象
——若干理論與實踐問題再探究
【作者按】現代化的研究是實體象轉入工具象。連結二者是主體范疇與經濟范疇。政治經濟學的主體范疇是對“實體象”的對象性鎖定,確定“由道及象,由象索識,由識而知”的范疇定制原則。以著名的“商品兩因素”(道器兩儀)為例,寫就物象的是工藝學的使用價值,只有價值規定(質與量統一的主體的異化關系)才構成“主體象”(與古代共同體社會“君子之氣”相對立的“死勞動”——物化勞動象)。作為道器關系的矛盾具象,使用價值與價值主體范疇分別引出其在商品社會所對應的經濟范疇——勞動分工與商品生產勞動,從而表明是“價值”絕非勞動本身(“真正的勞動”即勞動主體范疇)、更加不是使用價值(各種商品“物象”),連通商品世界的對象歷史。象的起點不是圖,是宇宙本身。圖,是象文字的歷史起點。可見,“具象”(無論圖文并茂抑或大象無形)針對的始終是范疇法。相較而言,抽象勞動是一項客觀知識,直指商品“異化獸”的經濟共識。一旦認定“資本=投資”,否認資本原罪的原始積累,否認利潤索取來自資本積累,就陷入新古典術語所集成的邊際主義的分析思路。所謂資本的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是西哲及其社會學的流行用語,其反映資本家內心對于“資本善”的認知訴求。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馬克思區分必要價值從而勞動力價值和剩余價值,乃至區分價值本身和資本的剩余價值,目的就是區別算法生產方式和算法惡。如果資本不是分配關系的算法惡(從價值惡到剩余價值惡),又怎會嚴重依賴于算法方式呢?很明顯,機器及其衍生形態(包括信息、科技、數字和信用)乃是資本所依賴的能夠稱得上“算法文明形態”的東西。資本惡本身包含了算法文明和算法分配惡,但它完全排除勞動工藝學意義的文明規劃;勞動美學是不在場的,在場是范疇“孫行者”“孫悟空”,——以“陶行知”“陶知行”為方法論。在革命詞典里,價值理性為“價值象”(實體象)替換,工具理性則被工具象的術語所替代。蓋因工具象支配著工具理性,工具象自身也由資本的價值象所支配。導致自“資本惡”切入機器的分析機理,由實體象而工具象,便循著“從抽象上升到具體”路線進行。機器的生產方式(作為“技術獸”)始終是抽象規定,機器和生產關系的結合則是“工具象”的具體知識。機器形式是資本惡在先進的生產制度意義項下所借助的特別的社會形式——經濟形式、政治形式乃至思想文化形式。這給了要素論由“知”而“識”的可乘之機。由“賈知知”到“賈淺淺”,資產階級理論教科書為知而知,人為制造了現代文明的景觀理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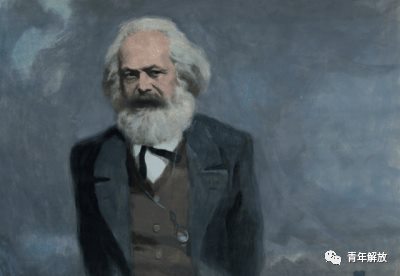
《資本論》具象法之一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資本論》具象法之二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資本論》具象法——有機構成與理論體系形成探究”第四部分
《資本論》具象法之三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引論:現代化所孕育的文明矛盾
主要矛盾——如上文提到的現代化矛盾,是矛盾的實踐類型。有機構成所突出的就是這種類型。資本主義現代化和Pm: A的道路通史有關,然則,它的實質內容是闡明機器的從無到有以及轉化形態及衍生形態的各種社會規定。社會主義現代化和A:Pm與Pm: A通史關系的處理有關,由此引出勞動者的各種歷史考察以及主體的經濟社會形態考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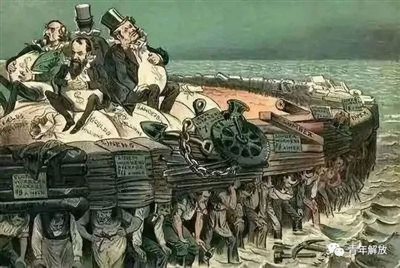
這表明,“現代化理論”歸根結底是有機構成意義的現代化路徑探究——如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機器本位、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勞動者本位,而無論是哪一者都可以直接追溯到馬克思對工場手工業的歷史研究與講述。《資本論》中,馬克思對現代化命題的掌握正是基于機器的歷史產生、它的資本主義利用以及圍繞著這個物質基礎。“大工業必須掌握它特有的生產資料,即機器本身,才能生產其他機器。這樣,大工業才建立起與自己相適應的技術基礎,才得以自立。”
【注:馬克思.資本論(法文版)[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386-387.】
“不管貨幣資本和商品資本怎樣執行資本的職能,怎樣順暢地流通,它們只有轉化為生產資本的流動組成部分,才能夠變為和固定資本相對立的流動資本。”“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的形式規定性之所以產生,只是由于在生產過程中執行職能的資本價值或生產資本有不同的周轉。”
【注: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86-1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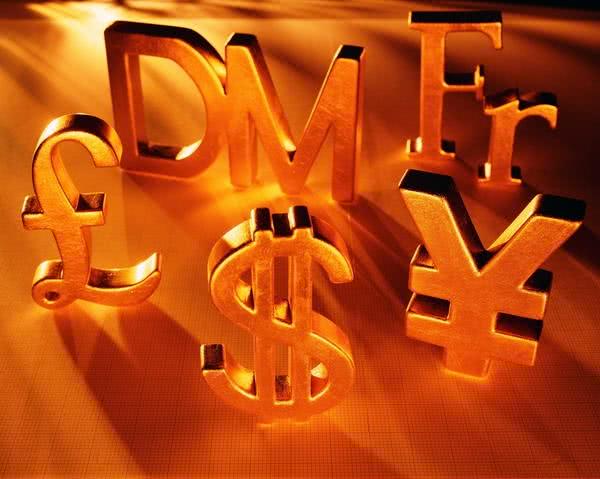
進而,“由積累提供的追加資本,主要是充當利用新發明和新發現等的手段,總之,是充當利用工業改良的手段……一方面,在由于集中而加劇的積累進程中形成的追加資本,同它自己的量比較起來,會越來越少地吸引勞動者。另一方面,舊資本周期地經歷的技術變革和相應的價值構成的變化使它越來越多地排斥以前它所吸引的勞動者。”
【注:馬克思.資本論(法文版)[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6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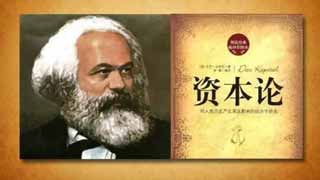
“在利潤率中,剩余價值是按總資本計算的,是以總資本為尺度的,所以剩余價值本身也就好像從總資本產生,而且同樣地從總資本的一切部分產生,這樣,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的有機差別就在利潤的概念中消失了。因此,實際上,剩余價值本身在它的這個轉化形式即利潤上否定了自己的起源,失去了自己的性質,成為不能認識的東西……一般利潤率,從而與各不同生產部門所使用的既定量資本相適應的平均利潤一經形成,情況就不同了。”
【注: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87.】

同時,“市場價值(關于市場價值所說的一切,加上必要的限定,全都適用于生產價格)包含著每個特殊生產部門中在最好條件下生產的人所獲得的超額利潤。把危機和生產過剩的情況完全除外,這一點也適用于所有的市場價格,而不管市場價格同市場價值或市場生產價格有多大的偏離”。
【注: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21.】
機器:資本主義現代化進程的表征
對機器的物質基礎的生產形式、流通周轉形式及競爭分配形式的分析表明:機器是資本主義進程的“現代化表征”。這促使馬克思深入探究它的歷史來源和根據,最終得出結論:“作為工場手工業分工的產物的這種工場,又生產出機器。機器使手工勞動不再成為調節社會生產的原則。一方面,技術上不再有必要使勞動者終生適應于某種局部職能;另一方面,這個原則本身加于資本統治身上的限制也消失了。”
【注:馬克思.資本論(法文版)[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372.】

矛盾不僅僅是結果,同樣是發生;歷史也不僅僅是結果,同樣是發生。《資本論》指示的“總公式矛盾”不僅是一個總的歷史結果,而且恰恰是歷史的開端——歷史發生的矛盾展開。這意味著靠“邏輯定義”為唯一手段的敘說已經無濟于事。那么,教科書該如何安排“發生的矛盾”的敘述形式?馬克思對總公式矛盾的處理方式是“絕對剩余價值”與“相對剩余價值”的理論關系,即處理機器的如何發生與機器的如何成長。
機器首先是一個歷史的具體——工藝學的歷史具體,其次是資本主義的理論抽象。它作為理論具體是把實踐理論化,由此有了馬克思的這種理論說法:“以分工為基礎的這種協作,在工場手工業上取得了自己的典型形態,在真正的工場手工業時期占據統治地位。這個時期大約從十六世紀中葉到十八世紀末葉。”
【注:馬克思.資本論(法文版)[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338.】
協作作為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特殊形式”是馬克思的命名,因為它是資本主義進程主要矛盾的具象發生。歷史具體(抽象)→理論抽象→理論具體,顯然,這指示了總公式與生產一般的統一,以理論抽象為中介的歷史具體和理論具體結合,展示的工作路線是“歷史本位——理論定位——邏輯本體——實踐本相”,“于是,邏輯推進線路更正為:對象(抽象和具體)——思維(抽象和具體)——知識(抽象和具體)”。工作鏈條的進階是形成“思維具體”;“這顯然意味著‘大寫字母’意蘊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路徑的知識生產,體現了對辯證法的方法論構造——對象(具體—抽象)——研究對象(抽象和具體合一)——知識理論建構(抽象—具體)——實踐化思索。”
【注:許光偉.抽象和具體的辯證法意蘊——再論《資本論》的研究方法與敘述方法及其時代意義[J].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04):6-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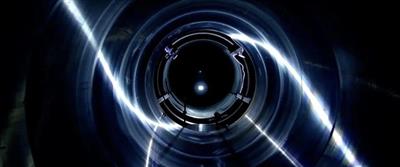
由此,《資本論》具象的機器研究線索包括:1.實在→具體→(在工藝學中形成)歷史具體的運動環節。這就是勞動資料的工藝學形式研究,“勞動資料是人置于自己和他的勞動對象之間作為自己的活動的傳導者的物或物的綜合體。”
【注:馬克思.資本論(法文版)[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167.】
2.歷史具體→抽象→理論抽象的運動環節。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展示了機器的從無到有,為了整體調查與勘探這一歷史狀況,馬克思研究了工場手工業的整個機構,耙梳它的全部的歷史,從中區分工場手工業的兩種基本形式:混成的工場手工業和有機的工場手工業。馬克思指出,“第二類工場手工業,是工場手工業的完成形式,它生產的產品要經過相互聯系的發展階段,要經過一系列的階段過程,例如,制針手工工場的針條要經過72個甚至92個工人之手,其中沒有二個人是完成同一種操作的。”
【注:馬克思.資本論(法文版)[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3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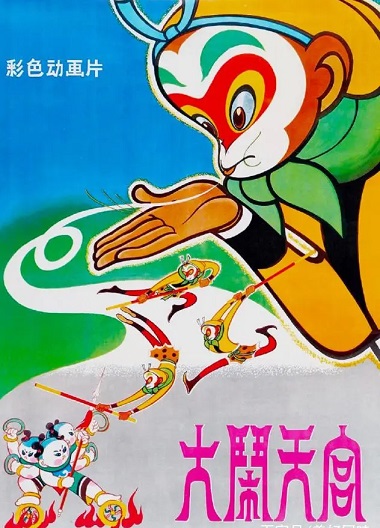
“數量較多的工人受同一資本指揮,既是工場手工業的自然起點,也是一般協作的自然起點。但是,工場手工業所要求的分工使所使用的工人人數的增加成為技術上的必要。現在,單個資本家所必需使用的最低限額的工人人數,要由現有的分工來規定。”
【注:馬克思.資本論(法文版)[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62.】
以分工為基礎的協作或者說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當然是一個理論抽象:“以分工為基礎的協作,也就是工場手工業,最初是自發的無意識的創造物。一旦它得到一定的鞏固和十分廣泛的基礎,它就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有意識的、有組織的形式……(以致可以說)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專門的科學,是在工場手工業時期才出現的,它只是從工場手工業分工的觀點來考察整個的社會分工,把社會分工看成是用較少的勞動生產更多商品,從而使商品便宜和加速資本積累的手段。”
【注:馬克思.資本論(法文版)[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367-368.】
并且,這里已經顯示:“從抽象規定的‘絕對剩余價值的生產’(第三篇)出發,到特殊規定的‘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第四篇)”,由此,“每一‘一般(抽象)—特殊(具體)—個別(具體)’序列的實踐發展都表示‘總體建構’的一次完成。這表明,總體和它的思維形式的發展是同步的。”
【注:許光偉.抽象和具體的辯證法意蘊——再論《資本論》的研究方法與敘述方法及其時代意義[J].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04):6-17.】

3.理論抽象→(邏輯上升到)思維具體→(重回)歷史具體運動環節。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中形成的“理論抽象”是一種生產關系范疇,從而,機器不是別的經濟形式,乃是“資本主義形式的分工。”
【注:協作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基本形式,但不是特征形式;在機器時代,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的原則已經并入機器體系,作為機器改變世界、資本主義利用機器系統進行經濟關系協調與生活統治的基礎。機器是資本主義統治形式的分工,從而是生產方式的特別具象,它的根基是特殊規定的矛盾。這些是理解“簡單勞動價值論”和“資本主義現代化進程”的鑰匙。】

它表明:“在一定的歷史基礎上,分工不可能采取別的形式。”機器手段或者說“無非是生產相對剩余價值的一種特殊方法……靠犧牲勞動者的利益來增加人們稱之為國民財富的資本收益。它創造出保證資本對勞動的統治的新條件。因此,它既表現為社會經濟形成過程中的歷史進步和必然的階段,又表現為文明的、精巧的剝削手段。”
【注:馬克思.資本論(法文版)[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368.】

這種技術分工形式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運動路徑于是成為“社會形式的運動規定”,“并說明‘生產總體’總要向著社會統制的系統前進”,“這決定必須從‘現實的機體’即個別的總體中提取規律認識”;然則,“總體的發展以思維形式表現出來,就形成了‘總體思維約束下的客觀知識’。顯然,這是從對象思維出發的批判路徑的邏輯知識生產”。“在這項社會客觀知識下,流通過程體現為‘資本積累的條件和形式系統’的分析……這使得關于‘社會總體’內容和形式的結合分析終歸也成為起點的規定……它是研究起點和敘述起點在現象過程的統一。‘資本總體’概念于此才真正地開始形成,因為一個有了流通規定的資本主義分配,就實現了對‘三位一體公式’的全面克服,關于‘資本’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第一次從思維上被具體把握,形成有抽象規定內置其中的‘思維的具體結構’。”
【注:許光偉.抽象和具體的辯證法意蘊——再論《資本論》的研究方法與敘述方法及其時代意義[J].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04):6-17.】

機器成為資本形式以及機器的資本形式再度成為流通形式,都不過是鞏固資本主義的物質基礎和社會基礎。機器的物質基礎是現實基礎,同時是統制的系統內容和形式,從而是經濟基礎,作為制約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手段和調節工具,機器形式甚至是上層建筑的直接組成內容和組成形式,各種轉化形式的社會機器和衍生形態在現代資本主義生活中日益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功能角色,行使經濟權杖和超經濟的統治力——而這就是當代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工業化邏輯”。對機器形式本身的治理仍舊整體服從于資本的再生產策略和集體分配的需要。
以上對《資本論》機器研究的概述,從另一角度實證與演繹了馬克思對“有機構成”實踐路線的解讀:生產→生產資料和生產關系→生產關系和交往關系→國家形式和意識形式同生產關系和交往關系的關系→法的關系→家庭關系。它說明了剝削手段和條件的具象的全過程。這對中國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無疑提供了反面的啟發。
具象歸根結底是實踐邏輯
《資本論》具象法的立足點從而是資本主義的抽象統治,并且更加關注財產本體的抽象統治如何轉化為“資本的具體統治”——它的策略和手段工具。資本統治的同質空間旨在從抽象出發,把一切“具體理性”攝入自己的統治規定,成就“資本=剩余價值”這一價值抽象性的特殊社會理性實體。抽象性是資本統治的實體,這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就實質內容而論,資本主義生產唯一性的根據是抽象統治,這個規定性的核心出處乃是“資本主義經濟五行”(G—W……P……W′—G′),在于這個五行循環運動的中心成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乃至進行系統維護、運行與統治的“絕對真理”。

為了完成抽象統治,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得不變身為理性同質系統,使剩余價值成為目的理性的“唯一者”:這可能引導人們對“抽象”的把握,是從畸形化和異化形式上思考“抽象的發生”,并傾向于用它直接替換和認識覆蓋“具體本身的發生過程”。但就資本主義統治既通過資本、又通過機器而言,它們既是抽象和具體的關系,作為統治手段的每一方又都同時是“抽象和具體”;統治形式是否抽象或具體,亦需要從統治方式的技巧和隱蔽性程度的結果上進行判別。因此不能將抽象僅僅視為理論的元素和邏輯的行動,它必須同時甚至首先是實踐的元素和歷史的行動。另外,抽象也不是一個個孤立的思想單元,乃是范疇家族的有機聯系。其不是從一個預設的理念范疇(就像理性假設那樣)如價值,演繹一切價值形式直到價格現象運動。抽象統治的本質內容包括階級關系統治和拜物教的意識形態統治,決定具象必須包括全部的內容,包括這兩方面的抽象和具體的結合。

所謂“從抽象上升到具體”,實際指馬克思對生產一般的兩次運用:一次作為思想形式的“結果—發生—發生—結果”,一次作為和實踐配合的行動路線即“起—承—轉—合”;由此達到的奇妙效果是使發生學成為研究方法的工作邏輯,普遍的形式是從個別上升到一般。有機聯系是總聯系的“范疇”。這一規定使唯物史觀處于工作的狀態、實踐的狀態,而破除了無方向的循環解釋神秘,提供道路和系統的母子體用思考理性維度。
理論大結局
以最高范疇而論,天——氣——道——象,為中國人的具象法。歸納起來看,中國具象包括四方面內容:形象,物象,意象,抽象。以此觀之,中國人的文化觀不是感性和無邏輯,是以直觀和領悟為第一元素。在其看來,宇宙根本上是一連通器,在理解上唯有運用“象思維”。中國的主體審美曰“象”(托物的象、意念的象)。舞蹈水袖,建筑飛檐,書法狂草,意境禪宗;小橋流水,蘆葦戲鴨,人劍合一,鯤鵬展翅。這些無不貫通“物象”和“意象”,具象一如。心不自心、因境故心,境不自境、因心故境,說的乃是象思維的構境法。無一例外,這都是主體在“說”。人始終是托象的主體因素。萬物和人須臾不離。階級問題更是如此,曰:
惡 為 階 級 名
范 疇 具 象 生
我 欲 乘 風 去
概 念 纏 吾 身
—— 階級 · 絕句

商品,首先是道,其次是象,最后才是黑格爾邏輯的改造和運用的問題。抽象只是象的落腳。象思維的要點在于以對象解象,以規律解道。主體(Juche)是宇宙本身。這是典型的象思維。于是,應當結合中華思維學考察階級用語的“象、物、精、真、信”。象為首,信為落腳。在思維形式上,價值是市民階級的“信”——主體共識。價值來自勞動,價值是勞動的異化象,徹底背叛了勞動美學。
有機構成的抽象和具體讓“總公式—生產一般”成為連體的思維工作形態,也就迫使比類成為對取象的客觀反映、綜合成為對分析的客觀反映、具體成為對抽象的客觀反映乃至演繹成為對歸納的客觀反映。
這些反映形式由此獲得科學認識的理性,成為具有“批判力”和能夠服務于階級分析的理性工具。
(文章全部貼完)
「 支持烏有之鄉!」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