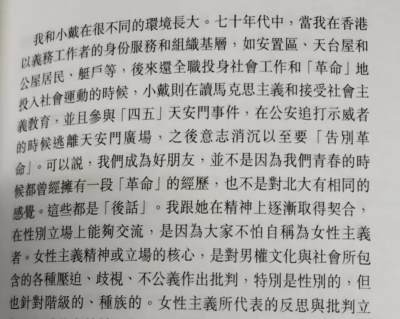我自己的理解是戴老師自己給出的框架,中國有一個意識形態斷裂的過程,官方對社會主義思想的處理大概經歷了這么幾個階段,八九十年代是一個妖魔化的過程;千禧年之后現代中國和社會主義逐步成為自我合法性的重要一部分;18年之后中國的經濟增速放緩,深層次經濟、政治矛盾加劇,自由派的觀點不能再為個人境遇給出有力回應,左翼思潮回歸,這是“戴錦華熱”出現的大背景。一方面官方對斷裂意識形態的成功接續使得左翼思想家可以在公共平臺上發聲;另一方面,自由派對現實解釋的無力使得左翼思想更容易引起大家的共鳴。戴老師獨特的語言魅力和個人風格,以及她用電影作為切入的方式也使得這些優點被極速放大,讓她再度被大眾發現。
呈現在B站上的戴錦華是被標題黨斷章取義的,她曾與新啟蒙派論戰,試圖澄清他們妖魔化的敘述當中究竟遮蔽了什么,在這個過程中,對于不了解歷史與左翼政治光譜的人而言,呈現出來的很可能是在去蔽的同時為當下的辯護,這可能也是端的文章(《反思“戴錦華熱”:中國特色限定版女權主義》)想要批判的。
戴錦華容易吸引到青年一代,他們離六十年代與八十年代較遠,是沒有歷史包袱、容易對革命產生浪漫化想象的一代,我期待經由“戴錦華熱”所連接到的二十世紀社會主義實踐的理論資源能夠通過不同的受眾誕生出一種不同的新的社會想象。
皮卡丘
大眾傳媒是促成“戴錦華熱”的重要因素。戴老師曾在訪談中講過自己為什么會入駐B站,她入駐B站的初衷是知識共享,打破知識傳播的界限。我是北大老師,那么我的知識傳播范圍就是在北大校園,但是通過網絡可以打破學校的壁壘,讓知識傳播到其他地方去。當傳播形成一定熱度并與其他要素纏繞起來以后就會成為事件,無法受戴老師本人控制。
我覺得要理解“戴錦華熱”這個現象首先要講清的一個問題就是受眾。受眾的構成是什么?對戴錦華的批評也好、追捧也好,不同受眾的出發點以及具體的立場是什么樣的?我們今天觀察到的戴老師的主要受眾是像我們這樣的學生,但是學生這個群體在整個社會上來說,數量可能沒有那么大,其實還有其他各個階層的人都是戴老師的受眾。
我們可以試著從大眾的反響中梳理出一些基本線索,戴老師大多數的追捧者可以說是知識中產,學生其實也可以歸到這一類。作為其中的一員,我們從戴老師這里獲得了許多力量和理論資源。對其中一部分人來說戴老師只是自己的“嘴替”,你說出了我想說但不會說/不敢說的話,你批判了我想批判但不會批判的東西,對他們來說戴老師更像是一個政治性抑郁的宣泄口,他們無意于反思,只是想發泄。我覺得端那篇文章“嘴替”心態挺明顯的:一直以來我把你當“嘴替”,但是這幾年我越來越發現其實你不是我的“嘴替”,所以我對你很失望。
對戴老師的這一種接受很容易劃向一個危險的方向,戴老師很多文章和講座常常運用一種模式,通過前面一大串的分析,最后總結出一句“戴氏金句”,或者稱之為“戴氏語錄”,大家看一下每篇講座推送或者B站視頻的標題,一定會有一句非常提綱挈領、有點像雞湯的一句話。像前面提到的“做現實主義者,求不可能之事”就是典型的戴氏語錄。它本來可以起到一個指示方向的作用,但是它對沒怎么有批判精神的人來說主要起到療愈作用,最后變成了一句雞湯,形成了一種“我在反思”“我在反抗”的錯覺。它無法促使他們再去深入思考什么東西,更不用說轉化成行動。甚至“戴錦華”會成為一種象征品位的符號,比如說看戴錦華的視頻就是比看沈奕斐的視頻要有格調,仿佛看戴錦華就象征著更有思想,實際上這不過是一種精英式的啟蒙的幻覺。
國家主義者在“戴錦華熱”中同樣沒有缺席。他們主要接受的是戴老師之前談民族主義的那類視頻,戴老師說和日本學者在一起常常會忍不住變成一個民族主義者,對此國家主義者紛紛點贊,稱贊戴老師為有良心的知識分子,這個視頻也是端批的一個點。問題是首先這句話是在一個具體的語境當中,因為她面對的那些人確實很容易讓人惱火,而且戴老師在那段話后面緊接著說的就是她一直很警惕這種情緒。我們也可以看到國家主義者對戴老師的批評,比如戴老師說歷史是一種敘事,這一常識性問題被他們大批特批:如果歷史只是一種敘事,那么你是不是可以說南京大屠殺是子虛烏有,你這個臭公知。
每個人都有批評的權利,公共知識分子必須始終接受公眾的批評,戴老師堅決反對權威,她對批評是樂于接受的。但公共領域當中同樣充斥著各種惡意,就像戴老師說她不敢看網上的評論,因為她承受不了非理性的惡意。作為一名女性,戴老師面臨著許多針對女性的惡意與凝視。我們在百度搜索框中輸入“戴錦華”,搜索框下面就會出現“戴錦華結過婚嗎”“戴錦華年輕時有多漂亮”,仿佛只要是女性學者,大眾首先關注的都是她的婚姻狀況和長相,而不是思想。
來自國家主義者的批評與來自男性的凝視是公共領域隨處可見的有害垃圾,在“戴錦華熱”中不具有特殊性。端那篇文章是目前最有系統性的批評,其中的一些批評是有道理的,戴老師在很多論述上的確不夠嚴謹,在與上野的對談中戴老師的確暴露出很多問題。當然那篇文章的立場非常明顯,比如說你不能批評龍應臺和張愛玲的作品是冷戰文學(潛臺詞是龍應臺和張愛玲這樣偉大的作家是不能批評的,尤其不能從意識形態角度批評,然而即使是從純文學角度評判《秧歌》等等也很難算得上好作品),為什么要把自己標榜為張愛玲的發現者而不提夏志清的貢獻(潛臺詞是不提夏志清是出于意識形態的偏見,然而夏志清的意識形態偏見是數一數二的,避而不談普實克對夏志清的批評難道就不是意識形態偏見嗎)等等,我們可以一眼識別出背后的自由主義立場。
延維提到戴老師一直在努力重新激活毛時代的遺產,但是這些遺產是許多人,尤其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不能接受的:他們會覺得如果要繼承毛時代遺產,那么你是不是也要從文革中繼承遺產,文革有什么可繼承的?這一點確實有戴老師自己做的不夠的地方,戴老師只是提供了一個方向,具體該繼承什么、如何繼承戴老師都沒有講清楚,很多在左翼內部不言自明的問題都是需要講清楚的,這些問題最應該講清楚。我覺得這個局限性其實也和學院的身份有關,確實有很多話沒法在學術體制里說出來。為了與毛時代的批評話語區分開,學院左派必須用各種復雜的理論包裝自己的語言,這些理論對大眾來說不過是一些時髦的句子。通過電影研究來回應現實問題本身也是一件非常尷尬的事,電影研究本身只是介入現實問題的一個中介,它與現實隔了好幾層,我不是通過直接介入現實問題來回應,而是通過這個中介,必須隔一層,通過一種比較迂回的方式,然后再來回應社會問題。而且我也不是通過對社會問題的分析,而是通過解讀文本這樣一種非常曲折的方式來告訴大家,最后其實也并不是給大家一些具體的方案,而是總結出一條有一點點雞湯的語錄。
我覺得這幾年戴老師可能確實有一點轉變,世紀初戴老師親身到第三世界進行考察,我們可以感受到她非常真誠地在介入現實,感覺近幾年戴老師有些過于封閉,已經太久沒有出去看看,對現實的動向好像缺乏了解。當然我也不清楚戴老師這幾年的實踐,但如果真的把電影作為理解現實的唯一窗口,這個傾向是非常危險的。這個傾向是大部分受眾一個很大的問題,他們把理論或者文學作品作為認識世界的唯一方式,這實際上是對現實的拒絕和逃避。
白山
就“戴錦華熱”的成因而言,我覺得最重要的一點是階級矛盾變得可見、甚至是很明顯了。之前左翼思想一直在西方學界流行,中國的情況可能不太好說。有一個朋友跟我講,05、06年的時候他在讀高中,當時他跟周圍同學提“階級”的時候,他們都覺得不存在這個概念,他們都堅持認為中國的階級已經消失了。但是今天你去刷社交媒體,就會經常看到兩組數字,一個是996,一個是208。大家對于自己被剝削的現狀其實是認識得更加清楚了,然后因為一些社交媒體能夠很真實地展現有錢人的生活,所以說大家的落差感會更大,能夠更加真實地感受到階級鴻溝。再加上這兩年經濟下行,周圍很多人都處于失業狀態,所以大家會開始去懷念前三十年,或者哪怕沒到這個程度,至少會去反思新自由主義轉向,比如最近非常流行的《漫長的季節》以及里面那首以“打個響指吧”開頭的詩,勾起了大家對于改制前的體制的一些記憶和懷念,這種集體性懷念放在幾年前是難以想象的。我覺得這能夠體現出今天階級矛盾的尖銳性以及其與左翼思潮興起的聯系。
第二點是文化研究和女性主義在近些年逐漸成為了一門顯學,現在很多人會去讀這個專業,并且會在生活中關注這方面的問題。比如說對于一些文學作品,之前大家可能不會從女性主義角度來分析,但是現在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有這種視角,比如說“漫長的季節爹味”也上了熱搜。雖然我不太同意這個判斷,但是這種視角、這個詞條的出現有進步意義。我覺得隨著文化產業和女性主義在中國的發展,戴老師所做的一些研究更加和當代民眾所關心的問題相契合,這也是她出圈的一個原因。
另外想分享一件我覺得有意思的事情。前段時間我看到關于《快樂大本營》停播原因的討論中有一個熱評,說是因為21年湖南衛視的整個發展方針有一個從“快樂中國”到“青春中國”的轉向。我看到這個的時候其實覺得蠻驚訝而且激動的,因為我在19年寫論文的時候有看到過跟這個基本上是一模一樣的一個預言。它是從一些官方文件、講話和一些文學作品、文化現象中得出了“再政治化的政治”這么一個結論,就是說大家會從一個講究個體的感受和快樂的小世界、小時代,轉化到凝聚青春力量去建設波瀾壯闊的大時代。我覺得文化研究的這種對于社會現實的剖析還是很準確的。在《隱形書寫》里戴老師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話,“我們不是卡珊德拉,無法預言城邦的未來,但是面對一座幻影重重的文化鏡城,勾勒一幅文化地形圖的嘗試,無疑艱難,卻必須。這是一個文化研究者的必須。”戴老師作為文化研究領域的一個學者有很多分析,很多我在當年讀的時候可能沒有特別的感覺,但是在若干年之后再回看就會覺得好像對于這個時代把握得還蠻準確的,甚至真的有一點卡珊德拉的預言家之感。不僅僅是她一個人,還包括其他很多文化研究學者,都讓我作為讀者能夠更好得了解到自身的處境和我們所身處的這個時代。
對于“戴錦華熱”,當然也有很多需要警惕的東西,剛剛延維和皮卡丘都說了很多,包括對于革命所帶來的浪漫化的想象,或者是她的一些文本被抽離出具體的語境,僅僅變成一些金句等等。大家都說得很深入,我想補充另外一點,就是對于文化現象和文化作品的討論確實比較容易吸引普通受眾的關注,但是另一方面這也有很大的危險性。比如戴錦華老師的學生林品老師之前發了一篇文章討論粉絲文化,然后討論到了肖戰粉絲的現象,結果被肖戰粉絲辱罵和舉報了很久。我覺得大家對于你的理論分析的關注和支持,有可能是出于一些ta個人的目的,比如為了支持某個ta欣賞的文化作品,或者通過你的批判理論將某個ta不欣賞的明星指認為“特權咖”。而一旦與ta的喜好或意見相左,就可能會涌現出非理性的攻擊。換句話說,ta不一定是真正站在一個理解和批判的基礎上來關注你,文化研究的這種熱度背后也是有需要去審視和警惕的東西在。或許不能僅僅停留在文化層面,畢竟如戴老師的那個鏡子的比喻所說,文化領域是非常光怪陸離、難以找到方向的,我覺得可能還是要回歸到政治經濟學的分析以及具體的歷史語境、具體的問題當中去。
夜深人靜
關于“戴錦華熱”及其限制,我覺得視頻平臺和主體參與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戴錦華如何在B站這個平臺輸出內容,實際上導致了一種局限。正如皮卡丘說的那樣,戴錦華在B站的視頻經常是以她視頻中某種“金句”為題,去吸引眼球,這就導致人們在接受時會先通過金句去詮釋整個視頻的內容,而不是一步一步追尋視頻的內生邏輯看下去。
戴錦華評論電影時經常用一個詞叫“類型片”,某種意義上我們也可以把戴在b站上的視頻納入某些已有視頻類型當中,從而就能理解觀眾是從什么角度去“接受”戴錦華的。我覺得基本可以是這么幾種類型,一是拉片式的電影解讀,二是泛左翼up主的國外左翼運動介紹,三是B站知識區的所謂知識分享。
戴錦華需要同時迎合以至調和這三種不同類型的觀眾的口味,某種意義上就不可避免地必須收斂鋒芒,而滑向了觀眾,尤其是B站的觀眾們在看完電影拉片或者知識分享后所欲求的那種“自我充實”感。這種自我充實感就集中體現在戴錦華視頻中所謂的金句里,成為了擁抱現實的一種和解。和解降低了批評的鋒芒,但卻更為大眾所接受,這也使得戴錦華能與羅翔等人一道被列入B站所謂知識分享官的全神堂中,盡管后者的意識形態可能恰恰是戴曾經批評的對象,而戴本人對此也報以欣然接受的態度。
而另一方面,即使以一種左翼視角為基點來看戴錦華的視頻,也容易走向某種誤區,因為我們知道,戴除了她本人的官方號在B站發的電影批評以外,還有許多搬運的講課視頻,而這些視頻中的很大一部分,是有著左翼底色的全球六十年代的介紹。但這里就存在一個內容的時間性和空間性的問題,我們知道六十年代發達國家的學生造反與第三世界的反殖民斗爭,是與社會主義中國相關聯的,而且是與社會主義中國內部的斗爭相關聯的,但戴在講述前者的時候,由于平臺本身的限制,使她不可能過度牽扯到后者,于是這種聯系就變成了與空洞的、作為民族國家的“中國”這一能指發生的聯系,而中國內在的斗爭與世界相聯系的豐富性在這里就被省略掉了,并且這種空洞的中國就能被無裂隙的順延到當下的中國,因而很容易被國家主義者做出有利于自己的解讀。而那些因為戴老師講這些所以對她比較欣賞的“共趣”們,也在這兩年完成了從刷屏國際歌到要么“唉,資本”要么波波meme的蛻變,在這種情況下,所謂戴錦華熱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有用的,可能需要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
左翼思想系譜中的戴錦華
夜深人靜
戴錦華的思想歷程和我們歸結為新左派的那一代許多知識分子,比如汪暉和甘陽等人非常像,他們都算是曾經參與過社會運動。所以我們可以發現,雖然說今天新左派具有強烈的國家主義傾向,但是當比如戴錦華、汪暉提及八十年代末時,他們并不會像護黨主義老左一樣,認為這就是全盤西化,這就是顏色革命,而是將之視作一場因初步的改革出現大規模社會分化而發生的具有社會保護或者社會自救色彩的運動,這個面向在后來的自由派歷史敘事中很少會有提及。
到了九十年代,伴隨激進市場化而來的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分化,新啟蒙的英雄們召喚的大眾文化在市場化的推動下變成了現實,但這個時代,這個同時也存在許多問題的時代恰恰又不需要這些知識分子,不需要他們再居高臨下地指點社會,(當然我們可以發現這種“社會”或者說初生的“市民社會”大多由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構成,他們當然不會允許知識分子對社會問題提出質疑,即使這些知識分子壓根不反對改革)知識分子將這個現象稱為人文精神的失落,其實也就是知識分子面對如何定位自己角色的問題,他們不能明白背后的政治經濟動向,而只能借著新啟蒙的語言將之視作人文精神的失落,舊有的語言制約了對新現象的討論,所以這個所謂的“人文精神大討論”最終也無疾而終了。
后來就是新左派與自由派的論戰。戴肯定是屬于新左派這一陣營,但我覺得,這里值得研究的是,戴為什么會成為一個新左派?因為從運動場上退下,并不意味著一定會成為左。我個人一個想法是,戴錦華在八十年代對中國現代文學所做的女性主義批評,也就是那本《浮出歷史表面》和其他一些電影批評,在戴錦華到達美國訪學之后,獲得了文化研究這樣一個命名。我們知道文化研究在歐美屬于左派文化政治的范疇,在這樣一種左派命名之下,做文化研究的自覺讓戴錦華能意識到自己是,或者說應該是一個左派。
還有一個重要的事件,跟之前所講的國家主義與民族主義也有關,就是在世紀之交的時候,我們現在認知或者當時認知的許多左派知識分子,比如溫鐵軍、劉健芝,比如索颯和張承志,都去美洲尤其是拉丁美洲進行過考察,而戴錦華也在這一行列之中,我認為這些人左轉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對拉丁美洲的考察,或者叫“發現第三世界”。一方面,他們在第三世界對于以美國為代表的抗爭話語,比如世界體系理論或者依附理論中獲得了新的思想資源。而我們知道,在入世前夕的中國,其出口導向型的經濟結構實際上非常依賴于美國,而這也讓這些知識分子從現實上選擇將中國“誤認”為像拉美等第三世界一樣,處于美國的依附性地位,而這種對美國及與美國所代表的全球化市場霸權的反對,事實上也是新左派論戰中對抗以美國保守自由主義為圭臬的徐友漁、朱學勤、劉軍寧等人所需要的。而另一方面,當戴錦華他們在拉丁美洲親眼見證到薩帕塔起義或者巴西無地農民抗爭這樣的事件時,事實上也喚醒了他們對于格瓦拉,對于卡斯特羅,對于六十年代的第三世界抗爭,以及對于那時的社會主義中國的一種記憶,這種記憶以及與第三世界產生的“想象性連結”,使他們能有在一個以全球化市場化為歷史終結的時代,再度去尋找另類現代化這樣一種可能的變革的信心,這對九十年代末的中國批判知識分子來說,是極為重要的。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這些人會有一種民族情結,就像戴錦華被端傳媒批評為民族主義、國家主義一樣。但這種所謂的左翼民族主義,在90年代是有它的思想史基礎的。比如九十年代末孫歌等人在《讀書》上所倡導的東亞知識共同體,討論東亞的戰爭經驗,責任與記憶,以及其他的東亞共同感受,也是在跟東亞進行一種區域性連結以對抗全球性的知識霸權,而戴錦華做文化研究本身也是呼應整個東亞知識界文化研究轉向的一個事情。這樣一個區域性的連結,其實恰恰是從九十年代末的民族主義里生發出來的,因而我并不贊成那種將民族主義強加在一切歷史階段的知識之上,以為如此就能盡到批評的責任的做法,而是要細致去探討到底一種思想乃至一種民族主義所誕生的思想史基礎到底是什么。
當然我們知道,在2006年左右,這批新左派出現了大規模的國家主義轉向,開始稱贊起所謂的“中國模式”乃至被收編到今日,去吹鼓所謂的“中國式現代化”,某種意義上這代表著九十年代末新左派批評的盡頭,他們的反全球化面向被建制收編為單調的反美面向,而缺少對自身參與其中的世界體系的自我批判。但戴錦華在其中仍然是非常特殊的存在,她沒有完全被官方收編,而是仍對民族主義進行著批評,這也使她能將新左派論戰中那種更為可貴的對時代政治經濟的左翼批判態度留存到今日,以便我們對其進行爬梳與分析,再度養成對今日之中國的一種批判的眼光,乃至更進一步地“指歸在動作”,我想,這便是戴錦華的思想史意義所在了。
「 支持烏有之鄉!」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