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 馮友蘭“晚年之惑”釋謎
(《經濟思想史研究》2022年第五輯P66-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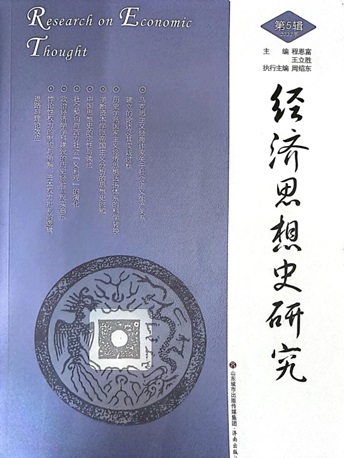
概要馮友蘭一生學術,思想興起是《中國哲學史》,思想之用是《中國哲學史新編》,思想之根是貞元六書中創立的新理學(新形上學)哲學體系。“新理學”是運用邏輯分析方法建構“正的方法”(主客二分的邏輯學)和“負的方法”(主客同一或不分的邏輯學)哲學認識論的過程,有一組形而上學的命題,其首要命題曰:有物(實際)必有理(真際)。“他的邏輯分析方法的哲學實質在于:以‘如果——則’的蘊涵關系剪裁存在與思維、個別與一般、部分與整體、相對與絕對之間的辯證關系,從而導引出‘真際’‘理’‘道體’‘氣’等一系列形上學的觀念,力圖證明新理學的形上學能夠成立。”由于馮友蘭堅持以西方邏輯學解說和貫通中國,“他采用的邏輯分析方法,實則是一種知性的思維方法。”由此認為,“所謂‘負的方法’就是中國哲學中常常采用的直覺主義的方法……許多中國哲學家沒有從正的方法講形上學,但不等于他們沒有自己的形上學,也不等于他們不關心形上學,只是他們不喜歡從‘主客二分’的視角出發,去講那種知識形態的形上學。他們采取主客不分的哲學思考方式,把形上學看成主客同一的基礎,而不視為主體認知的對象或客體。”然則,“道家和儒家都不主張從正面講形上學”,是因為“按照中國哲學家的看法,主體亦在形上學的范圍之中,因而無法把形上學對象化。從這個意義上說,人實在不能把形上學當成言說的對象,只能當成直覺或體驗的對象,故而形上學不能講。”【注:宋志明,梅良勇.馮友蘭評傳[M].中國青年出版社,2016, 140-142.】
對象I(主觀,客觀)如何向對象II(主體,客體)轉化是馮友蘭一生求索卻總也無法解決的學術難題。這其實不是學術難題,而是歷史道路難題——歷史唯物主義的中西分殊的認識論難題。如果存在“仇必仇到底”,則“仇必和而解”是假命題;而若“仇必和而解”為真,則“仇必仇到底”是假命題。這是真假命題之戰,亦是大前提之爭。所謂“極高明而道中庸”是中華辯證法,而馮友蘭用在此處,是同樣當作了哲學認識論,而欲否決哲學路線的斗爭原則(仇必仇到底),轉而支持它的對立面——統一原則(仇必和而解)。從形式邏輯出發,使馮友蘭寧可相信統一路線而摒棄斗爭路線,所謂:“中道亦即是庸道。程子說:‘庸道,天下之定理。’定理者,即一定不可移之理也。所謂公式公律等,都是一定不可移之理,都是定理。康德說:凡是道德的行為,都是可以成為公律的行為。例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行為,是可以成為公律的。若果社會上各個人都如此行,則社會上自然沒有沖突。”【注:馮友蘭.三松堂全集.第4卷[M].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394.】
由于秉持形而上學的“理在先”,馮友蘭先生固執地認為:“客觀辯證法的兩個對立面矛盾統一的局面,就是一個‘和’。兩個對立面矛盾斗爭,當然不是‘同’,而是‘異’;但卻同處于一個統一體中,這又是‘和’。”然則,“‘仇必和而解’是客觀的辯證法。”【注:馮友蘭.三松堂全集.第10卷[M].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657.】
馮友蘭認為他的中國哲學思想史研究是用清晰的歐洲思維邏輯來闡明中國對象的,依據這個路徑,導致他以一般和特殊的邏輯學詮釋共相和殊相的相互關系。亦即,“這里所討論的,正是一般和特殊的關系問題……關于一般和特殊的關系的正確的說法,是一般寓于特殊之中;寓于特殊之中的一般,就是這一類特殊的義理之性。實際上,沒有不寓于特殊之中的一般,也沒有不在氣稟之中的義理之性。”【注:馮友蘭.三松堂全集.第10卷[M].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629.】
繼而,“馮友蘭主張共相先個體而‘潛存’,認為未有飛機已有飛機之理。金岳霖對于這個問題作了進一步的分析,指出:共相是現實的,現實必然個體化,而共相又不是一個一個的個體。一個一個的個體是殊相,殊相必然在時間空間中占有一定的位置。共相不是殊相,不在時間空間中占有一定的位置,它超越殊相和時空。”【注:馮友蘭.三松堂全集.第4卷[M].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204.】
由于馮友蘭的“共相”脫離道路和共同體并且刻意使之抽象化,“這種‘共相先于殊相’的看法,也是一種客觀唯心主義學說。”【注:宋志明,梅良勇.馮友蘭評傳[M].中國青年出版社,2016, 128.】
所謂從“我們要西洋化”到“我們要近代化或現代化”:“這并不是專是名詞上改變,這表示近來人的一種見解上的改變。這表示,一般人漸已覺得以前所謂西洋文化之所以是優越的,并不是因為它是西洋的,而是因為它是近代的或現代的……照此方向以改變我們的文化,則此改變是全盤的。因為照此方向以改變我們的文化,即是將我們的文化自一類轉入另一類。就此一類說,此改變是完全的、徹底的,所以亦是全盤的。”“所以中國雖自一種文化變為另一種文化,而仍不失其為中國,仍是行中國先圣之道。康有為之說,其一半為我們所不以為然,但其一半卻是我們所贊同者。”【注:馮友蘭.三松堂全集.第4卷[M].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205-207.】
“‘新理學’作為一個哲學體系,其根本的失誤,在于沒有分別清楚‘有’與‘存在’的區別。馮友蘭一方面贊成金岳霖的提法,說理是不存在而有;一方面又隨同當時西方的新實在論的說法,承認‘有’也是一種存在。”唯名論以“共相”為空名,概念論則以之為一個概念,追隨新實在論者,“馮友蘭贊成‘不存在而有’的提法,另一方面也用所謂‘潛存’的說法,這就是認為共相是‘不存在而有’,同時又承認‘有’也是一種存在。這是新理學的一個大矛盾。”【注:馮友蘭.三松堂全集.第10卷[M].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632.】
關于毛澤東的《矛盾論》,馮友蘭先生談到:“其中接觸到兩個真正的哲學問題:其一是兩個對立面的統一和斗爭的問題,其二是一般與特殊、共相和殊相的關系的問題。”【注:馮友蘭.三松堂全集.第10卷[M].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594.】
這里說明了“客觀辯證法”的過程轉化意義:“客觀的辯證法有兩個主要范疇:一個是統一,一個斗爭。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思想認為,矛盾斗爭是絕對的,無條件的;統一是相對的,有條件的。這是把矛盾斗爭放在第一位。”同時,“客觀的辯證法只有一個,但人們對于客觀辯證法的認識,可以因條件的不同而有差別……中國古典哲學沒有這樣說,而是把統一放在第一位。”即是說,“一個統一體的對立面,必須先是一個統一體,然后才成為兩個對立面。”不過,“這個‘先’是邏輯上的先,不是時間上的先。用邏輯的話說,一個統一體的兩個對立面,含蘊它們的統一性,而不含蘊它們的斗爭性。”馮友蘭最后強調:“顯而易見,‘仇必和而解’的思想,是要維持兩個對立面所處的那個統一體。”“理論上的這點差別,在實踐上有重大的意義。”【注:馮友蘭.三松堂全集.第10卷[M].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654-655.】
馮友蘭先生運用自己的理解,這導致他認為,“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這就是把一般和特殊相結合,以此領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由此生出“《矛盾論》的兩個要點”:(1)“對于一般和特殊的問題,毛澤東歸結為一般寓于特殊之中。一個‘寓’字,準確地說明了一般和特殊、共相和殊相既有區別、又有聯結的情況。這個提法,中國傳統哲學稱為‘理在事中’。”(2)“對于兩個對立面統一斗爭的問題,毛澤東歸結為:‘新陳代謝、除舊布新或推陳出新’。”【注:馮友蘭.三松堂全集.第10卷[M].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597.】
通過以上處置,馮友蘭在認識上借由“矛盾論”將共相、殊相問題進一步引導到“正——反——合”的探究路徑,——這表示其走出形式邏輯的一個歷史分析的努力。依照馮友蘭的理路,“仇必和而解”依舊可以是前提規定,不過在這里,是作為否定對象的“肯定(前提)”。否定發展環節當然是“仇必仇到底”,這是哲學路線的斗爭原則對共同體的主體進化原則的“邏輯否定”,也是基于知識生產原則的對象II之于對象I(統一原則)的工作置換。合的邏輯關系問題的真實道路景象是“歷史轉化運動”:對象I-研究對象-對象II(現代意義的“極高明”“道中庸”),——哲學認識論斗爭路線I向路線II轉化的認識圖景(馬克思主義知識論)正是由該種歷史運動所主持的規定。可見,統一“斗爭原則”和“統一原則”的不是別的,正是矛盾(生成)運動的“轉化原則”;由主體啟動知識決定了“階級論”規定對“主體論-知識論”思想有機構成的知識鏈條的工作嵌入關系。肯定是矛盾統一體的確立,否定才是對統一體的破壞和瓦解,否定之否定則是重建新的統一體。然則,釋謎之路沿著以下路徑進行:主體論的對象I(客觀,主觀)——研究對象(主體論與知識論的中介:蘊涵階級史觀的知識客體)——知識論的對象II(客體,主體)。
原理具寫于下圖。

圖1 中國思想史的定性與讀法
圖1展示了“對象I-研究對象-對象II”路徑下哲學認識論之“仇必和而解”(思想路線I)與“仇必仇到底”(思想路線II)的運動轉化及思想共構。這個總構圖以簡潔的線條勾勒出思想路線斗爭的發生機理及其作用機制。客觀生主觀、主觀克客觀,言主體觀(或曰“生產方式的主體表達”)的必然性矛盾規定,于是,主體的斗爭哲學必然定格為在客觀主義與主觀主義之間形成的思想路線斗爭;客體生主體、主體克客體,言知識觀(或曰“生產方式的知識表達”)在構成上的必然性矛盾規定,于是,知識的斗爭哲學又必然定格為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之間的思想路線斗爭。“就張載當時說,它是要維持中國封建社會那個統一體。”【注:馮友蘭.三松堂全集.第10卷[M].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654-655.】
誠如馮友蘭提示,客觀主義與主觀主義的思想路線斗爭是歷史轉化運動之始,天人合一蓋求思維、存在同一之命題,此為理一;唯物論與唯心論的知識之辯謂為分殊,由于理氣統一謂為“理一分殊”,分殊便是理的知識統治手段。“嚴復曾批評‘中體西用’造成了‘體用割裂’”,“嚴復此處是就其作為辯證法的架構規定而論的;換言之,嚴復欲強調的是中學之辯證法與西學之辯證法的合璧。”但不可否認,中國社會“在‘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的共同體主義論證思路的求索上用功較多”,顯然,是有關于“主體社會理論的探索(如‘皇帝制’-‘官僚制’-‘官僚制的瓦解’)”,然則其“作為中華思維學體系和路徑的學科求索,就可能免除由于西學術語或論斷方面產生的種種抵悟情形所帶來的理解上的語義沖突。”【注:許光偉.中國經濟學行動議程與方法論命題——中華思維學的進展及其創造性轉化[J].武漢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2), 207-216.】
這是“知識改良派”的情形:以主體進化觀推動階級之社會進化,是為思想路線I的斗爭產物。“思想路線I→思想路線II”意味著思想共相對思想共生之轉化,而有了獨立化的革命知識生產。“主體-社會”→“主體-客體”→“主體-階級”→“主體-知識”,于是這里,一旦引入主觀史對客觀史的轉化運動的“反映論”,唯物論與唯心論之間乃至客觀與主觀之間的搖擺型的思想切換現象即立刻被根除。一系列的轉化運動構成母子-體用的兩重路徑和結構,由階級史觀的客觀工具(思想有機構成I和思想有機構成II)的工作聯合關系予以統一。馬克思主義知識規定定格于“兩重轉化”歷史成長區間之內,作為轉化運動結合產物的歷史思想形式。
「 支持烏有之鄉!」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