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鐘雪萍,美國塔夫茨大學教授兼中文部主任,旅美學者,著有《Masculinity Besieged》、《Mainstream Culture Refocused》;研究范圍包括:(中西)文學和文化批評理論與思想史,(中西)文化研究及其歷史,(中西)女性主義理論和批評及其歷史,
在會議議程上,我發言的題目是“為什么反思‘革命與婦女解放’成了女性的專業”。我先說一下這個題目。
2005年我在《讀書》雜志上發過一篇文章,題為《后婦女解放與自我想象》。提交時的題目是《后婦女解放與男性知識分子的自我想象》,刊出時“男性知識分子”被去掉。盡管如此,我當時的考慮仍是源于對一個現象的好奇,即,中國現代史上,有不少男性知識分子和革命者呼吁婦女解放;不但如此,婦女解放更是作為重要的綱領目標之一,存在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訴求和實踐當中。但是,改革開放以后,在研究領域,“男同志能干的,女同志也能干”這類集體化時期男女平等話語被質疑,在男性知識分子的視野中更是很快地被弱化了。20世紀80年代出現的女性研究、90年代出現的性別研究,都伴隨著一個男女分化的過程,即,“女性研究”和“性別研究”主要成為女性學者的研究領域。我當時感到好奇:如何理解這個變化?男性知識分子的撤出是女性主義的勝利嗎?
十幾年過去了,盡管這個現象依然存在,我自己的認識卻發生了一些變化。
2016年,在上海大學召開的“社會主義女性主義:歷史與現狀”討論會上,我發言的題目是《重溫中國婦女解放的階級性》。今天發言的題目其實是那個話題的繼續。中國婦女解放的成功與其鮮明的階級性直接相關,而這一關系直接來自于中國革命的性質本身。
剛才應星教授在發言中說,20世紀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不同性質的革命,一次革命,二次革命,要聯系起來看。這確實很重要。當然,最終成功的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表現在它帶來的民族獨立和中國社會飛躍性的變革。對中國婦女解放的認識,關鍵在于對20世紀中國革命的全面認識,更在于對社會主義革命的認識。
我在這里提到的“革命”特指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在此前提下對婦女解放與中國革命之間的關系進行延伸思考,并對改革開放語境中出現的“性別話語”進行反思。
近年來,在國內學界,對中國革命——包括其在中國和世界歷史中的重要意義以及認識這些重要意義的當下性等等——出現了很多頗具新意的思考。比如蔡翔的《革命/敘述》,2010年在國內出版時引發了很多反響。這樣的研究和思考無論在國內還是在海外中國學學界都很少見,不僅打破了一直以來的對“十七年文學”要么丑化、要么擱置、要么簡單描述的局面,更重要的是,通過對其“敘述特性”的深層次剖析,作者提出了一系列理解中國革命的新思路,包括如何理解中國革命的現代性、文化建構與社會改造的關系、革命后面臨的危機,等等。我和紐約大學歷史系的瑞貝卡·卡爾(Rebecca Karl)教授合作翻譯了這本書。英文版本2016年出版時,引發了不小的反響。當然有很多并不愿意正面認識中國革命的人,在學者中也大有人在,而且男女都有。但是,只要是稍微愿意正視中國革命在世界歷史中意義的人,就會承認國內學者在這方面所取得的突破。我們作為譯者所感受到的反應,就證明了這一點。
在蔡翔的討論中,“革命/敘述”不可避免地包含對中國革命與婦女問題和性別問題的思考。我提《革命/敘述》這本書,是想說,其實無論男女,認真研究中國革命的學者,是不能不意識和認識到婦女解放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意義的,因為在中國革命帶來社會飛躍性變革的同時,其解放勞苦大眾的綱領,無論遺留多少問題和遺憾,給廣大勞動婦女帶來的變化是結構性的,無論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層面上還是在個人層面上,既具有社會主義革命的特征,又同時在全方位的變革上一直面對深層次的挑戰。對婦女解放的訴求和實踐與中國革命的特質直接相關,一方面婦女解放因此得以成為中國革命的重大成功之一,另一方面也顯示出革命所面臨的各種挑戰,包括倒退的挑戰。二者互為歷史關系,互為政治關系,互為辯證關系,其中共同的內在基礎,是對社會結構變革和重建的目標以及主體變革和重建的訴求。
在海外中國學學界,盡管真正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上、高屋建瓴地認識中國革命尤其是中國革命的世界史意義的,仍屬鳳毛麟角,但相對左翼的學者,無論是否真正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上,也無論是同情還是反對中國革命,一般認可革命的現代性意義以及中國革命在中國現代歷史中對改變中國所起的重大作用。
所以,再次強調,我今天發言題目中提出的問題,并不是想停留在男/女的問題上,而只是從這個(繼續存在的)現象進入,提出一些想法。希望大家批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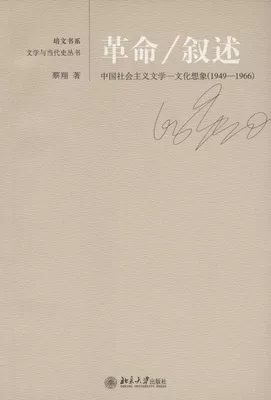
《革命/敘述:中國社會主義文學-文化想象(1949-1966)》
作者:蔡翔
北京大學出版社
我先從兩個(男性作者的)文本進入。
一個是魯迅的《娜拉走后怎樣》。熟悉它的人都知道,那是魯迅1923年在北京高等女子師范學校的演講。五四運動提出個人解放、女性解放,走出家庭。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介紹到中國以后,在當時文藝青年中流傳頗廣。娜拉的出走被看作“現代女性”的覺醒。魯迅則看得更為透徹,他認為娜拉出走以后只有兩條路,不是回家,就是出賣自己的身體,別無其他選擇。他在《傷逝》中,給子君安排的就是回家以及之后的死亡。魯迅考慮的問題是,個體覺醒后會怎樣?在當時的中國社會沒有發生根本性變革的情況下,個體面對的必然就是那個社會結構的邏輯,而這一邏輯必然繼續殃及即使是“覺醒了”的個體。
縱觀魯迅的其他小說和文章,我們知道,魯迅并不認為這只是那些覺醒后的女性所面對的命運。魯迅不斷指向的是社會本身(鐵屋子)需要變革的問題。魯迅當然不可能知道后來的革命具體發展成怎樣,如今有很多人認為假如他活得更長,也許他自己會被他所期待的社會變革所吞噬,但是,歷史畢竟是不能基于假設的(盡管假設可以成為歷史學家們的學術游戲)。無論人們如何假設魯迅本人會怎樣,中國的革命歷史證明,魯迅的拷問是對的。從魯迅的其他作品中,我們還可以讀出,魯迅所關心的,遠非只是類似“娜拉”或“子君”這樣的中產階級/小知識分子女性,他關心的還有“祥林嫂”“閏土”甚至“阿Q”,那些更為底層且處于散沙一片的大眾。盡管人們認為魯迅透過這些人物把批判的目光聚焦在傳統文化上,但是,如果全方位地認識和理解魯迅的話,可以說他從來都不是簡單的“文化主義者”,他對文化現象的拷問是對社會本身的拷問,是一種疾呼社會要變革的拷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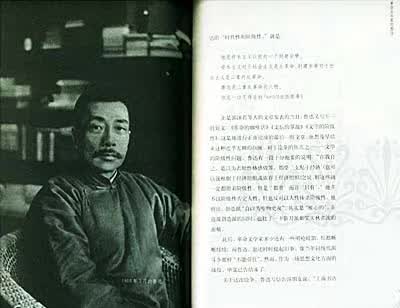
另外一個文本,來自20世紀80年代:1983年出品的電影《黃土地》。相隔上述魯迅的演講整整60年。不知道大家是否看過這部電影,因為教學的原因,我看過幾十遍。作為電影,《黃土地》確實是一部經典。據說1983年在中國大陸上映時,它根本沒有票房。同當時許多頗受歡迎的其他電影相比,這部被認為是“第五代導演”首次亮相的代表作,在國內基本沒有票房可言,也沒有引起當時文化界的關注。1984年在香港上映時,才在那里的文化精英中引發轟動,被認為中國總算出現了值得“國際社會”觀看和認可的電影。隨之而來的,是西方學界對《黃土地》的關注,出現了一些學術性的討論,聚焦影片看似表現“革命”實則質疑革命的象征手法和象征意義。有意思的是,當時中國的文化主流被“傷痕文學”引領著,沉浸在對“文革”的控訴當中;而這部大多數人覺得“不好看”的電影卻被悄然置入質疑中國革命本身的歷史語境中。
影片的故事很簡單,時間1939年,地點黃土高原(革命歷史上的陜甘寧邊區),只有四個人物:一位收集民歌的八路軍戰士(顧大哥)、翠巧、憨憨(翠巧的弟弟)以及翠巧和憨憨的父親,片段性地講述顧大哥作為八路軍的文化工作人員,因收集民歌,借住在這個貧窮農民的三口之家,與他們之間的交流。在這部高度象征化的影片里,戰士代表革命及其動員力量,翠巧和憨憨代表可以被動員的群眾力量(尤其是年輕男女),他們的父親則代表傳統文化及其頑固的存在和影響。影片中,“革命的啟蒙”最成功的對象是翠巧。當她得知父親為還債而仍然要將她嫁人時,嘗試著請求顧大哥帶她加入八路軍,卻被不知情的顧大哥婉拒,說是要領導先批準。她被迫出嫁以后,決定逃跑,跟弟弟說要到河對岸找八路軍。當弟弟讓她等到河水不再湍急再過河時,翠巧對憨憨說“姐苦啊,姐等不了了”。于是,翠巧一邊唱著顧大哥教給他們的革命歌曲,一邊向對岸劃去。但是,當她唱到“救人民來了共產黨”時,那個“黨”字沒有唱出,即刻被湍急的河流聲代替,隨之而來的是站在岸邊的憨憨大聲喊出的“姐……”
在這個敘述里,翠巧的故事(也包括憨憨的)可以跟魯迅的演講(和小說)做一個(逆向)“互文”解讀。在翠巧身上,也發生了一種“覺醒后”的出走;因為是發生在中國革命的歷史框架里,她的出走象征革命對貧苦農民大眾動員之后女性的“覺醒”和決定。但是,出走后的翠巧命運如何?影片似乎直接給出了答案:死亡,而且是唱著那首跟顧大哥學的革命歌曲,跟沒有唱出的“黨”字一起消失。如何理解這個處理?20世紀80年代,不少海外學者按著當時對中國婦女解放提出質疑的思路,認為影片就是中國人自己對中國革命和婦女解放的質疑:中國革命似乎并沒有給中國婦女帶來什么變化,她們不是繼續面對傳統就是面對反抗帶來的死亡。

電影《黃土地》海報
通過對這兩個文本的“逆向”互文,我們可以看出,在質疑“革命”的歷史語境中,婦女解放的發生,它的革命性,或者說在社會變革層面上的意義,被擱置被遮蔽(如果不是被完全否定的話)。這自然跟這一語境自身特有的話語邏輯有關,與知識分子的“現代話語”的回歸有關。這是我下面討論的重點。
《黃土地》代表的是20世紀80年代的“文化熱”,以及內涵其中的“告別革命”的走向。這一走向經由把革命與“傳統”相勾連,進而否定革命的現代性,在邏輯上通向1986年出品的《河殤》以及所謂的回歸五四重新啟蒙。于是,“革命”等同于“傳統”,“西方”等同于“現代”。
與“革命是非現代甚至是反現代的”話語邏輯合拍的,是一種對“普世現代”的想象,一種基于自由主義的“告別革命”的話語。聯系到“婦女問題”,就是如何解釋中國的婦女解放。至少在20世紀80年代,關于婦女解放的話語,很快被“回歸中心”的精英知識分子占領,經由將革命定性為“傳統文化”而受到質疑甚至否定。
比如,20世紀80年代后半期,在張藝謀的影片里,那些鞏俐扮演的女性角色。有批評者指出,張藝謀最初導演的“三部曲”(《紅高粱》《菊豆》《大紅燈籠高高掛》)有“自我東方主義”傾向,即,按照西方對中國文化的刻板印象呈現中國,從而強化西方的“東方主義”(即,西方中心)文化邏輯。但是,批評者少有提到的,恰恰是這些影片中同時隱喻著的“去革命”的話語,即,無視革命對中國社會帶來的巨大變革,把也許無法通過一次性革命而全然改變的文化問題,看作革命本身,予以否定。值得一提的是,這類通過表現女性質疑革命的隱喻手法,在80年代的男性文人——作家、導演、學者——筆下和鏡頭里似乎比比皆是。類似翠巧、菊豆、“四太太”(《大紅燈籠高高掛》)等被“傳統”摧殘的女性,外加各種“馬列主義老太太”形象,共同表示出一種“不到位的現代”,頗為巧妙地把“婦女解放”庸俗化、去現代化,因而不值得呼吁回歸五四的知識分子待見。
進而言之,如果“回歸五四”走向的不是魯迅,而是“于永澤”一類,那么這一走向勢必首先質疑來自“林道靜”的挑戰,質疑她對革命和所謂“自由”兩者之間的選擇。

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
對婦女解放和革命的另一種質疑,來自西方學界包括女性主義學者。
20世紀80年代初,一些后來頗有影響的專著,定性中國的婦女解放不是“被推遲”就是“沒有完成”。那么是不是這樣的?如果是這樣的應該怎么解釋?對各種解釋中存在的問題應該如何回應?其實國內已經有不少回應,基調是,對,確實仍然存在問題,需要反思,尤其是對革命中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存在的不足應予以反思。但是,在虛心接受的同時,如果要進一步思考,應該跟中國革命重新做進一步的勾連,在重新認清中國革命性質的基礎上,再做反思。近年來,王玲珍教授對西方女性主義的“冷戰”背景的分析和批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思考。
我想補充的是,也許其中纏繞的不只是“冷戰話語”中形成的“西方”/“中國”思維定式,還反映出自由女權主義無法真正處理的“階級”問題,包括中國革命和婦女解放的階級性。
其實,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個問題相對無意識地也反映在80年代出現的中國女性知識分子(包括女作家和女學者)重點關心的“女性特質”問題上,認為婦女解放對男女平等的強調弱化了女性的“特質”和“異質”,糾結于“男女相同”還是“男女不同”等問題。在當時的語境中,這些質疑有它的道理,而且應該還是在接受婦女解放的前提之下提出的。她們的質疑指出革命話語中對兩性關系和性別歧視的認識存在盲點,在與革命的大綱領緊密相關的一些小綱領及其實踐中存在盲區和問題。對這些盲區和問題,女性主義的性別話語確實有打開批評視角的重要作用。
但是,今天回過頭去看,需要重新認識的恰恰包括對西方女性主義批評接受層面上的歷史語境:在“告別革命”的邏輯影響下,從“婦女”到“女性”多少有點類似西方70年代、80年代出現的“女性主義跟馬克思主義離婚”的走向。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個走向助長——我不是給男學者一個借口——性別研究本身性別化的現象,也助長“女性”被認為具有“普遍”內涵,而“婦女”則因其特定的政治內涵被特定化、邊緣化(甚至丑化)。
進而言之,所謂“后婦女解放”的“后”,其特征之一,是“女性”這個相對去政治內涵的字眼的主流化。而其中自由主義(亦或資產階級)的“原子個體”這一核心內涵,往往因為“社會性別”這一概念強調社會建構,一并被接受為普世的權利觀。如此,這一變化成功地為接受自由主義女性主義打開了認知層面上的綠燈,但對中國婦女解放本身的結構性意義,并不能提供革命現代和世界史意義上的認識。
指出問題后,在這里,我想回到“重溫婦女解放的階級性”這個話題,經由這個角度強調中國革命的性質及其婦女解放的目標和實踐,至少有三個方面值得強調。
第一,林春關于中國革命的“階級性”的討論以及革命中國的“國家階級性質”的討論,值得一提。在她2013年出版的《中國與全球資本主義:馬克思主義、歷史和當代政治》(China and Global Capitalism: Reflections on Marxism, History, and Contemporary Politics)專著里,以及即將出版的一篇文章里,林春比較深入地探討了從國家有沒有階級性這個問題出發認識中國革命的性質及其世界史意義。在資本主義以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形式向世界擴張的歷史中,中國在當時那樣的世界范圍內,作為一個被壓迫的國家,它的這個地位的階級性跟中國革命的訴求勾連起來,才能既理解中國革命的正當性、合法性,也能理解為什么革命的終極目標和具體實踐在于,既通過武裝斗爭奪取政權來解放中國的勞苦大眾,也通過建立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國家來解放中國的勞苦大眾。
第二,婦女解放與解放勞苦大眾相關,其階級性取決于中國革命自身的階級性。在這個大前提下,進一步思考和認識內在于中國革命的婦女解放與革命的大綱領和小綱領之間的各種關系,所謂“性別視角”才可能提供積極的批評和反思。剛才應星教授說,近年來對革命的研究中,存在注意材料的收集但同時又具有碎片化傾向,實證研究關注樹木,但樹林本身是怎么回事兒卻不太關注。我在想,其實有些實證研究本身其實已經是主題先行,用看似新鮮的材料論證并不那么新鮮的觀點。對婦女解放的研究中,是否也有這樣的問題?就婦女解放跟中國革命的大綱領和它經常變化的各個時期的小綱領之間的關系而言,我發現,對小綱領之間的關系勾連比較多,但是對大綱領——也就是說到底是怎么樣一場革命——的勾連似乎欠缺。
應該指出,20世紀中國發生的幾次革命到底還是不同的。辛亥革命、國民革命、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后來的社會主義革命,它們到底有一些什么樣的根本不同或者說相同的地方,就是說,它的“同”應該怎么去理解,“不同”又應該怎樣理解,婦女解放的實踐跟這一切又是怎樣的關系,等等。這些方面的認識都很重要。要在結構層面上,而不只是停留在個人經歷和經驗層面上,做一個比較清晰的認識。我覺得它們的“不同”就在于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所強調的階級特征:解放勞苦大眾,建立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國家。盡管在多年“去革命”的話語影響下,這一點在不少人群中會被認為只是教條的說法、過時了的說法,但這種說法無法否定的仍然是革命本身的階級特征,包括婦女解放本身的階級特征。
第三,從“女性”到“婦女”,再從“婦女”到“女性”,“階級性”內涵的變化。關于“女性”和“婦女”這兩個詞,已經有不少學術論說。但是探討其中階級性的,似乎不是很主流的研究。但是,在20世紀的中國,對這兩個詞接受的變化以及其中的思考,與革命的特質以及對這一特質的認識本身直接相關。
如果回到魯迅,前面也提到了,他所關注的問題,不只是如娜拉和子君那些中產階級或者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女性。今天,我們看他寫的很多東西,發現他的思考對當下仍然有關聯、有意義。他對女性的命運和中國社會的認識,關注的是對結構性問題的思考:只有改變中國,改變社會,才能改變性別不平等,改變廣大婦女受壓迫的現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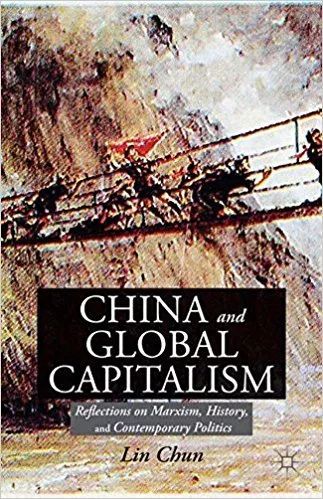
安東尼奧·葛蘭西的著作,《獄中札記》
《中國與全球資本主義:馬克思主義、歷史和當代政治》
林春 著
在過去的幾十年里,已經有過很多關于“婦女”和“女性”有什么不同的討論。盡管在這里無法展開,但是我在想,如果把這兩個詞的用法和對它們的爭論和討論放進具體的歷史語境里,它們本身的階級內涵應該是很明顯的。中國革命強調“婦女”在于其自身的階級性;改革開放以后,“女性”的回歸,看似回歸“五四”,實際是沒有了五四時期“女性”這個字眼的革命性。社會主義時期的婦女“走出家庭”“走上工作崗位”,確實并非源自女性群體和個體的抗爭,并且因為它的所謂自上而下的即所謂“國家女性主義”特征,而被很多自由女權主義者詬病為被動的、工具性的(被國家利用的),而非“真正個體解放”的解放。這種觀點在國內被很多人接受。但是,其中存在“個體為上”和工具主義的邏輯,基本無視婦女解放的階級性,即,對勞動婦女帶來的解放。也無法解釋為什么在社會主義時期,不同階層的婦女“走出家庭”以后,面對的不會再是魯迅指出的兩種“選擇”;為什么中國革命帶來的社會變革,給廣大勞動婦女帶來的不僅僅只是有了工作機會,而且是參與社會和主體改造的意識和機會;為什么前所未有的社會變革才是個體解放的大前提;等等。
盡管變革中仍然存在很多問題和不足,而且還會出現倒退,但就像前面已經提到過的,如果只用“女性”“性別”這些字眼,只是從“性別政治”的角度出發,去理解婦女解放的革命性,產生不出足夠有力的分析。原因之一在于“女性”這個詞本身的局限性:“她”與自由主義的“原子個體”同源,盡管承認社會建構性,但以“普遍人性”為前提,將“性別”等同于男性/女性之別,而其想象所基于的“男”和“女”,則無法超越作為主要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自由主義本身的想象范圍。
正因如此,在我看來,西方自由女性主義視野中的“女性”/“女權”實在難以反觀中國革命中婦女解放的“身體政治”(姑且借用一下這個自由女權主義的說法)。難道婦女解放的身體政治真的只是“否定女性特質”“女人跟男人一樣”“男女平等就是男女相同”而沒有其他特征、表現和意義嗎?婦女解放對新的“主體性”建構難道不是包含了很多層面的階級性和社會性,包括男男女女都需要通過學習才能認識到的對傳統的父系制度以及傳統的性別歧視和習俗的批判和否定?難道結構性的變革中同時產生的文化和認識上的改造,就沒有廣大婦女自身主觀能動地參與和推動?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這些年來出現的一些研究,對這些問題有了重新的思考和認識。中國的婦女解放的重要性和它在革命當中成功的原因,在于革命將其視為自身的一部分,即,將婦女解放視為改變社會、改變中國國家的各種各樣的制度上面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一個有機的部分。重新進入研究革命歷史,就是研究自己的歷史,為了理解當下,想象未來。
面對復雜的“變遷”,如何延續?
回到我發言題目提出的問題,質疑“女性化”走向,是想強調中國革命和婦女解放的共同目標。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變革會不斷發生,不可能一場革命就把所有問題都解決了,而且革命有時會走向它的反面。但是,更為重要的是,不能因為一場革命當中沒有解決所有問題,就認為這場革命本身是失敗的。對婦女解放和革命進行反思的當下性,需要重新回到結構性問題的層面上,真正認識在什么意義上我們懂得,中國革命是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的革命。對這個問題的思考,需要也必須超越簡單的性別區隔。謝謝大家。
「 支持烏有之鄉!」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