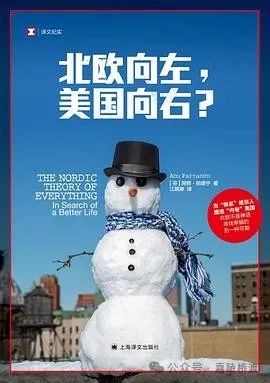《北歐向左,美國(guó)向右?》這本書(shū)很有意思。書(shū)作者阿努·帕塔寧2008年跟隨美國(guó)丈夫赴美生活,期間擔(dān)任美國(guó)多家主流媒體的撰稿人、客座記者,2018年左右又舉家返回了芬蘭生活。
這本書(shū)詳細(xì)對(duì)照了芬蘭為代表的北歐資本主義模式,與美式資本主義模式的優(yōu)劣,凸顯出北歐模式的優(yōu)勢(shì):善待員工,慷慨賦予各種假期和社會(huì)福利;發(fā)展高水平的基礎(chǔ)教育,淡化社會(huì)競(jìng)爭(zhēng)壓力,使得高等教育和職業(yè)教育都不再成為“卷”的代名詞或者說(shuō)分類標(biāo)準(zhǔn);較低成本維系了較高水準(zhǔn)的公共醫(yī)療服務(wù);發(fā)展出很高水準(zhǔn)的養(yǎng)老服務(wù)體系,耗資不高,但對(duì)待老齡尤其是高齡老人較為友好。
美式資本主義一貫自詡“小政府”,但美國(guó)的稅法為代表的法律體系卻非常繁復(fù),以至于美國(guó)中產(chǎn)階級(jí)和富裕階層的居民都必須聘用專門(mén)的會(huì)計(jì)師來(lái)幫助報(bào)稅。相較之下,芬蘭等北歐國(guó)家的政府更像是小政府,按照書(shū)作者的親身體驗(yàn),在芬蘭報(bào)稅非常清晰而簡(jiǎn)單。
而且,芬蘭的稅收體系主要面向中產(chǎn)及以上階層的居民,而美國(guó)20世紀(jì)80年代以來(lái)的歷次減稅已經(jīng)使得工薪階層成為主要的稅負(fù)承擔(dān)者(富豪則成為減稅政策的最大受益者),就連巴菲特、比爾·蓋茨等超級(jí)富豪都因?yàn)樽约杭{稅甚至比秘書(shū)還少而感到羞愧。書(shū)作者以芬蘭、瑞典、挪威等國(guó)的案例指出,雖然北歐國(guó)家對(duì)于富豪的征稅比例比較高,但并未產(chǎn)生一些經(jīng)濟(jì)學(xué)家所說(shuō)的抑制創(chuàng)新、造成金融活力不足等問(wèn)題。
在美國(guó)的總統(tǒng)大選以及聯(lián)邦(參眾)議員、各州州長(zhǎng)的選舉中,經(jīng)常出現(xiàn)候選人渲染征稅增加、福利增長(zhǎng)會(huì)有損資本主義活力,甚至踐踏公民自由的言論。雖然,美國(guó)的政治學(xué)家、經(jīng)濟(jì)學(xué)者其實(shí)完全可以看到北歐國(guó)家的例子,但是卻往往將北歐國(guó)家說(shuō)成是類同于蘇聯(lián)那樣,認(rèn)為不利于個(gè)人主義發(fā)展。書(shū)作者的觀點(diǎn)恰恰相反,指出在充分提供公民福利的基礎(chǔ)上,才可能為發(fā)展個(gè)人自由創(chuàng)造條件,“強(qiáng)烈的個(gè)人主義氣質(zhì)正是構(gòu)成北歐社會(huì)的基石之一”。
《北歐向左,美國(guó)向右?》書(shū)中介紹了芬蘭的生育保障,包括相關(guān)的產(chǎn)假、陪護(hù)假等制度安排。比如,每對(duì)父母最低的育兒假期在九個(gè)月左右。在芬蘭,孩子出生后三年內(nèi),家長(zhǎng)有權(quán)隨時(shí)回去工作,交替照看孩子,薪資、工作機(jī)會(huì)等不受影響。而在孩子三歲后,芬蘭還有國(guó)家補(bǔ)貼的日托中心為之提供服務(wù)。一個(gè)簡(jiǎn)單的道理就在于,“個(gè)體強(qiáng)則家興”,反過(guò)來(lái),給予適齡婚育人口以比較好的生育制度、福利保障,不僅僅可以促成社會(huì)人口的良性增長(zhǎng),保障勞動(dòng)力供給充足,而且還能切實(shí)起到減負(fù)的作用,避免中青年適齡人口在婚育后陷入家庭與工作兩方面事務(wù)難以兼顧的困境。

更重要的是,受益于芬蘭國(guó)家、社會(huì)的幫助,芬蘭的孩子從小就得以不斷降低在生活、經(jīng)濟(jì)上對(duì)于父母的依賴,更早地成長(zhǎng)為社會(huì)人,具有獨(dú)立意識(shí)、自主意識(shí)。相較之下,在美式制度環(huán)境下,每個(gè)生育、養(yǎng)育長(zhǎng)大的孩子,實(shí)際上耗費(fèi)了家庭的大量投資和精力,對(duì)于家庭的依賴度就很高,反而更可能成為難以自立的“巨嬰”。
《北歐向左,美國(guó)向右?》書(shū)中指出,北歐的社會(huì)福利也并不像美國(guó)人所設(shè)想的那樣,會(huì)造成大量的“福利女王”。事實(shí)上,北歐經(jīng)驗(yàn)的核心是促進(jìn)女性在婚育后繼續(xù)留在職場(chǎng),繼續(xù)投資于自身的職業(yè)技能,繼續(xù)籌劃個(gè)人職業(yè)生涯發(fā)展。
芬蘭的教育,其實(shí)可以解釋這個(gè)國(guó)家為什么有能力、有意識(shí)、有財(cái)力維持覆蓋如此之廣的公民福利。書(shū)作者指出,芬蘭1917年擺脫沙皇俄國(guó)的統(tǒng)治獨(dú)立,但在二戰(zhàn)結(jié)束后也仍然是個(gè)窮國(guó),除了森林以外沒(méi)有其他可利用的自然資源,也沒(méi)有海外殖民地為本土“輸血”。所以,這種情況下,芬蘭除了老老實(shí)實(shí)發(fā)展教育,然后通過(guò)培養(yǎng)的人才發(fā)展產(chǎn)業(yè),再用稅收不斷致力于提高教育的覆蓋范圍和發(fā)展水平,才可能養(yǎng)活自己,才可能迎來(lái)富足的生活——良好的教育體系,才能讓適齡婚育人口也就是社會(huì)的中堅(jiān)人群,盡可能擺脫后顧之憂去投入工作。芬蘭人在當(dāng)時(shí)的選擇,并沒(méi)有效仿美國(guó)引進(jìn)、發(fā)展私立教育,而是分步驟籌建并最終推廣統(tǒng)一的高質(zhì)量教育體系,由國(guó)家出資建立。
《北歐向左,美國(guó)向右?》書(shū)中甚至想到了反對(duì)意見(jiàn)者的觀點(diǎn),并給出了回應(yīng)說(shuō)明。中文互聯(lián)網(wǎng)上,曾經(jīng)有人談到芬蘭模式,認(rèn)為芬蘭是個(gè)小國(guó)家,族裔單一,而美國(guó)等國(guó)家地域遼闊、人口較多,所以不認(rèn)為芬蘭模式具有可復(fù)制性。問(wèn)題在于,美國(guó)的教育、醫(yī)療、社會(huì)福利問(wèn)題,其實(shí)是美國(guó)大多數(shù)州共同存在的。美國(guó)的這些政策困局,不同程度上出現(xiàn)在各州,而美國(guó)的州和地方權(quán)限本身較大。美國(guó)的州,與芬蘭的規(guī)模就差不多,也就是說(shuō),至少在美國(guó)很多州,完全可以通過(guò)引進(jìn)芬蘭哪怕部分經(jīng)驗(yàn),來(lái)擺脫政策困境、走出政治困境。
在分析美國(guó)的醫(yī)療困境(美國(guó)的醫(yī)療總支出、人均支出在發(fā)達(dá)國(guó)家中排名第一,服務(wù)水平和供給質(zhì)量卻位列倒數(shù)第一)后,書(shū)作者進(jìn)行了進(jìn)一步的剖析。
所評(píng)圖書(shū):
書(shū)名:《北歐向左,美國(guó)向右?》
作者:(芬)阿努·帕塔寧
譯者:江琬琳
出版社:上海譯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4年2月
「 支持烏有之鄉(xiāng)!」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wǎng)站日常運(yùn)行與維護(hù)。
幫助我們辦好網(wǎng)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xiāng)網(wǎng)刊微信公眾號(hà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