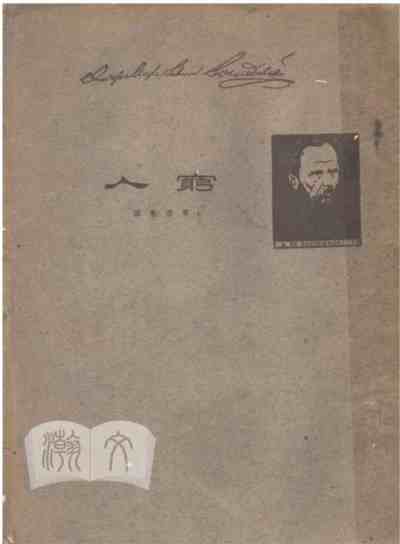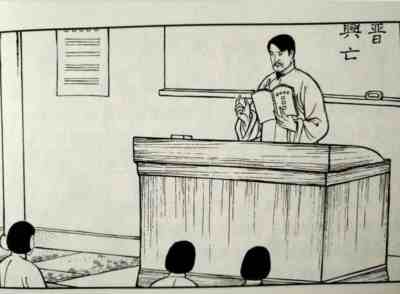魯迅的短篇小說《高老夫子》寫于1925年5月,發表于同年《語絲》雜志第26期。小說寫的是一位女子高等學校新聘的歷史教員——高老夫子——第一次登臺講學,即在女學生的“凝視”中落荒而逃的故事。這篇作品在魯迅的小說中一直不受重視,被簡單地視為一篇《儒林外史》式的諷刺小說,其主旨通常被理解為對假道學或偽新黨的批判。關于它的小說技巧,歷來的評價頗不穩定。早期評論家任叔認為,《高老夫子》對人物心理的表現,已“超過了阿Q時代”1,李長之則指出,與《孔乙己》《阿Q正傳》相比,《高老夫子》是藝術上不完整的“失敗之作”2;而就諷刺藝術而言,許欽文和林非也提出了截然相反的看法,前者認為《高老夫子》比《肥皂》的人物刻畫更加“活形活現”3,后者則認為它不如《肥皂》深切,較為模糊、單薄4。魯迅給研究者留下如此紛紜乃至針鋒相對的意見的作品是不多見的,這也意味著我們可能并未真正理解《高老夫子》的詩學機制。
在魯迅以都市知識分子為主角的小說序列中,《高老夫子》處在《端午節》和《肥皂》的延長線上。與《孔乙己》《阿Q正傳》這類鄉村題材作品相比,由《端午節》所開啟的都市知識分子小說,是魯迅直接面對其當下生活和文化情境的產物。然而,在諷刺小說和國民性批判的閱讀慣性中,這批作品很少得到充分語境化的闡釋,它們只是被籠統地理解為魯迅對知識分子劣根性的批判。近年來,藤井省三、彭明偉、陳建華、郜元寶等學者對《端午節》《肥皂》《弟兄》背后可能與魯迅創作動機有關的“當日之時事”(即陳寅恪所說的“今典”5),多有考證,并由此激發了頗富新見的闡釋,為我們提供了閱讀魯迅都市小說的新視野6。
錢曄 《高老夫子》連環畫封面
與《端午節》《肥皂》相比,《高老夫子》在塑造主人公的方式上發生了微妙變化:高老夫子在“高干亭”和“高爾礎”兩個角色之間游移不定,其中,“高爾礎”的自我意識得到了強調和凸顯,而“高干亭”的形象則隱藏在黃三、老缽、萬瑤圃等人的面目下,小說的敘事詩學呈現出復雜的中西雜糅的樣態。薩特論及福克納時表達過一個信念:“小說技巧總是讓讀者領悟小說家的哲學理念。”7本文試從解析《高老夫子》的形式詩學出發,通過引入與它具有互文關系的世界文學資源以及1925年前后魯迅所面對的“當日之時事”,在一個擴大了的文學和社會語境中,對其主旨和理念進行重新解讀。筆者試圖闡明,《高老夫子》在寫實小說的面紗下,蘊含著對現代中國文化情境的寓言式書寫:小說塑造的在“高干亭”和“高爾礎”之間游移而分裂的主人公,可以讀作魯迅對晚清以降的“新文化”及其未完成性的文學寓言。
從“照鏡子”談起
《高老夫子》開頭,有一個主人公照鏡子的細節。即將走上講臺的高老夫子,在鏡中仔細察看左邊眉棱上“尖劈形的瘢痕”,在回憶了一番瘢痕形成的兒時經歷并怨憤父母的照料不周之后,即擔心“萬一給女學生發見,大概是免不了要看不起的”8。這個照鏡的動作,看似和小說情節關系不大,但主人公由鏡中所見的“瘢痕”而引起的不安,卻構成了籠罩全篇的基調。這面鏡子也成為小說中的一個重要道具。它隨后還出現了兩次:一次是小說中間,高老夫子的老友黃三來訪時,“向桌面上一瞥,立刻在一面鏡子和一堆亂書之間,發見了一個翻開著的大紅紙的帖子”9;另一次是臨近末尾,主人公從講堂上落敗回家,將聘書和教科書都塞進了抽屜,“桌上只剩下一面鏡子,眼界清凈得多了”10。
姜彩燕指出,高老夫子出場時照鏡子的場景與芥川龍之介的小說《鼻子》有神似之處11。《鼻子》是芥川對日本禪智和尚長鼻子故事的改編。內道場供奉禪智因長了一個駭人的長鼻子而傷盡自尊,他費盡心思將鼻子縮短之后,卻并沒有將自尊心挽救回來,反而更加不安。魯迅1921年翻譯了這篇小說。《鼻子》開場不久,也有主人公對著鏡子察看自己的“長鼻子”,并希望在意念中將其變短的情景。對比魯迅的譯文12與《高老夫子》的開頭,兩者在細節上確有幾分神似;而就籠罩全篇的主人公的“不安”而言,兩篇作品的基調也頗為相近。可以想見,魯迅在創作《高老夫子》時,應該是想到了這篇他曾翻譯過的芥川小說。
芥川龍之介與魯迅相似,也是一位俄國文學的熱心讀者。《鼻子》在情節構造上與果戈理的同名小說《鼻子》頗有淵源:在果戈理的小說中,鼻子離開了八等文官科瓦廖夫臉上本來的位置,穿著軍銜更高的制服滿城亂竄。在這兩篇小說中,“鼻子”都是主人公另一個自我的象征13。不過,與果戈理小說不同的是,芥川小說還著重描寫了禪智內供因“長鼻子”而感到他人目光無處不在,這種對外界神經質般的察言觀色,也是《高老夫子》主人公的重要特點——“高爾礎”登臺講學之際,耳邊即縈繞著一種來歷不明的“嘻嘻”的竊笑聲(這一描寫在小說里出現了六次之多)。這種主人公對他人目光和話語的高度敏感,顯然又與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有著親緣關系。
果戈理《鼻子》,魯迅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年版
在陀氏的處女作《窮人》中,也有一段主人公照鏡子的著名場景。杰符什金因抄錯公文被叫到上司辦公室,他在鏡中瞥見了自己的模樣。原本竭力要裝得不被人注意、仿佛在世上不存在似的主人公,突然被鏡中的自我形象驚醒,因而發生了一連串悲喜劇14。最早發現《窮人》的價值并令陀氏在文壇聲名鵲起的評論家別林斯基,曾引述小說這段情節并大加贊賞15。但巴赫金認為,別林斯基并沒有真正領會這段描寫在藝術形式上的意義。在他看來,陀氏讓杰符什金從鏡中看到自我形象并出現痛苦驚慌的反應,不僅僅是如別林斯基所理解的從人道上豐富了“窮人”的形象,它恰恰是陀氏在主人公的塑造方式上,對其文學前輩果戈理的“革命”16。
《窮人》 韋叢蕪譯 未名社 1926年版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早期創作有著明顯的果戈理源頭,如《窮人》對“小人物”和貧困官吏的描寫即深受《外套》影響,而繼《窮人》之后的《二重人格》(又譯作《同貌人》《魂靈》),則將果戈理《鼻子》中人格分裂的主題發展到了極致。盡管主題相似,但在藝術法則上,陀氏從一開始就有自己的主張。在《窮人》中,他借主人公之口,對果戈理的小說詩學提出質疑:瓦蓮卡將《外套》一書借給了杰符什金,后者讀完感到十分惱怒,他在《外套》的主人公中認出了自己,但對果戈理的寫法非常不以為然,在他看來,將窮人的外貌、衣著以及日常生活的細節在小說中一覽無余地暴露出來,某種程度上是對人物的侮辱。對此,巴赫金有一段精彩評論:
陀思妥耶夫斯基還在創作初期,即“果戈理時期”,描繪的就不是“貧困的官吏”,而是貧困官吏的自我意識(杰符什金、戈利亞德金,甚至普羅哈爾欽)。在果戈理視野中展示的構成主人公確定的社會面貌和性格面貌的全部客觀特征,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便被納入了主人公本人的視野……甚至連果戈理所描繪的“貧困官吏”的外貌,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讓主人公在鏡子里看見而自我觀賞。17
在巴赫金看來,將自我意識作為塑造主人公的藝術上的主導因素,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說史上掀起的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窮人》中的杰符什金,已具備了陀氏小說的典型主人公——“地下室人”的雛形,他時刻在揣測別人怎么看他以及別人可能怎么看他。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窮人》中采用了書信體的形式,而書信本身,如巴赫金所云,即一種“察言觀色的語言”18。小說中杰符什金的形象,是通過他在信中的自我觀察和自我陳述為讀者所知的,因而有效避免了果戈理小說中敘事者的“僭越”;而陀氏讓杰符什金從鏡中照見自己的形象,正是其小說詩學的微觀表達——這里的“鏡子”,既有現實功能,也是主人公在他人目光和話語中感知自我的一個道具、一種隱喻。在這個意義上,無論是芥川的《鼻子》,還是魯迅的《高老夫子》,主人公的“照鏡”以及由此引發的不安的自我意識,皆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這里找到源頭。
芥川是被公認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影響的日本作家,而魯迅與陀氏也有不淺的淵源19。關于陀氏,魯迅最早形諸文字的論述是1926年為韋叢蕪譯、未名社出版的《窮人》所寫的《小引》。據韋叢蕪回憶,他1924年下半年從英譯本譯出《窮人》并經韋素園對照俄文修改后,1925年3月26日前后,由他的同鄉張目寒送給魯迅審閱20。張目寒是魯迅當時在世界語專門學校的學生,也是魯迅與未名社成員之間最早的聯絡人。查魯迅日記,1925年4月21日記有“目寒來并交譯稿二篇”21;同年8月11日,又有購買原白光譯《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5卷的記錄。據胡從經考證,此書便是魯迅據以校改《窮人》的日譯本22,此時,魯迅已與韋素園、韋叢蕪、李霽野等青年譯者一起計劃成立未名社,《窮人》也在醞釀出版。值得注意的是,魯迅收到《窮人》譯稿的時間,就在寫作《高老夫子》前不久。這意味著,我們有足夠的理由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角度,來審視《高老夫子》的小說形式及其新變。
《高老夫子》與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
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角度來閱讀《高老夫子》,不難發現,這篇小說的核心情節,其實主要是發生在主人公自我意識中的事件:從一開始的“照鏡”和備課時的“怨憤”,到站上講臺之后的心理風暴,都是發生在高老夫子內心里的戲劇,與外在的現實并不相干。雖然小說在主人公登臺講學前插敘的黃三來訪的情節,頗有《儒林外史》風味,但涉及女校講學這一主干情節時,高老夫子則變成一位十足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在擺脫了黃三之后,高老夫子即跑到賢良女學校,在門房的引導下,走到教員“豫備室”,繼而又在教務長萬瑤圃的引導下,經過植物園走進講堂。一路上,萬瑤圃滔滔不絕,高老夫子則沉浸在備課不充分的煩躁愁苦中。小說用了兩個“忽然”,來描寫他的動作:
“哦哦!”爾礎忽然看見他舉手一指,這才從亂頭思想中驚覺,依著指頭看去,窗外一小片空地,地上有四五株樹,正對面是三間小平房。23
爾礎忽然跳了起來,他聽到鈴聲了。24
隨后,小說又用了兩個“忽而”,來標識講課的開始與結束:
高老師忽而覺得很寂然,原來瑤翁已經不見,只有自己站在講臺旁邊了。25
他自己覺得講義忽而中止了……一面點一點頭,跨下講臺去,也便出了教室的門。26
錢曄《高老夫子》連環畫
在這兩個“忽而”的中間,就是高老夫子面對“半屋子蓬蓬松松的頭發”“小巧的等邊三角形”27所起的心理驚駭。
反復出現的“忽然”“忽而”,形象地寫出了沉浸在自我意識中的高老夫子,對外在物理時空感到的錯愕與茫然。這段敘述(也包括小說開頭兩段冗長的內心敘事),遵循的并非外在的物理時間,而是主人公的心理時間。高老夫子從教員“豫備室”走向講堂,小說的敘述與萬瑤圃滔滔不絕的說話一樣十分冗長,而從講堂走回教員“豫備室”的敘述,則十分迅疾;高老夫子的講課時間并不長,前后不過一小時,但在心理上卻幾乎是無限長,因此也無法度量,只能用兩個“忽而”來加以標識。這里的高老夫子如同夢游癥患者,似乎永遠也無法真實地感知周遭的世界,始終處于追趕、不安的狀態——時緩時疾的敘事節奏,與高老夫子惶惑不安的內心,形成絕妙的共振。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中敘事的變形和流動性,是不少研究者都注意到的特質。梅列日科夫斯基指出,陀氏作品的敘事“有時候被許多細節拉長、弄亂、堆積起來,有時候又過度壓縮、折褶”28。對于這種時而過分拉長、時而過度壓縮的敘事方式,巴赫金將之歸納為一種適用于陀氏整個創作方法的“時空體”(chronotope),簡言之,即小說的敘事并不遵循嚴格的敘述歷史的時間,而是往往超越這一時間,將情節集中到危機、轉折、災禍的時刻;而空間也通常超越過去,集中在發生危機或轉折的邊緣(如大門、入口、樓梯、走廊等)和發生災禍或鬧劇的廣場(通常用客廳、大廳、飯廳來代替)這兩點之上。這種“時空藝術觀”或“時空體”,巴赫金稱之為“非歐幾里得”式的,它超越了經驗的真實性和表面的理性邏輯,背后是一種狂歡化了的時間觀和世界感受29。在這個意義上,《高老夫子》對主人公在女校登臺講學的敘述,其敘事時空體——時而拉長、時而壓縮的時間,集中于邊緣(從“豫備室”到講堂的路)和廣場(講堂)的空間,與陀氏小說的時空藝術有著奇妙的契合。
目前學界已有的關于《高老夫子》的討論,無論是著眼社會語境的分析,還是從個體心理學或精神分析角度進行的解讀,都將高老夫子視為一個穩固的作為客體的主人公形象,“高爾礎”和“高干亭”之間的行為差異,通常被理解為虛偽、造作和言行不一。這顯然是仍然在用閱讀《孔乙己》《阿Q正傳》的方式,或更確切地說,仍然在單方面地用《儒林外史》的詩學,來理解這篇作品以及“高老夫子”的形象。我們并不否認《高老夫子》與《儒林外史》之間的顯著關聯,魯迅所稱道的吳敬梓“無一貶詞,而情偽畢露”30的諷刺藝術,在《高老夫子》對黃三、萬瑤圃等人物的刻畫中有著精妙的復現。然而,僅僅在《儒林外史》的視野中來閱讀這篇作品,會將小說中大量關于高老夫子自我意識的描寫排除在外,或僅作為主人公緊張心理的一個注腳。這一閱讀方式,很難真正照亮小說的形式,因而也產生了對其人物形象和諷刺藝術的歧義紛紜的理解。
紀德在闡述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藝術時指出,陀氏在描繪其小說近景中的大人物時,往往“不去描繪他們,而是讓他們在整本書的過程中自己來描述自己,而且,描畫出的肖像還在不斷變化,永遠沒有完成”31。巴赫金論及陀氏小說的主人公形象時,曾引入拉辛作品的主人公來做對比,得出了與紀德類似的看法:拉辛的主人公是如雕塑一般穩固而堅實的存在,陀氏的主人公則整個是自我意識,他“沒有一時一刻與自己一致”32。置于陀氏詩學的視野中來觀察,不難發現,《高老夫子》想要集中呈現的,并非一個穩固的作為客體的主人公形象,而恰恰是主人公在自我認知上的曖昧性和不穩定性。
《高老夫子》中敘事者對主人公的指稱頗有意味:一開始是一個孤零零的第三人稱代詞——“他”;“爾礎高老夫子”的名字,首次出現在女學校的聘書上,而在老友黃三的口里,主人公則被稱作“老桿”,以至接下來敘事者不得不在這兩個稱謂之間做一番連接:“老桿——高老夫子——沉吟了,但是不開口。”33直到小說最后,主人公的本名“高干亭”,才通過老缽向牌友的介紹而為讀者所知。這種先尊稱人物頭銜字號、最后才揭示人物本名,或者借人物對話和正式文書才說出人物正名的方式,其實是《儒林外史》常見的技巧34。不過,在《儒林外史》中,參差互見的人物字號、官銜和本名,最終指向的是同一個客體對象,而在《高老夫子》這里,不同指稱方式的變幻,暗示的卻是主人公自我認同的游移與分裂。
《高老夫子》的文本以主人公的講學和回家為界分為兩節。第一節是小說的主體,寫的是高老夫子如何以“高爾礎”的身份粉墨登場;第二節類似尾聲,寫的是他向“高干亭”的回歸。對于這一登場與回歸,小說均有詳細描寫:
他一面說,一面恨恨地向《了凡綱鑒》看了一眼,拿起教科書,裝在新皮包里,又很小心地戴上新帽子,便和黃三出了門。他一出門,就放開腳步,像木匠牽著的鉆子似的,肩膀一扇一扇地直走,不多久,黃三便連他的影子也望不見了。35
他于是決絕地將《了凡綱鑒》搬開;鏡子推在一旁;聘書也合上了。……一切大概已經打疊停當,桌上只剩下一面鏡子,眼界清凈得多了。然而還不舒適,仿佛欠缺了半個魂靈,但他當即省悟,戴上紅結子的秋帽,徑向黃三的家里去了。36
“紅結子的秋帽”俗稱“瓜皮帽”,是清末民初市民常戴的一種便帽;至于高老夫子為登臺講學所準備的“新帽子”,小說沒有具體描述,但可以想見應是民國剪辮之后適用的新式禮帽。關于“帽子”的描寫,在小說中也并非無關緊要的細節。借用巴赫金的術語,主人公在“高干亭”與“高爾礎”之間的游移和切換,豈非一場生動的“加冕”和“脫冕”的狂歡式鬧劇?
當高老夫子戴上象征市民生活的“紅結子的秋帽”向黃三家走去后,小說中搖晃不定的敘事總算安穩下來,空間也轉向了室內——最后,高老夫子在黃三家點了洋燭的麻將室內,才最終找到了身心的“舒適”。
《高老夫子》在《語絲》初刊時,前后兩節之間印有明顯的分節符37,這一分節符不僅區分了情節發展的兩個階段,也切分了兩種不同的敘事時空體:當主人公以“高爾礎”的身份登場時,他如同夢游者一般,行進在一個由過道與講堂構成的充滿危機的空間中,其內心世界與外部世界充滿了緊張的錯位與摩擦,這一節的敘事時空體,接近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的狂歡式或“非歐幾里得”式;而當他以“高干亭”的身份匯入老友黃三、老缽的群體后,則立即恢復了行動力與現實感,黃三家中點著“細瘦的洋燭”的麻將室,賦予了人物身心的雙重安寧與舒適——這是我們在《紅樓夢》《儒林外史》等傳統小說中常見的時空體。
《高老夫子》,初刊《語絲》第26期
如此看來,魯迅交織著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與《儒林外史》筆法,在《高老夫子》中極為藝術地完成了對主人公的兩個“自我”,或者說二重人格——“高爾礎”和“高干亭”的形象塑造。在這個意義上,《高老夫子》的情節輪廓與主旨理念,其實與果戈理和芥川龍之介的同題小說《鼻子》(也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二重人格》),形成了頗有意味的同構關系:在果戈理和芥川的小說中,主人公的“鼻子”——不管是離開科瓦廖夫擅自行動的鼻子,還是讓禪智內供傷盡自尊的長鼻子,在經歷了一番游歷或改造之后,最終都得到了復原;而在《高老夫子》中,“高爾礎”則相當于離開主人公獨自遠行的“鼻子”,它最終也因對新角色的極度不適,而復原為“高干亭”。魯迅后來在1934年還重譯過果戈理的《鼻子》38,可見他對這一“同貌人”主題的持續興趣。那么,魯迅在《高老夫子》中精心塑造出這一在兩個“自我”之間游移而不安的主人公,究竟想要表達什么呢?小說的主旨顯然并非諷刺假道學、偽新黨那么簡單。對此,我們還需將目光轉向小說之外。
陀思妥耶夫斯基《二重人格》新文藝出版社1958年版
女學生與新文化:作為“今典”的《一封怪信》
《高老夫子》的情節高潮是高老夫子與女學生的“看”與“被看”。試圖“鉆進”女學堂里去“看”女學生的高老夫子,反而成為“被看”的對象:
他不禁向講臺下一看,情形和原先已經很不同:半屋子都是眼睛,還有許多小巧的等邊三角形,三角形中都生著兩個鼻孔,這些連成一氣,宛然是流動而深邃的海,閃爍地汪洋地正沖著他的眼光。但當他瞥見時,卻又驟然一閃,變了半屋子蓬蓬松松的頭發了。39
錢曄《高老夫子》連環畫
這段描寫是《高老夫子》中的名文,即便對小說整體評價不高的李長之,也認為寫得“確乎好”40。高老夫子朝向講臺下的“看”,其實并未真正看見,他與女學生的對視,僅僅存在于場景閃現的瞬間。最終,在不可見的女學生的“凝視”下,他被迫收回眼光,落荒而逃。實際上,這一從未真正出場的“女學生”,是《高老夫子》的一個關鍵詞。從一開始,在高老夫子“照鏡”之際,女學生便作為想象的他者出現了,“萬一給女學生發見,大概是免不了要看不起的”。可以說,正是以假想的女學生的眼光,高老夫子才特別“發見”了眉棱上的瘢痕,因此開始了對自我的喬裝改扮;而此刻,當他的這一喬裝的自我想要向作為客體的女學生謀求欲望的滿足時,卻遭遇了這一客體的無情反擊。
竹內好指出,《高老夫子》只能看作魯迅“厭惡自己的產物”41。排除其中的酷評成分,這一觀察其實頗為敏銳。與《端午節》相似,《高老夫子》也有著魯迅當下生活的投射。1923年7月,時任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校長的許壽裳聘請魯迅擔任國文系小說史科的兼任教員。1924年9月,女子高等師范學校改為女子師范大學,魯迅的兼職不變。寫作《高老夫子》前后,魯迅每周都到女師大上課,作為女學生之一的許廣平即在班上聽課,并已與魯迅有書信往返。女學堂來了男教員,這對素來嚴于男女之大防的中國傳統倫理,提出了相當程度的挑戰。《高老夫子》的情節高潮,可以說是對這一新舊更迭時代女子教育的生動寫照。魯迅借此對包括他自己在內的男性知識分子,如何處理新的制度與文化情境之下的師生倫理,提出了靈魂拷問。
《高老夫子》寫于1925年5月。這一時期,魯迅每月都會收到商務印書館寄送的《婦女雜志》。《婦女雜志》第10卷第10號是“男女理解”專號,起源于不久前一樁鬧得沸沸揚揚的“韓楊事件”。1924年5月7日,《晨報副刊》“來件”欄中發表了以韓權華的名義送登的《一封怪信》。韓權華是北京大學的一位女學生,《一封怪信》是指北大歷史系教員楊棟林(字適夷)寫給她的一封疑似求愛的兩千多字的“情書”。楊在信中首先述說自己聽到的關于他和韓之間“要好極了”、甚至已經“訂婚”的“謠言”,然后他仔細研究并報告了“謠言”的由來,最后則是對韓的請求,以及他想出來的共同對付的方法。韓權華感到被冒犯,同時也為了申明自己的態度,故將此信在《晨報副刊》上公開發表,并在“按語”中寫道:“不意我國高等學府的教授對本校女生——素不認識的女生竟至于如此。我以為此等事匪但與權華個人有關,實足為我國共同教育(Co?education)之一大障礙。”42所謂“共同教育”即“男女共校”,這是“五四”前后頗受矚目的一樁新文化事件。韓權華能在北大求學,正是拜這一新文化所賜。
最初入北京大學之女生,《少年世界》1卷期
《一封怪信》刊出后,立即引起巨大的輿論反響。一方面是大學生貼榜發文,對楊棟林的行為大肆討伐。楊棟林迫于壓力,兩天后即向北大辭職43,不久其他兼職院校也將他辭退。隨后,此事又在報刊中引發知識階層的激烈討論。與大眾輿論對楊棟林一邊倒的討伐不同,江紹原、周作人以及《民國日報·婦女周報》《婦女雜志》的評論作者,對當事人有著更多的理解與同情,并呼吁一種更為寬容和理性的道德尺度。江紹原和《婦女雜志》的評論者“起睡”都認為,韓楊事件只是個人私事,不應貿然付諸社會公斷44。《民國日報·婦女周報》的社論則指出,如果不是抱著蔑視女性的態度、將女性看作“易損品”的話,則楊棟林的信最多只是對于韓女士個人的無禮,對她并不構成損失,作者在文末呼吁中國青年男女迫切需要一種“心的革命”,以打破傳統的兩性觀念45。《婦女雜志》的“男女理解”專號,正是以此事為契機,以“我所希望于男子者”和“我所希望于女子者”為題,向雜志的女性和男性讀者征文,以期增進兩性的相互理解。這期專號的“卷頭言”即題曰“男女之心的革命”。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報刊輿論中,“新文化”成為一個隨時被征用且意義多元曖昧的新名詞。費覺天是當時為楊棟林辯護最有力的一位,他搴出新文化的旗幟,為楊的行為尋找根據。在他看來,在“反對舊禮教、反對三綱五常”的“新文化運動旗幟”下,應當承認先生可以同學生結婚(他舉出羅素與勃拉克的戀愛為例),也當承認男女婚姻個人自主,如果認同這一新文化理念,那么楊棟林的信就是“很光明,很平常”的事情,韓女士的舉動實屬處置失當46。而幾乎同時發表意見的周作人,則將批判的矛頭指向了“貼黃榜,發檄文”的大學生,在他看來,“中國自五四以來,高唱群眾運動社會制裁,到了今日變本加厲,大家忘記了自己的責任,都來干涉別人的事情,還自以為是頭號的新文化,真是可憐憫者”47。周作人的文章針對的是大學生過激行為背后所蘊含的群眾對個人自由的侵犯,但他取了一個聳人聽聞的標題——“一封反對新文化的信”。
韓權華(1903-1985)
與周作人不同,魯迅并沒有就韓楊事件直接發表意見。但如果將《高老夫子》納入考察視野,不難發現,這篇小說對《一封怪信》及其引發的報刊輿論,實有著不同程度的反饋與折射。高老夫子作為一個對外界高度敏感的主人公,與《一封怪信》的作者楊棟林之間,頗有神似之處。有意思的是,楊棟林的書信文體,與陀氏小說《窮人》中杰符什金寫給瓦蓮卡的信也非常相似,充滿了對他人話語以及對自己的愛慕對象的察言觀色。我們不妨略引一段:
那天聽了這話我也不知道是吉是兇,也不知道誰造的這謠言。但是無法探聽真相,只好忍耐著,卻是弄得我在講堂上心神不安了。狼狽之至,狼狽之至!48
楊棟林的“狼狽”,既源自他所說的謠言,更源自他對女學生韓權華的欲望。在這個意義上,《高老夫子》的情節高潮——主人公在女校講堂上對女學生的看與被看,不啻是對楊棟林的心理所進行的一個絕妙的傳神寫照和精神分析。
將《一封怪信》作為《高老夫子》的“今典”來閱讀,可令我們對這篇小說產生全新的理解。“韓楊事件”本身并不特殊,晚清興女學以來,類似的事件便時有發生。夏曉虹曾探討過晚清的一起著名案例,即京師大學堂譯學館學生屈彊投書四川女學堂學生杜成淑以示傾慕,卻遭遇杜以公開信方式發表的嚴詞拒斥49。這類從晚清一直延續到“五四”的性別之爭,在在顯示了新制度與舊道德之間的裂隙。1924年前后,距清末女學堂的開設已近二十年,“男女共校”也已在制度上確立。然而,傳統的兩性觀念似乎并沒有得到改觀,且女性仍然在用將私人信函公開發表的方式來維護自身的聲譽。這不禁令我們懷疑,剛剛過去的致力于破除舊禮教、重估一切價值的新文化運動,是否真正形塑了健全且能與新的社會狀況相適應的新倫理和新道德。
起睡:《兩性間一習見的事》,《婦女雜志》10卷七號,1924年7月
《婦女雜志》“男女理解”專號刊出的應征文章中,不少女性讀者即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成效提出了質疑。章君俠指出,“知識界中有一般表面上似乎尊重女性……的男子,他們一面大唱特唱‘女子解放’‘自由戀愛’等新名詞以博時譽,另一面卻在虐待妻女,以鞏父權、夫權”50。而在心珠女士看來,無論是四年前在《京報》上罵蘇梅女士的幾位先生,還是韓楊事件中在《東方時報》發表《廁所內的婚姻問題》的青年學生,都是新文化運動的主力軍,但他們心中仍然“充滿了以女子為物的觀念”51。此外,還有不止一位女性讀者感慨,從前男子以女子為玩物,而現在則以女性為偶像,其實“都是不以人的眼光看女性”52。看來,現代中國的“男女之心的革命”,實任重而道遠。
魯迅在《高老夫子》中所塑造的在女學生的“凝視”中敗下陣來的高老夫子,通常被視為假道學或反對新文化運動的復古派的代表。然而,置于《一封怪信》及其引發的上述輿論語境中,高老夫子的形象與其說是對新文化的反對者的諷刺,不如說是對新文化運動本身的反思:這位在“高干亭”和“高爾礎”之間搖擺不定、造作不安的主人公,正是對當時被作為一個新名詞而隨意挪用,但卻意義曖昧、難以自處的“新文化”的絕妙隱喻。
新文化的“擬態”
1925年11月,收錄了魯迅“五四”前后報刊評論文章的雜感集《熱風》在北新書局出版。魯迅在《〈熱風〉題記》中對新文化運動的“名目”提出了質疑:
《熱風》初版本 北新書局發行
五四運動之后,我沒有寫什么文字,現在已經說不清是不做,還是散失消滅的了。但那時革新運動,表面上卻頗有些成功,于是主張革新的也就蓬蓬勃勃,而且有許多還就是在先譏笑,嘲罵《新青年》的人們,但他們卻是另起了一個冠冕堂皇的名目:新文化運動。53
袁一丹注意到魯迅這番言論與我們通常對新文化運動的評價之間的差異,并詳盡探討了其背后“另起”的“新文化運動”的狀況54。在筆者看來,魯迅此論,不僅只是為新文化運動辨“名”,更源于他對新文化運動之“實”的觀感。換言之,新文化運動時期引入的新觀念、新話語乃至新制度,與它們在中國的現實實踐之間的分離、分裂或者說變形,恰恰是魯迅在包括《高老夫子》在內的《彷徨》中的諸多小說(如《幸福的家庭》《傷逝》《離婚》)中,所探討的核心議題55。
在《〈熱風〉題記》中,魯迅兩次用到了“擬態”一詞:一是文章開頭寫西長安街一帶衣履破碎的窮苦孩子叫賣報紙,“三四年前,在他們身上偶而還剩有制服模樣的殘余;再早,就更體面,簡直是童子軍的擬態”;一是文章臨近結尾,“自《新青年》出版以來,一切應之而嘲罵改革,后來又贊成改革,后來又嘲罵改革者,現在擬態的制服早已破碎,顯出自身的本相來了”56。“擬態”(mimicry)是一個生物學術語,指的是一種生物模擬另外一種生物或模擬環境中的其他物體以保護自己或攻擊敵人的現象。在拉康看來,生物的擬態并非單純為了適應環境,而是依據他者的存在形構自身的存在,即因為想象自己將被看而模仿性地改變自己的視覺形態57。在《高老夫子》中,主人公正是以想象的女學生、新學堂為潛在他者,從而多方面地展開了對自我的改造和形構:他為自己配備了新知識(《論中華國民皆有整理國史之義務》)和新形象(新帽子、新皮包、新名片),其中,最具戲劇色彩的情節,則是追慕俄國文豪高爾基而改字“爾礎”。
這正是一種典型的“擬態”行為。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將《高老夫子》與《〈熱風〉題記》進行互文閱讀:如同高老夫子對“高爾礎”的角色扮演,當時冠以“新文化”名目的諸多革新運動,在魯迅看來,亦不過是一種對想象的(西方)新思想、新文明或新制度的“擬態”。
高老夫子之外,魯迅還花了不少筆墨寫了黃三和萬瑤圃這兩個人物。在小說中,黃三是“高干亭”的舊友,但在高老夫子接受了女校的聘書后,這位“一禮拜以前還一同打牌,看戲,喝酒,跟女人”的老友,就變得“有些下等相了”58,成了主人公急于擺脫的對象;而當高老夫子敗退回家,將憤怒指向女學堂之際,他的內心獨白——“女學堂真不知道要鬧到什么樣子,自己又何苦去和她們為伍呢?犯不上的”59,恰與此前黃三來訪時說過的話一模一樣,聽起來就像是黃三的幽靈附體。很顯然,黃三(包括另一位牌友老缽)正是主人公那“欠缺了”的“半個魂靈”。除了“高干亭”的舊友,小說還濃墨重彩地寫了“高爾礎”的新同事——教務長萬瑤圃。致力于新學問的高老夫子,對萬瑤圃與女仙酬唱的那套舊文學毫無興趣,在走向女校講堂的路上,他與這位喋喋不休的教務長一直貌合神離。但小說有一個意味深長的細節:萬瑤圃與女仙贈答的《仙壇酬唱集》,與高老夫子叩響新學問的敲門磚《論中華國民皆有整理國史之義務》,其實是刊登在同一張報紙——《大中日報》——上的。這意味著,萬瑤圃也不過是主人公化裝為“高爾礎”后的另一個“復影”。
錢曄連環畫《高老夫子》
周作人指出,魯迅在小說中將黃三、老缽與萬瑤圃這兩群人分開來寫,但中間也加些呼應,如見面時,都是“連連拱手,膝關節和腿關節接連彎了五六彎,仿佛想要蹲下去似的”,在他看來,“這重復不是偶然的,它表示出他們同樣的作風,是一伙兒的人物”60。周作人的觀察頗為敏銳,但他隨后將這一描寫溯源至紹興鄉間“浮滑少年”的作風,則未免誤導了闡釋方向。如同上文所分析的“鏡子”和“帽子”一樣,這一拱手屈膝禮,在小說中也并非無關緊要的細節:相似的禮儀,將高老夫子兩個看似不相干的“魂靈”與“復影”聯系起來。兩者的相似,除了拱手屈膝禮,還有對待女性的態度:無論是黃三的將女學生視為“貨色”,還是萬瑤圃的將女詩人捧為“仙子”,背后均是以女子為“物”的陳腐觀念,正如上文所引《婦女雜志》征文中多位女性讀者所感慨的,他們都沒有將女性當作平等的“人”來看待。如此看來,黃三和萬瑤圃的形象,實代表了高老夫子潛意識中受到壓抑的愿望,用魯迅不久前譯介的廚川白村的文學理論來表述,他們乃是主人公的“苦悶的象征”61。在小說中,盡管高老夫子拼命拒絕與黃三、萬瑤圃混為一談,但最終仍是他的這些潛意識的“魂靈”“復影”占了上風,借用《〈熱風〉題記》的說法,“擬態的制服”終究脫落,“顯出自身的本相來了”。
趙延年1976年作 《高老夫子》版畫插圖
高老夫子在“擬態”與“本相”之間的反差,構成了《高老夫子》重要的反諷結構。如果將這篇小說的主人公視為新文化的隱喻,那么魯迅通過具象化地呈現高老夫子的擬態與本相、意識與潛意識之間的錯位和反差,深刻地揭示了新文化的分裂和它的未完成性。新文化以擬想的西方新思想、新文明、新制度為“鏡”,將自己用新皮包、新帽子和新名字裝扮一新,然而,這一喬裝的自我,如同將一個他者引入自我的形式結構之中,始終與現實的物理時空無法協調:小說中,高老夫子的手表與女學校的掛鐘之間永遠“要差半點”62(掛鐘這一細節出現了兩次),而女學校的空間場所,如教員“豫備室”、講堂、過道乃至植物園,都對高老夫子并不友好;“爾礎高老夫子”行進在一個“非歐幾里得式”的時空之中,始終不具備行動的主體性(他的走路要么“像木匠牽著的鉆子似的”,要么要由駝背的老門房或花白胡子的教務長引導),也無法與任何人(包括萬瑤圃和女學生)產生實際的交流。這是一個空洞的、惶惑的、未能完成的主體。
拉康在著名的“鏡像階段”理論中,揭示了鏡子裝置前后主體與鏡像之間的異質性,在他看來,主體對自己“鏡中之像”的認同,本質上是一種“誤認”,它需要穿越想象與真實、他者與自我、外在世界與內在世界的多重難以逾越的界限63。魯迅在《高老夫子》中所著力描繪的主人公的“擬態”行為及其失敗,可以說以一種十分形象的方式,揭示了鏡像認同的誤認機制。在小說開頭意味深長的“照鏡子”情節中,高老夫子第一次朝向鏡子觀看時,對鏡中那個帶有瘢痕的身體形象并不認同;隨后,他開始按照想象的新學堂、女學生的眼光喬裝改扮,以高爾礎的形象粉墨登場。然而,這一喬裝的(或者說擬態的)自我,在賢良女學校所上演的戲劇并不成功,他先是在欲望的客體(女學生)的“凝視”中敗下陣來,繼而又遭到了植物園里桑樹“一枝夭斜的樹枝”64的致命一擊——這棵桑樹,似乎成為高老夫子在女學堂里遭遇到的唯一真實之物。至此,其“擬態”的自我(高爾礎)終于徹底失效。當高老夫子在植物園撞上桑樹后狼狽地回到教員“豫備室”時,小說寫道:
那里面,兩個裝著白開水的杯子依然,卻不見了似死非死的校役,瑤翁也蹤影全無了。一切都黯淡,只有他的新皮包和新帽子在黯淡中發亮。看壁上的掛鐘,還只有三點四十分。65
這意味著,作為主體的女學校和高爾礎都已如鏡花水月般消失不見,只剩了皮包和帽子這些被褪下的“擬態的制服”。
《高老夫子》的文本中,出現了兩個用方框標識的圖像符號,一是女校的聘書,另一個則是女校植物園中將桑樹標識為“桑/桑科”的木牌。聘書和木牌無疑是新文化的象征,在它們的文字之外加上方框,看似是對這兩個物件極為寫實的再現,但這一圖像與文字的跨媒介并置,卻在文本中制造了新的意義:用方框圈起、作為圖像呈現的聘書和木牌,又何嘗不是新文化的一件可能并不合身的“擬態的制服”?聘書和木牌,原本具有名片或名牌的指示作用,指向的是現實中的人和樹,但在《高老夫子》中,它們其實均已被切斷了與真實之物的關聯,而淪為純粹的表象——如同高老夫子的新皮包和新帽子,它們除了“新”之外,別無所指。這兩個用方框圈起的聘書和木牌,無疑也是對“新文化”之淪為膚泛的新名詞——一個空洞的能指——的絕好象征。
光緒《了凡綱鑒》古籍線裝書
如此看來,魯迅寫于1925年5月的《高老夫子》,可以視為他對其時剛剛過去的新文化運動所進行的生動描寫和深刻反思。當時冠以“新文化運動”名目的諸般革新運動,看起來“蓬蓬勃勃”,但如細察這一運動,新文化究竟為何物,則難免令人心生疑竇。在魯迅看來,與高老夫子類似,其時甚囂塵上但又意義膚泛的新文化,也是一個在他者目光和話語中不斷被異化的主體:它既對自身帶有“瘢痕”的傳統無法認同,同時又與以西方為鏡的新學問這一象征秩序并不相容,因此在中西古今之間幾乎無所歸依。正如“高爾礎”不過是對高爾基名字的拙劣仿用,而新式《中國歷史教科書》與傳統歷史教科書《了凡綱鑒》之間,“也有些相合,但大段又很不相同”66。如同高老夫子在擬態與本相、意識與潛意識、他者與自我、想象與現實之間的無所適從,新文化本身,也是一個惶惑的、未完成的、分裂的主體。這一缺乏主體性的、未完成的文化狀態,既是晚清以降中國諸多現代性變革的內在隱憂,又何嘗不是我們今天依然要面對的嚴肅課題?小說題為“高老夫子”,“夫子”是舊時學生對老師的尊稱,這也提醒我們,儒家關于師道的禮教已經崩壞,但與新的社會文化情境相適應的師生倫理尚未建立,高老夫子正處在一個真空地帶,無地彷徨。
注釋
1 任叔:《魯迅的〈彷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魯迅研究室編:《1913—1983魯迅研究學術論著資料匯編》第1卷,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63頁。
2 40 李長之:《魯迅批判》,上海北新書局1936年版,第120—122頁,第120頁。
3 許欽文:《仿(彷)徨分析》,中國青年出版社1958年版,第64頁。
4 林非:《論〈肥皂〉和〈高老夫子〉——〈中國現代小說史上的魯迅〉片段》,《魯迅研究》1984年第6期。
5 參見陳寅恪:《讀哀江南賦》,《陳寅恪集·金明館叢稿初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版,第234—235頁。
6 參見藤井省三:《中國現代文學和知識階級——兼談魯迅的〈端午節〉》,《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2年第3期;彭明偉:《愛羅先珂與魯迅1922年的思想轉變——兼論〈端午節〉及其他作品》,《魯迅研究月刊》2008年第2期;郜元寶:《〈弟兄〉二重暗諷結構——兼論讀懂小說之條件》,《文學評論》2019年第6期;陳建華:《商品、家庭與全球現代性——論魯迅的〈肥皂〉》,《學術月刊》2020年第7期。
7 轉引自喬治·斯坦納:《托爾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嚴忠志譯,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4頁。
8 9 10 23 24 25 26 27 33 35 36 39 58 59 62 64 65 66 魯迅:《高老夫子》,《魯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76頁,第77頁,第84頁,第80—81頁,第81頁,第82頁,第83頁,第82頁,第79頁,第79頁,第84頁,第82頁,第77頁,第84頁,第80頁,第83頁,第84頁,第76頁。
11 參見姜彩燕:《自卑與“超越”——魯迅〈高老夫子〉的心理學解讀》,《西北大學學報》2015年第5期。
12 “每當沒有人的時候,對了鏡,用各種的角度照著臉,熱心的揣摩。不知怎么一來,覺得單變換了臉的位置,是沒有把握的了,于是常常用手托了頰,或者用指押了頤,堅忍不拔的看鏡。但看見鼻子較短到自己滿意的程度的事,是從來沒有的。內供際此,便將鏡收在箱子里,嘆一口氣,勉勉強強的又向那先前的經幾上唪《觀世音經》去。”(《魯迅譯文全集》第2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84頁)
13 離開科瓦廖夫的“鼻子”,代表著主人公的社會野心,而禪智內供對“長鼻子”的殘酷改造,則意味著潛在的社會規則對自我的形塑。
14 這一段韋叢蕪的譯文如下:“我看見大人在站著,他們都圍著他。我大概沒有鞠躬;我忘記了。我是如此狼狽,我的嘴唇抖戰,我的雙腿抖戰。這也是難怪的,親愛的姑娘。第一,我害臊;我一瞥右邊的鏡子,我所看見的光景也盡夠使人發瘋了。第二,我舉止動作常是避人,好像在世界上就沒有我這個人似的。……一個鈕扣——鬼氣!——系著一根線掛在我的制服上——忽然掉了,在地板上跳動(顯然是我無意之間碰了它),玎珰的響,可惡的東西,直接滾到大人的腳前——在一陣奧妙的靜寂之中!……大人的注意立刻轉到我的面貌和衣服上來。我記起我在鏡中所看見的;我忙撲上前去捉鈕扣!”(陀思妥也夫斯基:《窮人》,韋叢蕪譯,未名社1926年版,第215—216頁)
15 參見別林斯基:《彼得堡文集》,《別林斯基選集》第2卷,滿濤譯,時代出版社1952年版,第187—215頁。
16 17 32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白春仁、顧亞鈴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8年版,第83—85頁,第83—84頁,第87頁。
18 關于杰符什金“察言觀色的語言”的分析,參見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第281—289頁。
19 這方面的專論,參見李春林:《魯迅與陀思妥耶夫斯基》,安徽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
20 韋叢蕪:《讀〈魯迅日記〉和〈魯迅書簡〉——未名社始末記》,《魯迅研究動態》1987年第2期。魯迅日記1925年3月26日記有“得霽野信并蓼南(韋叢蕪筆名——引者注)文稿”(《魯迅全集》第15卷,第557頁),所得“文稿”為韋叢蕪的短篇小說《校長》,魯迅28日即將它轉寄鄭振鐸,后在《小說月報》16卷(1925年)7期中刊出。韋叢蕪在這段回憶中指出,《窮人》譯稿送給魯迅的時間即“大約在這前后”。
21 《魯迅全集》第15卷,第561頁。
22 胡從經:《泣不成聲的絕叫——〈窮人〉:讀魯迅序跋書札記》,《讀書》1981年第11期。
28 梅列日科夫斯基:《托爾斯泰與陀思妥耶夫斯基》,楊德友譯,華夏出版社2016年版,第231頁。
29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第210、235—245頁;另參見M. M. Bakhtin,“Forms of Time and Chronotope in the Novel”,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 by M. M. Bakhtin, Michael Holquist (ed.), trans. Caryl Emerson and Michael Holquist,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1, pp. 248-249。
30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魯迅全集》第9卷,第231頁。
31 安德烈·紀德:《關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講座》,余中先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39頁。
34 參見程毅中:《近體小說論要》,北京出版社2017年版,第96—97頁。
37 魯迅:《高老夫子》,《語絲》第26期,1925年5月11日。這一分節符(三個黑色五角星號)在收入《彷徨》以及后來的《魯迅全集》時,均以空格代替。
38 果戈理:《鼻子》,許遐(魯迅)譯,《譯文》第1卷,第1期,1934年9月。
41 竹內好:《從“絕望”開始》,靳叢林編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版,第113頁。
42 韓權華:《一封怪信》,《晨報副刊》1924年5月7日。據西夷《記北大的初期女生》(刊《正論(北平)》1947年第5期)一文的回憶,送登此信并寫文章駁斥楊棟林的是韓權華的姐丈,也是由他“壓迫”孫伏園將此信在《晨報副刊》發表。
43 1924年5月10日《北京大學日刊》發布注冊部布告(二):楊適夷先生辭職,所授功課暫行停講;另,1924年5月14日《時報》也刊發了一則短消息:“北大教授楊適夷、致函女生韓權華、被韓將函在報上宣布、楊辭職(本館十二日北京電)。”
44 參見江紹原:《伏園兄我想你錯了》,《晨報副刊》1924年5月12日;江紹原:《經你一解釋》,《晨報副刊》1924年5月15日;起睡:《兩性間一樁習見的事》,《婦女雜志》第10卷第7號,1924年7月。
45 奚明:《社評》,《民國日報·婦女周報》1924年5月21日。
46 費覺天:《從新文化運動眼光上所見之韓楊案》,《京報》1924年5月15、16、18日。
47 陶然(周作人):《一封反對新文化的信》,《晨報副刊》1924年5月16日。
48 韓權華:《一封怪信》。
49 參見夏曉虹:《晚清女性與近代中國》(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二章《新教育與舊道德:以杜成淑拒屈彊函為例》。
50 章君俠:《我所希望于男子者(六)》,《婦女雜志》第10卷第10號,1924年10月。
51 心珠女士:《我所希望于男子者(四)》,《婦女雜志》第10卷第10號。
52 小倩:《我所希望于男子者(九)》,《婦女雜志》第10卷第10號。
53 56 魯迅:《〈熱風〉題記》,《魯迅全集》第1卷,第307—308頁,第307—308頁。
54 袁一丹:《“另起”的“新文化運動”》,《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9年第5期。
55 《幸福的家庭》《傷逝》對“五四”話語的擬諷和反思非常明顯;關于《離婚》與“五四”女性解放話語之間的關系,參見楊聯芬:《重釋魯迅〈離婚〉》,《文藝爭鳴》2014年第6期。
57 參見吳瓊:《他者的凝視——拉康的“凝視”理論》,《文藝研究》2010年第4期。
60 周遐壽(周作人):《魯迅小說里的人物》,上海出版公司1954年版,第183—184頁。
61 1924年,魯迅譯出廚川白村的文藝理論著作《苦悶的象征》,隨后由新潮社出版。廚川白村糅合弗洛伊德和柏格森的理論,將文藝視為用改裝的具象形式把“生命力受了壓抑而生的苦悶懊惱”表達出來。他將這種表現法稱為“廣義的象征主義”(王世家、止庵編:《魯迅著譯編年全集》伍,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6—313頁)。《苦悶的象征》不僅對魯迅的創作頗有影響,也作為“今典”廣泛地存在于他這一時期的詩文小說中。
63 參見Jacques Lacan, “The Mirror Stage as Formative of the Function of the I as Revealed in Psychoanalytic Experience”, Écrits: A Selection, trans. Alan Sherida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pp. 1-7;吳瓊:《雅克·拉康:閱讀你的癥狀》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21—133頁。
「 支持烏有之鄉!」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