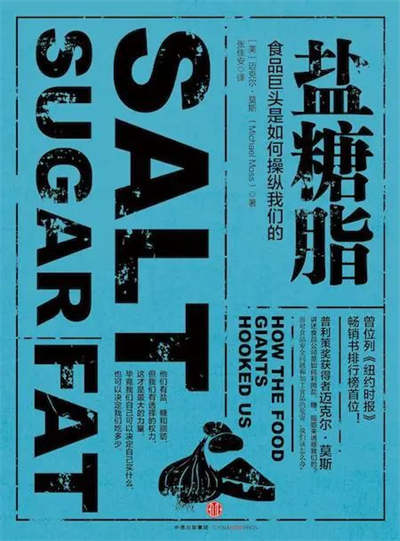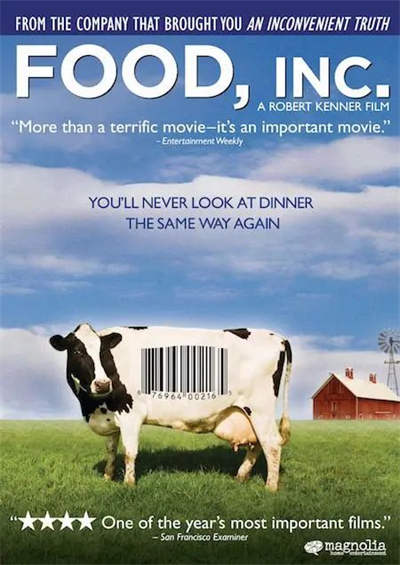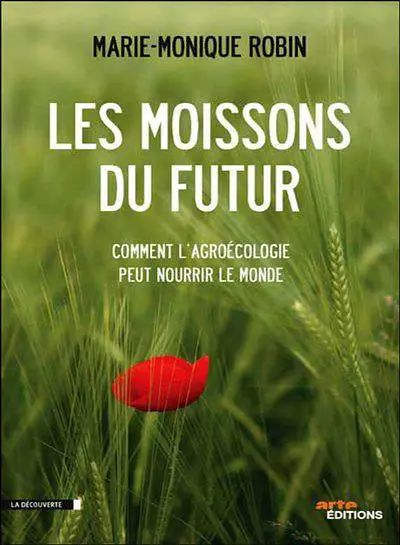導(dǎo)語:開學(xué)季,“預(yù)制菜進(jìn)中小學(xué)”的新聞在各地陸續(xù)爆出,不少人紛紛指出,“接受預(yù)制菜不等于接受預(yù)制菜進(jìn)入校園”,這讓預(yù)制菜再次進(jìn)入公眾視野,引發(fā)公眾的討論和質(zhì)疑。
即便早期甚至可能有優(yōu)秀的中央食堂配送的高端預(yù)制菜,但只要兒童青少年的健康不是校園餐飲的目標(biāo),學(xué)校的真正目的是更好的實現(xiàn)交換價值——賺錢,那最終不合格的、過度加工的、過度添加的預(yù)制菜劣幣驅(qū)逐良幣是有極大可能的,難道我們要到時候再“亡羊補牢”嗎?所以問題在于能否把青少年的健康發(fā)育包括與食育教育的結(jié)合作為校園餐飲的第一目標(biāo)。校園餐飲是一個事業(yè),不是一門生意,但現(xiàn)有的管理體制和機制都是把學(xué)生作為消費者來看待的,那么他們自然就淪為各種不健康食品的消費者。
在我們這個越來越追求效率的時代,預(yù)制菜看似是順應(yīng)了潮流,便捷了生活,但若細(xì)想,預(yù)制菜似乎也側(cè)面地反映出工業(yè)化生產(chǎn)埋下的食品安全隱患,也改變了我們的飲食習(xí)慣。如果追問我們的食物結(jié)構(gòu)為什么會發(fā)生這樣的變化,就要追溯到全球化的食物體系和食物政治。為了讓讀者更好地了解這個話題,今天我們推送一篇2018年澎湃新聞與清華大學(xué)嚴(yán)海蓉老師的訪談。
采訪者&撰文|朱凡
受訪者 | 嚴(yán)海蓉 清華大學(xué)人文與社會科學(xué)高等研究所
圖片來源:百度
01
霸權(quán)與全球食物體系的形成
Q1
最近,一部叫做《風(fēng)味人間》的美食紀(jì)錄片大熱,它把中國食物放在歷史脈絡(luò)和全球視野當(dāng)中進(jìn)行呈現(xiàn),并且講述了很多傳統(tǒng)食物和當(dāng)?shù)仫L(fēng)土人情、食物與人、食物與自然之間的故事。這雖然是一部面向城市觀眾的商業(yè)紀(jì)錄片作品,但這些主題似乎和“人民食物主權(quán)”網(wǎng)絡(luò)一直想要傳達(dá)的理念存在不謀而合的地方?
嚴(yán)海蓉:的確,我覺得《風(fēng)味人間》特別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不僅是一個食物的影片,它呈現(xiàn)了食物如何溝通人與自然關(guān)系、人與人的關(guān)系,其中有自然之美、勞動之美、人情故事,這些元素的結(jié)合調(diào)動了觀眾的口腹,溫暖了大家的心情。但另一方面,它又讓人覺得,它所呈現(xiàn)的好像是夕陽中遠(yuǎn)去的牧歌、日落前即將消失的瑰麗。它對工業(yè)化農(nóng)業(yè)或者說工業(yè)化的食物體系抱有一種無可奈何的態(tài)度,所選擇呈現(xiàn)的是在陰影以外的美好光點。
“食物主權(quán)”網(wǎng)絡(luò)和它相似的地方是:我們都會很珍惜人類的創(chuàng)造性和食物的多樣性;不一樣的地方在于:我們認(rèn)為不僅要看到陰影之外的東西,也應(yīng)該正視陰影本身,更重要的是要直面問題的癥結(jié)。我們不但要引入歷史和文化的視野,也要引入食物的政治經(jīng)濟學(xué)。人們通常會把飲食習(xí)慣看作人們自發(fā)的選擇和追求,但是往往不是這樣的。
比如,與30年前相比,中國臺灣【下同】人均一年少吃40公斤米,而隨著稻米食用逐年下降,小麥的食用逐年上升,2016年小麥人均年食用量達(dá)到38公斤,追趕稻米的44.5公斤。臺灣的小麥主要從美國和澳大利亞進(jìn)口,臺灣的糧食自給率只有31%。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種情況?還有我們現(xiàn)在吃牛肉越來越多,在我小的時候吃牛肉是非常少的,可能一年都吃不到一次兩次,那么這些變化是怎么發(fā)生的?如果我們追問我們的食物結(jié)構(gòu)為什么發(fā)生這樣的變化,就要追溯到全球化的食物體系和食物政治。
全球食物體系的演變離不開世界霸權(quán)的影響。現(xiàn)在學(xué)術(shù)界已經(jīng)有關(guān)于“食物體系(food regime)”的研究,兩位學(xué)者Philip McMichael和Harriet Friedmann不約而同地發(fā)現(xiàn):第一代全球食物體系起于1871年,終結(jié)于一戰(zhàn)開始的1914年。這個食物體系以大英帝國為中心和主導(dǎo),隨著歐洲人到新西蘭、澳大利亞、加拿大、美國等國殖民,歐洲的飲食結(jié)構(gòu)在不同大洲進(jìn)行推廣,在這一過程中,英國資本在這些地區(qū)推動了單一化種植和糧食出口。隨著英國從這些國家的的糧食進(jìn)口,全球也第一次出現(xiàn)了常態(tài)化的長距離糧食運輸和貿(mào)易,這是一個非常重大的突變。
第二代全球食物體系起始于二戰(zhàn)結(jié)束的1945年,這是一個以美國霸權(quán)為主的食物體系。這一時期美國把本國大量過剩的糧食如小麥,通過冷戰(zhàn)外交變成食物援助提供給第三世界國家,同時把所謂的“綠色革命”——也就是使用化肥、農(nóng)藥、雜交種子的生產(chǎn)方式——以技術(shù)援助的名義推廣到第三世界國家,以消解“紅色革命”的可能性。綠色革命推動了第三世界農(nóng)業(yè)和農(nóng)村結(jié)構(gòu)的變化,加速了農(nóng)村社會的分化。當(dāng)然,美國本身也發(fā)生了變化:1916年美國有3350萬農(nóng)業(yè)人口,占當(dāng)時總?cè)丝诘?2%,到2006年美國農(nóng)業(yè)人口只有290萬,占總?cè)丝诘?%。在這一過程中,一方面農(nóng)民大量消失,小農(nóng)戶被大量排擠出去,另一方面農(nóng)民內(nèi)部也沒有停止分化。生產(chǎn)規(guī)模不斷擴大,1938年美國農(nóng)場平均162英畝,2006年達(dá)到446英畝,盡管如此,今天美國中小農(nóng)戶仍然難以依靠農(nóng)業(yè)維持生計,最近英國《衛(wèi)報》報道說,美國農(nóng)業(yè)已經(jīng)成為一個高風(fēng)險的行業(yè),美國農(nóng)民自殺率是美國所有行業(yè)中最高的。
當(dāng)我們看到全球食物體系和其中的權(quán)力關(guān)系,就會明白我們飲食結(jié)構(gòu)的改變,不是簡單的消費者自主選擇的問題。現(xiàn)在除了麥當(dāng)勞、肯德基的全球化,美國還推動中國購買更多的美國農(nóng)產(chǎn)品,我們的飲食習(xí)慣的改變受到了全球食物體系力量的推動,這是我們應(yīng)該正視的。
Q2
您剛剛講到的全球食物體系的變化可能是相對隱性的,我們更加有切身感受的變化可能還是國內(nèi)的一些變化。一方面,近年來城市中產(chǎn)對于“吃”這件事越來越熱衷, 也越來越重視食物與健康的關(guān)系,但另一方面,城市中人們的飲食越來越趨同,快餐、外賣是很多繁忙的都市人主要的飲食選擇,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種充滿矛盾的景象?
嚴(yán)海蓉:我認(rèn)為食物的快餐化、同質(zhì)化主要還是和資本的選擇有關(guān)系,而不是人們自己的選擇。我們在香港也是一樣,香港是全世界麥當(dāng)勞最密集的地方。在雇傭勞動中,人們經(jīng)常性的被加班,超時工作帶來的疲憊,競爭帶來的緊張,導(dǎo)致了“生產(chǎn)時間”擠壓“生活時間”,生活的創(chuàng)造性勞動,如做飯,不再是生活的日常。
快餐化、同質(zhì)化的食物其實并不透明、更不健康。這方面的揭露在美國有不少。有一本書叫“Salt Sugar Fat: How the Food Giants Hooked Us”(該書中文版《鹽糖脂:食品巨頭是如何操縱我們的》已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它是一個獲普利策獎的記者對美國食品工業(yè)進(jìn)行的調(diào)查和揭示。他發(fā)現(xiàn)食品工業(yè)靠制造口感來賺取利潤,口感可以通過鹽、糖、脂肪的調(diào)配來達(dá)到,但食物的營養(yǎng)怎么樣、對人們的健康有什么影響,這些問題故意被忽視了。所以今天人們追求多樣化、健康的飲食,恰恰是因為這些在主流的食品工業(yè)體系下難以獲得。這種看似矛盾的景象其實是當(dāng)下不同選擇、不同力量之間的一種斗爭。
《鹽糖脂:食品巨頭是如何操縱我們的》書封
Q3
這是不是也和口感可以直接被消費者感知,而營養(yǎng)成分和健康與否難以直接判斷有關(guān)?
嚴(yán)海蓉:確實有這方面的原因。我們對食物的認(rèn)知日趨簡化。其實我們的父母輩去菜場買菜的時候,他們的考量是多方位的,是不是應(yīng)季,什么東西老的好,什么東西嫩的好,等等。年輕人去買東西的時候,往往就是看它長得怎么樣,認(rèn)知被極大地簡化了。我們把對食物的認(rèn)知簡化為外觀和口感,因為我們丟失了關(guān)于食物的經(jīng)驗性的知識和技能。
02
工業(yè)化解決不了饑餓和營養(yǎng)的問題
Q4
陳曉卿導(dǎo)演在談到工業(yè)化的食物對傳統(tǒng)食物的取代時說這種現(xiàn)代化的趨勢是不可阻擋的,比如幾十年間種子的種類就從一千多種下降到了幾百種,人類趨利避害的本能決定了人在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都是在追求以更少的付出獲得更多的能量供給,因此紀(jì)錄片的作用就是記錄下這些“正在不斷消逝的傳統(tǒng)的背影”;還有一種更為極端的觀點認(rèn)為,這種對傳統(tǒng)的懷念是矯情的、不必要的,過去只有精英階層才能享受美食,普通人甚至連飯都吃不飽,正是工業(yè)化的化肥、農(nóng)藥帶來了糧食產(chǎn)量的提升,才讓千千萬萬的普通人生活質(zhì)量得到了提高,有了享受美食的機會,因此應(yīng)該擁抱工業(yè)化。您對這兩種觀點怎么看?
嚴(yán)海蓉:我們對食物的傳統(tǒng)不應(yīng)只是一種懷舊,而是應(yīng)該把它作為全人類共同的財富去珍惜、去繼承。自從有農(nóng)耕文化以來,人類曾經(jīng)通過勞動,培育了很多新的品種。然而,當(dāng)下我們面臨著一場巨大的物種消失悲劇,在過去50年里,世界喪失了70%的生態(tài)多樣性。2016年聯(lián)合國糧農(nóng)組織發(fā)表了一個關(guān)于世界糧食和農(nóng)業(yè)動物遺產(chǎn)資源狀況的報告,報告說每一年都有十個農(nóng)業(yè)物種滅絕。這種速度是非常驚人的,我覺得這絕不僅僅是人類趨利避害的本能所帶來的結(jié)果,而是工業(yè)化農(nóng)業(yè)體系帶來的副作用。有研究者認(rèn)為全球物種滅絕速度比自然滅絕速度快了1000倍,地球正在進(jìn)入第六次大滅絕時期。而導(dǎo)致這一悲劇的因素包括工業(yè)化農(nóng)業(yè)對單一種植的大規(guī)模推廣和農(nóng)藥化肥的大量使用。
至于應(yīng)該擁抱工業(yè)化的觀點,我覺得在上世紀(jì)上半葉,“綠色革命”確實帶來了糧食產(chǎn)量的提高等積極作用,但今天它的負(fù)面性越來越大。今天,我們面臨的不再是糧食產(chǎn)量不夠的問題,而是分配的問題。當(dāng)下,不管在工業(yè)領(lǐng)域還是農(nóng)業(yè)領(lǐng)域,都不是生產(chǎn)效率無法滿足人們需求的問題,而是分配問題、營養(yǎng)和質(zhì)量問題。食物分配存在著驚人的不公平。在全球糧食豐裕的情況下,有8億人口長期遭受饑餓,其中5億在亞洲。挨餓的人們往往在農(nóng)村,在生產(chǎn)糧食、甚至出口糧食的地方。
另外,今天的食物還存在熱量有余而營養(yǎng)不足的問題,這就跟工業(yè)化農(nóng)業(yè)的生產(chǎn)方式、跟利潤主導(dǎo)的食品產(chǎn)業(yè)有很大關(guān)系。一方面我們失去了多樣化的飲食結(jié)構(gòu),另一方面我們今天的蔬菜和水果所含有的營養(yǎng)成分跟半個世紀(jì)之前相比是大打折扣的。美國農(nóng)業(yè)部有長達(dá)半個世紀(jì)的農(nóng)產(chǎn)品營養(yǎng)跟蹤數(shù)據(jù),顯示農(nóng)作物中的營養(yǎng)成分有顯著下降,比如紅蘿卜的鐵含量下降24%,茄子的維生素C含量下降44%。如果現(xiàn)在有些人認(rèn)為工業(yè)化能解決饑餓和營養(yǎng)問題,這種說法在今天是不對的。
Q5
在全球化市場經(jīng)濟體系下,食物背后的更多關(guān)鍵性問題都被消費主義文化對口感、審美的渲染所遮蔽,例如城鄉(xiāng)割裂、食品安全、生態(tài)破壞。這些問題可能部分與中國的國情有關(guān),發(fā)達(dá)國家的現(xiàn)代化農(nóng)業(yè)是否也面臨類似的挑戰(zhàn)?有沒有找到應(yīng)對的方法?
嚴(yán)海蓉:我前面提到過,農(nóng)業(yè)是美國現(xiàn)在自殺率最高的一個行業(yè)。美國的農(nóng)業(yè)已經(jīng)是規(guī)模化的,但這并不能保障農(nóng)民的生計。很多農(nóng)民仍然受制于金融資本的壓榨,債務(wù)纏身,所以大部分美國農(nóng)民的日子其實不太好過。這和中國農(nóng)民的處境有相似之處,雖然我們的規(guī)模比較小,但也推崇單一化,農(nóng)業(yè)風(fēng)險也很高,增產(chǎn)不增收的情況并不少見。生態(tài)的破壞、生物多樣性的流失是全球性的問題。美國出現(xiàn)了蜜蜂大量死亡的情況,中國也有,這說明工業(yè)化農(nóng)業(yè)已經(jīng)給生態(tài)系統(tǒng)帶來了很大的破壞。在以利潤為主導(dǎo)的工業(yè)化食品體系下,食品安全問題美國同樣也有。美國有一個紀(jì)錄片叫做《食品公司》,網(wǎng)絡(luò)上可以看到中文字幕版,里面就記錄了一個美國兒童因為食用了含有0157-H7型艾氏大腸桿菌的漢堡而夭折,他的母親為此走上了艱難而曲折的維權(quán)之路。
《食品公司》紀(jì)錄片海報
至于城鄉(xiāng)割裂的問題,我們中國今天有幸還有巨大的農(nóng)村,中國的農(nóng)村人口雖然也在不斷流失,但農(nóng)村人口依然可觀。美國有農(nóng)場,但很難說美國還有鄉(xiāng)村社區(qū),他們已經(jīng)消滅了鄉(xiāng)村。進(jìn)入21世紀(jì),人類社會第一次城市人口超出鄉(xiāng)村人口。我們現(xiàn)在反思城鄉(xiāng)關(guān)系,鄉(xiāng)村對于社會整體來說、甚至對于整個人類來說到底有什么樣的意義,這個問題我覺得真的需要提出來了。過去把城鄉(xiāng)關(guān)系理解為鄉(xiāng)村的城市化問題,那么今天我們提需要城鄉(xiāng)平衡發(fā)展,那么如何承認(rèn)鄉(xiāng)村在社會發(fā)展中的意義。
還有對農(nóng)業(yè)本身的再思考問題,農(nóng)業(yè)到底應(yīng)該以怎樣的方式進(jìn)行生產(chǎn),農(nóng)業(yè)的多功能性要不要考慮。我們已經(jīng)習(xí)慣于把農(nóng)業(yè)看成商品經(jīng)濟,今天不管是否是主糧,所有的作物都成了經(jīng)濟作物。但事實上,自古以來農(nóng)業(yè)就有多種產(chǎn)出,它產(chǎn)出社區(qū),它產(chǎn)出文化,它產(chǎn)出多樣性,它維系一方水土,為什么這些產(chǎn)出都被遮蔽掉了?農(nóng)業(yè)只被作為一種貨幣經(jīng)濟(cash economy),甚至不是更廣泛的經(jīng)濟概念,這種對農(nóng)業(yè)極度簡化、單一化的看法帶來的后果是很嚴(yán)重的。
Q6
那在發(fā)展中國家是不是反而有一些沒有被工業(yè)化農(nóng)業(yè)侵占的、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保存較好的樣本?這些地方能給我們帶來怎樣的啟示?
嚴(yán)海蓉:相對來說,古巴的情況還是不錯的。古巴經(jīng)歷過從工業(yè)化農(nóng)業(yè)向生態(tài)農(nóng)業(yè)的轉(zhuǎn)化。古巴曾經(jīng)也是單一化、大規(guī)模的工業(yè)化農(nóng)業(yè),主要用于出口。蘇東陣營解體之后,古巴的對外貿(mào)易急劇下降,古巴的原油進(jìn)口大幅度減少。在這種情況下,古巴的農(nóng)業(yè)不能再走老路。所幸的是他們有社會主義制度,科學(xué)服務(wù)于社會,各個地方都有農(nóng)業(yè)技術(shù)站,生態(tài)農(nóng)業(yè)技術(shù)很快得到推廣,農(nóng)民和科學(xué)家一起實踐,結(jié)合了傳統(tǒng)和創(chuàng)新,最終實現(xiàn)了一個比較成功的轉(zhuǎn)換。現(xiàn)在,古巴百分之七八十的農(nóng)產(chǎn)品都是生態(tài)的方式生產(chǎn)出來的。這個案例告訴我們,不依賴石油和化工產(chǎn)品的農(nóng)業(yè)也可以養(yǎng)活人。
古巴是有意識、有計劃、有目的地發(fā)展生態(tài)農(nóng)業(yè),非洲一些地方不是積極主動的選擇生態(tài)農(nóng)業(yè),而是由于農(nóng)資成本比較高,所以還基本保留了傳統(tǒng)的生產(chǎn)方式。我在非洲調(diào)研最多的地方是贊比亞,那里的中國僑民經(jīng)常很自豪地說,我們這邊雖然消費方面物資比較缺乏,但我們這里有一樣國內(nèi)缺少的東西,就是食品安全。因為當(dāng)?shù)剞r(nóng)藥、化肥比較昂貴,所以農(nóng)民如果是自己生產(chǎn)、自己消費一般就不買農(nóng)藥、化肥,生產(chǎn)出來有多余的就拿到市場上去賣,有點像中國八十年代初的情況。非洲今天一方面有農(nóng)民組織比較活躍的爭取食物主權(quán)的活動,但另一方面很多非洲國家的政府還是在推綠色革命和單一化的種植,同時西方一些大的基金會,比如比爾·蓋茨基金會在非洲有發(fā)展援助,其中包括在非洲推廣轉(zhuǎn)基因作物。
03
生態(tài)農(nóng)業(yè)和合作經(jīng)濟如何突破現(xiàn)有體系
Q7
農(nóng)夫市集和社區(qū)支持農(nóng)業(yè)(CSA)近些年很受歡迎,這些場景下消費者能夠和生產(chǎn)者直接接觸,《舌尖上的中國》等美食紀(jì)錄片熱播后,人們熱衷去食物的原產(chǎn)地旅游、覓食、團購,這是不是一種對現(xiàn)有體系的突破?
嚴(yán)海蓉:最起碼他們是意識到了主流體制存在問題,去尋找另外的途徑,但我覺得要真正形成突破的話,還要在消費行為、消費過程中真正地認(rèn)識到生產(chǎn)的問題。購買少用或者不用農(nóng)藥化肥的食物只是切入點,還要看到生產(chǎn)中的人,思考如何跟農(nóng)民去對接。如果農(nóng)民的生產(chǎn)方式要轉(zhuǎn)向生態(tài)化,消費者是不是也應(yīng)該共同承擔(dān)轉(zhuǎn)換的成本?在這個轉(zhuǎn)換的過程中,消費者也有一個學(xué)習(xí)的過程,也應(yīng)該交一些學(xué)費,陪同生產(chǎn)者一起走過這個階段。如果消費者還是抱著要用最低的價格買最好的東西的態(tài)度,那么我們走不出目前的矛盾和怪圈。
臺灣的主婦聯(lián)盟在這方面做得是比較好的,她們有陪伴生產(chǎn)者的理念。當(dāng)生產(chǎn)者遇到災(zāi)害和困境的時候,主婦聯(lián)盟會的消費者和他們共同承擔(dān)風(fēng)險,這就超越了市場關(guān)系,這種和生產(chǎn)者的團結(jié),才是真正地支持農(nóng)民和農(nóng)業(yè)。
內(nèi)地的情況有點不一樣,但也有探索和創(chuàng)新。比如北京有一個目前規(guī)模還比較小的消費者團體,叫“北京食安聯(lián)盟”,他們的做法就是團購生態(tài)產(chǎn)品,會有意地對接一些正在發(fā)展中的合作社,以后有力量了還可以支持更多。這樣可以形成長期的生產(chǎn)和消費對接的關(guān)系,這是從城市發(fā)端對接農(nóng)村生產(chǎn)的一類實踐。而山西蒲韓鄉(xiāng)村是一個合作聯(lián)社,他們是作為生產(chǎn)方直接和城市消費者進(jìn)行對接,他們組織、教育城市消費者,告訴他們這些食物是怎么生產(chǎn)出來的、怎么烹飪才是健康的。非常有意思的是,它完全扭轉(zhuǎn)了一般的城鄉(xiāng)關(guān)系。在城鄉(xiāng)關(guān)系中,城市往往被看作是知識的供應(yīng)方,而鄉(xiāng)村是接受方,城市教育農(nóng)村,但在蒲韓鄉(xiāng)村組織城市消費者的時候,鄉(xiāng)村和農(nóng)民也是知識的提供者,他們還歡迎城市消費者去夏令營或者帶著孩子去認(rèn)識鄉(xiāng)村,鄉(xiāng)村就成為了知識共享的地方。第三種方式是像河南的黃河共富合作社,他們是城市消費者去農(nóng)村老家承包荒地,進(jìn)行共同耕作,用生態(tài)的方式生產(chǎn),然后共享,他們希望慢慢把周邊的農(nóng)村都帶動起來,發(fā)展生態(tài)農(nóng)業(yè)。這些探索都只是剛剛開始,蒲韓走在前面一些,但我覺得這些嘗試真的都是在突破現(xiàn)有的體系。
Q8
“食物主權(quán)”倡導(dǎo)以生態(tài)農(nóng)業(yè)和合作經(jīng)濟作為化工農(nóng)業(yè)和消費主義大潮下的另類出路,“人民食物主權(quán)”網(wǎng)絡(luò)剛剛召開了5周年年會,根據(jù)過去五年的調(diào)查研究,這條道路的可行性和目前的困境在哪里?
嚴(yán)海蓉:我先講一下“食物主權(quán)”探索的目標(biāo)是什么。我們提倡生態(tài)農(nóng)業(yè),提倡合作經(jīng)濟,基于的是對現(xiàn)下的食物體制的反思。我們在觀察今天面臨的挑戰(zhàn)時,比如說氣候變化問題、物種大量消失問題、人們的健康問題等等,所有這些都是相關(guān)聯(lián)的,我們發(fā)現(xiàn)生產(chǎn)關(guān)系仍然是核心問題,但除此之外還需要調(diào)整生態(tài)關(guān)系,也就是人和自然的關(guān)系。如果說生產(chǎn)關(guān)系關(guān)注的是生產(chǎn)當(dāng)中人與人的關(guān)系,那么我們也同時需要關(guān)注和反思生產(chǎn)方式,所以我們要反思工業(yè)化農(nóng)業(yè),不改變生產(chǎn)方式,也就無法改變?nèi)伺c自然的關(guān)系。
可行性在哪里?很多的基層實踐都顯示了可行性,比如蒲韓鄉(xiāng)村,再比如我們今年暑期調(diào)研的藏北嘎措集體經(jīng)濟。嘎措是牧區(qū),以前我們對牧區(qū)如何進(jìn)行生態(tài)的生產(chǎn)沒有概念,通過這次調(diào)研,我們看到了可行性。他們不僅可以做到生態(tài)生產(chǎn),而且牧民的食物收入加上貨幣收入還相當(dāng)高,這也就驗證了前面說到的我們今天面臨的不是生產(chǎn)問題,而是分配問題。在嘎措的集體經(jīng)濟里,大家都是相對平等、按勞分配,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的收入不僅遠(yuǎn)遠(yuǎn)高于周邊牧區(qū)鄉(xiāng)鎮(zhèn)的收入,也遠(yuǎn)遠(yuǎn)高于拉薩周邊農(nóng)民的收入。
嘎措放牧點上的牧民給綿羊擠奶
圖片來源:“人民食物主權(quán)”網(wǎng)站
反而“綠色革命”的負(fù)面性日趨顯著,面臨著不可持續(xù)性。綠色革命雖然一度提高了生產(chǎn)率,不是唯一的生產(chǎn)方式。中科院植物學(xué)家和生態(tài)學(xué)家蔣高明老師一直在帶領(lǐng)學(xué)生進(jìn)行農(nóng)業(yè)種植實驗,他的試驗田已經(jīng)能夠用生態(tài)的方式做到“噸良田”,也就是說一年兩季能夠生產(chǎn)1噸的糧食,已經(jīng)趕上了“綠色革命”的成績。不僅是中國有這樣的案例,法國資深電影人瑪麗-莫妮克·羅賓(Marie-Monique Robin)執(zhí)導(dǎo)了《未來的收成》這一紀(jì)錄片,展示了全球各地生態(tài)農(nóng)業(yè)的案例。就產(chǎn)出來說,一家有30年生態(tài)農(nóng)業(yè)經(jīng)驗的德國農(nóng)場產(chǎn)出與工業(yè)化農(nóng)業(yè)的產(chǎn)出基本相當(dāng),而且在干旱的時候更有優(yōu)勢。生態(tài)農(nóng)田還有綜合產(chǎn)出,除了作物以外,還生產(chǎn)了草料、樹木、糞肥、禽畜等資源,不僅資源循環(huán),而且還維護了當(dāng)?shù)氐纳鷳B(tài)、環(huán)境。
我們面臨最大的挑戰(zhàn)是,現(xiàn)下的食物體制本身有既得利益者群體,他們本身構(gòu)成了巨大的障礙,而且這樣的體制還有慣性,也不斷生產(chǎn)出消費主義的文化,這些都是需要我們在知識上去不斷解構(gòu)、在行動上不斷試圖改變的地方。
《未來的收成》紀(jì)錄片海報,該片旨在探討
“不用農(nóng)藥到底能不能養(yǎng)活全世界”
Q9
您剛才講到了畜牧業(yè)的情況,最近也有不少關(guān)于中國近海出現(xiàn)魚荒的報道,目前有沒有漁業(yè)當(dāng)中比較成功的生態(tài)實踐案例?
嚴(yán)海蓉:我國這方面的實踐可能還比較少。國內(nèi)有一家叫做“智漁”的非營利組織在做推動漁業(yè)可持續(xù)發(fā)展的工作。我的理解當(dāng)中,漁業(yè)的問題和農(nóng)業(yè)的問題有一些相似之處。一方面是過度捕撈帶來的魚荒的問題,另一方面是單一性、密集性的生產(chǎn)帶來的抗生素和各種藥物大量使用,從而帶來的食品安全問題。但生產(chǎn)方面如果要改變,我們就需要消費上的變革或革命。
我們過去把農(nóng)牧漁看作是可再生的行業(yè),但農(nóng)業(yè)現(xiàn)在面臨的問題是,物種的基因多樣性(gene base)在消失,土壤的有機質(zhì)也在大量流失。我國有些地方的土壤的有機質(zhì)甚至是零,也就是說如果不用化肥,這塊土地長不出東西來。我們對土壤表土的破壞遠(yuǎn)遠(yuǎn)高于它再生的能力,中國和美國都是如此,畜牧業(yè)也有草場退化的問題,這就說明我們已經(jīng)把農(nóng)業(yè)和畜牧業(yè)變成了和采掘業(yè)一樣不可再生的行業(yè),這是可持續(xù)發(fā)展面臨的嚴(yán)峻問題。
對于農(nóng)業(yè)、漁業(yè)這些資源性的行業(yè),能不能進(jìn)行計劃性的生產(chǎn)和消費?我們現(xiàn)在的生產(chǎn)和消費是無序和無度的,一方面拼命生產(chǎn),生產(chǎn)出來后又恣意浪費,這是對資源的浪費,對勞動的浪費。我交流過一些種糧專業(yè)戶,他們自己都希望農(nóng)業(yè)有計劃性。
我曾經(jīng)在挪威參訪過一個全國性的奶產(chǎn)品合作社,每一年合作社都代表全國的養(yǎng)殖戶和當(dāng)?shù)氐某羞M(jìn)行談判,定產(chǎn)量定價格,這樣接下來的一整年牧民都可以安安心心生產(chǎn),不像我們的農(nóng)民心里七上八下。生產(chǎn)和消費的無政府主義既傷害生產(chǎn)者、也無益于消費者,還不利于保護資源。資源性行業(yè)尤其需要生產(chǎn)和消費的計劃性,但不一定是我們過去計劃經(jīng)濟的方式,而是可以有多個主體參與協(xié)商,這就需要生產(chǎn)者和消費者的組織化,在生產(chǎn)、消費和生態(tài)環(huán)保團體充分協(xié)商的基礎(chǔ)上一起來談計劃。
Q10
前幾年流行的返鄉(xiāng)書寫中描寫的農(nóng)村都是凋敝的、空心化的,最近一段時間時常看到返鄉(xiāng)創(chuàng)業(yè)的報道,前幾天農(nóng)業(yè)農(nóng)村部的一個數(shù)據(jù)說目前返鄉(xiāng)創(chuàng)業(yè)人員達(dá)到了740萬,你們在調(diào)研中有沒有發(fā)現(xiàn)這種趨勢?這種變化能否為新三農(nóng)問題的解決帶來轉(zhuǎn)機?
嚴(yán)海蓉:返鄉(xiāng)創(chuàng)業(yè)的案例我們也看到一些,但返鄉(xiāng)創(chuàng)業(yè)愿意去做農(nóng)業(yè)的可能沒有從數(shù)據(jù)上看到的這么樂觀。人們可能覺得很多人在農(nóng)村有地,那回去種地就好了,其實不是這樣的,現(xiàn)在進(jìn)入農(nóng)業(yè)的門檻還是比較高的。而且農(nóng)民經(jīng)常遇到的問題,如果返鄉(xiāng)創(chuàng)業(yè)做農(nóng)業(yè)同樣也會遇到,比如價格不穩(wěn)定的問題。我們經(jīng)常聽說果農(nóng)種出來的水果賣不掉,要靠賣悲情去賣水果,這肯定是不可持續(xù)的。再比如,總體來說,我們中國的蔬菜生產(chǎn)已經(jīng)是過剩的。這些問題如果不解決,對于有志于返鄉(xiāng)創(chuàng)業(yè)做農(nóng)業(yè)的人來說都是一種障礙。
其實現(xiàn)在政府也在推集體經(jīng)濟,我們看到做得好的集體經(jīng)濟是有創(chuàng)造就業(yè)的能力的,不僅是在農(nóng)業(yè)方面,也可以是在農(nóng)產(chǎn)品加工方面。比如嘎措的集體經(jīng)濟不僅可以做畜牧業(yè),還可以做畜牧產(chǎn)品的加工,比如羊毛坎肩、羊毛背心等等;再比如貴州大壩村的集體經(jīng)濟,他們是種果樹,種果樹其實不需要那么多人,也確實存在勞動力的剩余,那么他們就做水果的加工,生產(chǎn)果酒。農(nóng)村需要人才,返鄉(xiāng)青年最突出的能力可能不一定都在種植方面,他們的能力是多元的,可能在組織和聯(lián)系城市方面比較有優(yōu)勢,我覺得集體經(jīng)濟是對接的比較好的一種方式。
我的想法是,是不是可以在政策方面進(jìn)行呼吁,把對新集體經(jīng)濟的提倡和返鄉(xiāng)創(chuàng)業(yè)結(jié)合起來?同時結(jié)合政府也在提倡綠水青山、生態(tài)文明。前面還提到資源性行業(yè)需要有計劃的生產(chǎn),這些也是生態(tài)文明的前提。所以,要給新三農(nóng)問題帶來轉(zhuǎn)機,其實需要的是一個整體關(guān)系的大調(diào)整。
完
「 支持烏有之鄉(xiāng)!」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wǎng)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wǎng)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xiāng)網(wǎng)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