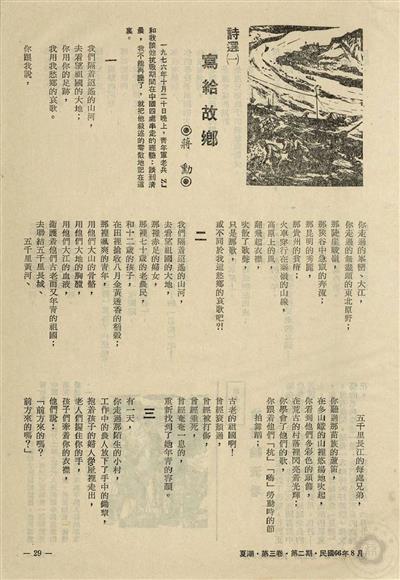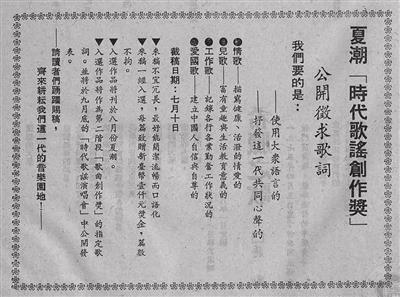摘要:蔣勛1977年發(fā)表于《夏潮》雜志的新詩《寫給故鄉(xiāng)》,經(jīng)李雙澤改編后,成為20世紀(jì)70年代臺灣傳唱一時的新民歌佳作《少年中國》。從詩到歌的轉(zhuǎn)化,體現(xiàn)了李雙澤通過音樂、繪畫和文學(xué)寫作對時代所需文化意識和青年自我的探索。《夏潮》雜志推動的新詩建設(shè)與“唱自己的歌”運動,承載了關(guān)懷現(xiàn)實、連接大眾的文化思潮之意涵與價值。
————————————————
20世紀(jì)70年代是中國臺灣“經(jīng)濟起飛”、從農(nóng)業(yè)為主的社會向現(xiàn)代工商業(yè)社會轉(zhuǎn)型的年代,也是歷經(jīng)“保釣”、國民黨威權(quán)體制松動、黨外運動興起等政治變動的年代,知識界隨之萌生強烈的自省意識,掀起了關(guān)懷現(xiàn)實、回歸鄉(xiāng)土的潮流,廣泛波及文學(xué)、繪畫、舞蹈、音樂等領(lǐng)域。就音樂領(lǐng)域而言,現(xiàn)代民歌運動逐漸成為一股潮流,在當(dāng)時市井流行的“甜歌”與改編自日本的閩南語歌曲、知識青年熱衷的英美熱門音樂以及官方推行的“凈化歌曲”之外,開辟了一處新的空間,不但為樂壇帶去新鮮的空氣,也與70年代臺灣一系列社會文化事件,如現(xiàn)代詩論戰(zhàn)、鄉(xiāng)土文學(xué)論戰(zhàn)等彼此呼應(yīng),構(gòu)成隱約的互文關(guān)系。
如果將20世紀(jì)70年代的臺灣現(xiàn)代民歌運動視為一江春水,那么以楊弦為代表的中國現(xiàn)代民歌運動與李雙澤發(fā)起的“唱自己的歌”運動分別構(gòu)成了兩條主要支流。楊弦主要將余光中的詩譜曲演唱,李雙澤則改編演唱陳秀喜、蔣勛等人的詩。繼20世紀(jì)60年代臺灣現(xiàn)代詩派強調(diào)詩與歌相分離后,詩與歌又再度結(jié)合。其中,“唱自己的歌”運動恰逢其時地成為70年代后期臺灣左翼力量在上下求索中的突破口,并獲得當(dāng)時隱含左翼立場的《夏潮》雜志的支持與推動。
1976年,30歲的蘇慶黎接手創(chuàng)辦不久的《夏潮》雜志,擔(dān)任總編輯。蘇慶黎是日據(jù)時代老臺共蘇新之女,她聯(lián)合陳映真、陳鼓應(yīng)等人,在白色恐怖時期的臺灣以“社會的、鄉(xiāng)土的、文藝的”為旨?xì)w,嘗試辦一份“社會主義的雜志”1。《夏潮》創(chuàng)辦時,臺灣現(xiàn)代詩論戰(zhàn)已落下帷幕,但新詩該往何處去,仍有待創(chuàng)作與批評的雙重實踐去界定。《夏潮》雜志上不斷回蕩著論戰(zhàn)的余音,它所刊登的詩評、詩作反映出與現(xiàn)代主義詩歌迥異的美學(xué)傾向。然而,《夏潮》推動的現(xiàn)實主義新詩創(chuàng)作雖然取得了一定成績,但批評與創(chuàng)作之間仍然存在落差。《夏潮》雜志寄寓新詩連接大眾、連接時代的功能,轉(zhuǎn)而通過詩與歌的結(jié)合,借助“唱自己的歌”運動得以繼續(xù)探索。2
01
從詩到歌:《寫給故鄉(xiāng)》與《少年中國》
20世紀(jì)70年代,留學(xué)法國的蔣勛曾寫下一組同題詩《寫給故鄉(xiāng)》,表達(dá)海外游子對家園、母親的懷念,其中第三首作于1976年10月,發(fā)表于《夏潮》1977年8月號“詩選”專欄。
《夏潮》并非一本專門的詩刊,但由于現(xiàn)代詩論戰(zhàn)的反對派旗手唐文標(biāo)與《夏潮》關(guān)系密切,加上《夏潮》核心成員陳映真持續(xù)關(guān)注新詩發(fā)展,使得《夏潮》與20世紀(jì)70年代末臺灣新詩走向關(guān)系匪淺。《夏潮》的出現(xiàn),對于破除六七十年代臺灣現(xiàn)代詩以詩社為中心的發(fā)展模式有積極作用,它所推出的“詩選”專欄,為這一時期帶有現(xiàn)實主義色彩、左翼關(guān)懷的新詩提供了為數(shù)不多的發(fā)表園地。同時,《夏潮》廣泛譯介第三世界反帝、反殖、反戰(zhàn)的詩歌,并發(fā)掘刊登日據(jù)時期具有反抗精神的詩作,包括賴和、楊華、王白淵、楊逵、王昶雄等人的詩,進(jìn)而通過推動詩歌批評、組織座談會等形式,引導(dǎo)新詩的發(fā)展方向。
蔣勛是《夏潮》上發(fā)表詩作數(shù)量最多的詩人3。他少年時代結(jié)識了擔(dān)任英文教師的陳映真,在后者影響下,逐漸走出對當(dāng)時盛行的現(xiàn)代主義文學(xué)的沉迷,重塑了自己的文學(xué)觀。420世紀(jì)70年代初,蔣勛負(fù)笈巴黎,以繪畫、藝術(shù)史為研究方向。返臺后,他成為《夏潮》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不僅關(guān)注新詩、繪畫、舞蹈、新民歌等議題,也撰寫“老國民感懷錄”專欄,假托“老國民”的身份,針砭社會文化現(xiàn)象。1977年起,蔣勛擔(dān)任《雄獅美術(shù)》主編,將該刊拓展為一份融匯美術(shù)、建筑、戲劇、文學(xué)等領(lǐng)域的綜合刊物,并時常與《夏潮》聯(lián)動,共同對70年代的社會現(xiàn)象、社會問題發(fā)聲。
蔣勛:《寫給故鄉(xiāng)》,《夏潮》第 3 卷第 2 期
在《寫給故鄉(xiāng)》的序跋中,蔣勛交代了寫作緣起:“我”在留學(xué)期間聽一位國民黨青年軍老兵徹夜講述年輕時的抗戰(zhàn)經(jīng)歷,心有所感,于是寫下這首長詩。全詩共九十七行,分成四節(jié)。第一節(jié)寫青年軍老兵在抗戰(zhàn)中縱橫馳騁,地理空間的更迭彰顯出祖國山河的壯美,而山河之美又與收復(fù)國土的昂揚意氣相互激發(fā)。第二節(jié)轉(zhuǎn)入祖國大地上的人民,引出“古老的中國”“重新找到了她年青的容顏”等語,凸顯“古老”與“年青”對立統(tǒng)一的關(guān)系。第三節(jié)寫老兵在陌生小村受到熱情歡迎,抗戰(zhàn)將軍民緊緊連在一起,詩人詠嘆“少年的中國啊!/你沒有學(xué)校,/你的學(xué)校是祖國的大地山川,/你沒有老師,/你的老師是這母親的撫愛……是這世代生活著、/頑強地生活著、/用他們的犁鋤改變了中國大地的人們”,這里“少年的中國”與第二節(jié)“古老的中國”相對,既指抗戰(zhàn)末期,經(jīng)歷了戰(zhàn)爭洗禮,軍民一心、迎接勝利曙光的中國,也指未來的、正在形塑中的新中國。第四節(jié)轉(zhuǎn)入抒情主體“我”的自責(zé),老兵的講述令其反躬自省,最后以“多淚的鄉(xiāng)愁”收尾。
詩中的“我”(蔣勛自指)是一位漂泊海外的臺灣外省青年。蔣勛1947年出生在西安,幼年赴臺,在臺灣長大。由于對祖國大陸缺少源自生命經(jīng)驗的體認(rèn),詩中“我”的鄉(xiāng)愁顯然是間接的、被喚起的,混雜著青年軍老兵浪漫化的青春記憶與詩人的想象,不過,蔣勛這首詩并沒有因為這“間接的”情感而隔膜、虛弱,反而情緒飽滿、感染力極強。那么,究竟是什么支撐起了這首詩?
老兵與蔣勛,即“你”與“我”的對位,鋪設(shè)了全詩的基本結(jié)構(gòu)。“你”與“我”鏡照出兩代知識青年截然不同的人生際遇:老一代知識青年在“十萬青年十萬軍”的號召下參軍抗日、保家衛(wèi)國,為收復(fù)國土浴血奮戰(zhàn)5;新一代知識青年則漂泊異國,在酒精的麻醉下啃噬鄉(xiāng)愁。詩中,“你”用自己的足跡深入祖國的大地和人民,“我”卻只能通過多淚的哀歌、鄉(xiāng)愁同祖國和人民發(fā)生關(guān)聯(lián)。貫穿全詩的是兩種相互交織的情感基調(diào):一是老兵激昂的青春記憶,熱情飛揚;一是“我”的“鄉(xiāng)愁”與“哀歌”,浸染著自責(zé)與焦灼,為整首詩抹上感傷虛無的底色。對照青春時代的老兵,“我”之狀態(tài)似乎正是由于疏離了故鄉(xiāng)、人民而造成的。“我”和老兵兩種截然不同的人生、情感基調(diào)疊合,構(gòu)成鮮明對照,既打開了詩中的情感張力,也豐富了情感的層次,整首詩因此讀來感情充沛而豐盈。
換個角度看,籠罩全詩的“鄉(xiāng)愁”并不必然是詩人“間接的”情感,而是“直接的”切身之痛。事實上,鄉(xiāng)愁不但籠罩于當(dāng)時的臺灣社會,而且?guī)缀跏俏ㄒ荒茉谕?quán)統(tǒng)治下訴之于眾的集體情感,因此它成為20世紀(jì)五六十年代臺灣文學(xué)藝術(shù)廣泛表現(xiàn)的母題,尤以詩壇為甚,涌現(xiàn)出大量描寫鄉(xiāng)愁的名篇,以余光中的《鄉(xiāng)愁四韻》《鄉(xiāng)愁》等最為知名。到了70年代,在臺灣回歸鄉(xiāng)土的潮流中,“鄉(xiāng)土”與“鄉(xiāng)愁”愈發(fā)彼此纏繞,但余光中這一代人筆下以鄉(xiāng)愁為核心的鄉(xiāng)土,在題材、情懷與表達(dá)形式上同臺灣社會現(xiàn)代化進(jìn)程中成長起來的新一代外省人的生命體驗已逐漸拉開差距。
作為一種頗具時代征候性的情感,鄉(xiāng)愁無疑也在第二代臺灣外省人特別是20世紀(jì)70年代負(fù)笈海外的臺灣青年留學(xué)生心頭郁積,但其表現(xiàn)形式已經(jīng)發(fā)生變化。這些青年大多同蔣勛一樣在臺灣長大,從小接受的是以“大中國”情結(jié)為出發(fā)點的國民黨政府民族主義教育,再配以“回鄉(xiāng)”“光復(fù)大陸”為目標(biāo)的文化政策,這一代青年在故鄉(xiāng)臺灣與故鄉(xiāng)大陸間有“混淆而復(fù)雜的情緒”6。相比第一代外省人,第二代關(guān)于“故鄉(xiāng)”“鄉(xiāng)愁”的指向遠(yuǎn)為混雜、曖昧,而70年代臺灣政治情勢的變動,無形中讓鄉(xiāng)愁的滋味更趨復(fù)雜。蔣勛的同題詩《寫給故鄉(xiāng)》(1974年11月)就刻畫了鄉(xiāng)愁在新一代外省人身上引發(fā)的失語焦慮:“如果再問我一次:/‘哪兒是你的故鄉(xiāng)?’/我還說是長安嗎?/我還說是臺北嗎?/如果再問我一次:/‘哪兒是你的故鄉(xiāng)?’/我該怎么說呢?”
發(fā)表于《夏潮》的《寫給故鄉(xiāng)》雖然仍有游子哀歌的痕跡,但詩中“你”“我”兩代人對照的表現(xiàn)形式,已同余光中等老一輩詩人有所區(qū)別,特別是第四節(jié)加入詩人一連串的自責(zé)、自省,內(nèi)中已經(jīng)隱含了對沉溺鄉(xiāng)愁、對海外虛擲歲月的懷疑,而隨后詩中勾勒出大平原的建設(shè)、為民眾獻(xiàn)出生命的少年等意象,則隱約指出新一代青年在鄉(xiāng)愁之外,情感與行為可能的旨?xì)w。與鄉(xiāng)愁的哀歌相比,這首詩中的情感有著更為豐富與飽滿的向度。
此外,《寫給故鄉(xiāng)》的感染力一定程度上也來自詩中的修辭效果。起首四行詩“我們隔著迢遙的山河,/去看望祖國的大地;/你用你的足跡,/我用我愁鄉(xiāng)的哀歌”在全詩中數(shù)次重復(fù),營造出一種回環(huán)往復(fù)的律動,讀來余韻悠長。全詩整體上采用無韻的自由體,唯獨這四行詩運用規(guī)律的“abba”式抱韻,呈現(xiàn)出富有格律的音樂之美,強化了情感的表達(dá)效果。7這些詩行中蘊藏的音樂性,或許正是吸引李雙澤,促使他將詩改編成歌的原動力,上述四行詩也因此在《少年中國》歌詞中得到延用,構(gòu)成了歌曲的主體部分。
陳映真曾評價蔣勛的詩是“第一個按著在批評現(xiàn)代詩中建立起來的新詩的哲學(xué)而寫詩,并獲至初步的、優(yōu)秀成績的作品”8。蔣勛的詩語言通俗、直抒胸臆,表現(xiàn)手法多為一種融合了浪漫主義的現(xiàn)實主義。他格外鐘愛排比,如詩中“用他們大地的骨骼,/用他們大山的胸膛,/用他們大江的血液,/衛(wèi)護著他們古老而又年輕的祖國;/去聯(lián)結(jié)五千里長城、/五千里黃河、/五千里長江的每處兄弟”等句,便借排比、反復(fù)的手法渲染情感,句式天然帶有連綿的音樂感,陳映真就曾說過,蔣勛的詩句每每使他想起李雙澤的歌。9
蔣勛與李雙澤同屬活躍在《夏潮》《雄獅美術(shù)》等雜志上的青年撰稿人。《寫給故鄉(xiāng)》在《夏潮》發(fā)表的那個夏天,李雙澤正埋首于新歌創(chuàng)作,籌備開學(xué)后在淡江校園舉辦的演唱會。9月10日,李雙澤在淡水海邊因救人不幸溺水身亡,友人從其遺物中發(fā)現(xiàn)了一組新歌,包括《少年中國》的歌詞與曲譜。
《少年中國》歌詞大幅改寫了蔣勛的《寫給故鄉(xiāng)》。首先,李雙澤刪掉原詩中的大量內(nèi)容,包括序與跋、詩中對祖國多元地理空間與各地人民的描寫,以及抒情主體的自我反省。詩中昆明、貴州等地在歌詞中替換成泛指的“大地”,老弱婦孺、善歌的苗族勞動者等形形色色的人物也替換成泛指的“人民”。其次,最顯著的不同體現(xiàn)在李雙澤改編的副歌部分—“你對我說/古老的中國沒有鄉(xiāng)愁/鄉(xiāng)愁是給沒有家的人/少年的中國也不要鄉(xiāng)愁/鄉(xiāng)愁是給不回家的人”10。經(jīng)此改寫,蔣勛詩中抒情主體的情感基調(diào),也即“我”的鄉(xiāng)愁的哀歌被陡然翻轉(zhuǎn)。原詩昂揚與感傷交織的雙重情感基調(diào)轉(zhuǎn)向創(chuàng)傷主體的治愈與超越—起首以低沉的曲調(diào)吟唱出鄉(xiāng)愁的感傷,副歌部分又以逐漸抬高的音階揚棄鄉(xiāng)愁,面向歌者與聽眾發(fā)出召喚,邀請他們參與少年中國的進(jìn)程。改編后的歌詞強化了“少年中國”的意象,前引原詩第三節(jié)的詩行被簡化為“少年的中國有新的學(xué)校/她的學(xué)校是大地的山川/少年的中國有新的老師/她的老師是大地的人民”11;進(jìn)一步凸顯“古老的中國”與“少年的中國”對立統(tǒng)一的關(guān)系,將二者視為精神與身體的棲居之所—前者是炎黃子孫永恒的精神與文化家園,后者則包含對未來中國的憧憬—其中,少年中國“以大地為學(xué)校,以人民為老師”的觀念浸潤了左翼民族主義理想,是“我們”建設(shè)的方向。
《少年中國》編曲以漸進(jìn)的升調(diào)滌蕩了鄉(xiāng)愁中的感傷,12以明快的節(jié)奏吟唱出副歌“少年的中國也不要鄉(xiāng)愁/鄉(xiāng)愁是給不回家的人”,將鄉(xiāng)愁所負(fù)載的情感包袱輕輕甩開,引導(dǎo)歌者與聽者走出哀傷的情感基調(diào),認(rèn)識到自己是有家、有故鄉(xiāng)、有歷史的,進(jìn)而去嘗試重新與大地以及大地上的人民連接,歌曲努力召喚聽者積極樂觀的情緒,引發(fā)共鳴。細(xì)聽楊祖珺、胡德夫演唱的《少年中國》,開場的音調(diào)沉郁緩慢,其后逐步上揚,副歌部分益發(fā)昂揚,煥發(fā)著生命的熱情。
民謠作為一種音樂形式,結(jié)構(gòu)、旋律大多簡單。李雙澤改編的歌詞也與這一特性貼近,既簡潔明了,又易學(xué)易唱。從詩到歌,特別是從《寫給故鄉(xiāng)》那樣包含豐富細(xì)節(jié)的長詩,到朗朗上口的民謠,精簡幾乎是必由之路。同時也因為這種簡化,歌詞的能指更趨抽象,所指更趨寬泛。在形式上,改編后的《少年中國》句式整齊、簡潔而富有韻律,更適于演唱;在情感基調(diào)上,原來的雙線交織變?yōu)閱尉€的情緒流動,從鄉(xiāng)愁的感傷逐步過渡到積極昂揚,更容易把握。
李雙澤離世后,歌手胡德夫、楊祖珺共同錄制了這首《少年中國》。楊祖珺談道:“我和胡德夫節(jié)拍愈唱愈快、音階愈升愈高,升半音、又升半音、再升半音…。抓到了、抓到了,我心中充滿了大歡喜……怎么一直沒有想通過,我的中國就在腳下呢?”13
20世紀(jì)70年代,面對進(jìn)退失據(jù)的國際環(huán)境和國民黨“反攻大陸”的宣傳破產(chǎn),臺灣知識青年普遍遭遇認(rèn)同危機,楊祖珺的話頗有代表性。《少年中國》恰好切中了這一時代征候,給出了令人鼓舞的答案。從立足當(dāng)下、面向未來而生出的積極情緒,取代了“鄉(xiāng)愁”的感傷哀歌。就從詩到歌、從可讀到可唱的轉(zhuǎn)化而言,李雙澤對蔣勛詩作的改寫應(yīng)該說是成功的,甚至蔣勛也受此影響,將自己的第一本詩集命名為《少年中國》。
02
李雙澤與“自己的”歌
20世紀(jì)70年代臺灣民歌運動所提倡的并非傳統(tǒng)意義上的“民歌”,而是“現(xiàn)代民歌”或“創(chuàng)作民謠”。李雙澤曾談到,創(chuàng)作民謠是“作曲以民謠的形式—樸實無華的詩詞、簡單優(yōu)美的旋律創(chuàng)作出來的民謠歌曲”14。這次運動本質(zhì)上是一場以現(xiàn)代民歌為中心、由知識分子發(fā)起的自覺運動。其中,楊弦、余光中推動的中國現(xiàn)代民歌運動與李雙澤“唱自己的歌”運動在今天有關(guān)臺灣民歌運動的表述中常被混為一談,但二者在意識形態(tài)、音樂表現(xiàn)形式、傳播方式上都有所不同,雙方對于何謂“自己的”理解也并不一致。本節(jié)結(jié)合李雙澤的生命歷程,著重討論“自己的”歌之于李雙澤的意義。
李雙澤祖籍福建晉江,1949年生于菲律賓,幼年抵臺定居,中學(xué)開始習(xí)畫、彈吉他;1968年考入淡江文理學(xué)院,1973年肄業(yè);1974年受美新處資助舉辦個人畫展,同年任《明日世界》雜志社美編。1975年,李雙澤前往西班牙、美國游歷,1976年10月返回臺灣,11月30日撰寫《歌從那里來?》一文,稱“我們無能,我們這一代無法唱出自己語言的歌……我們這一群人腦袋里的音符詞匯真被強奸了”15。12月3日,淡江校園舉辦西洋民謠演唱會,李雙澤上臺詰問:我們中國人為什么不唱自己的歌?并在一片噓聲中演唱了“國父紀(jì)念歌”及“補破網(wǎng)”等閩南民謠,此即為“淡江事件”,事后迅速在校園內(nèi)外引發(fā)熱議,成為“唱自己的歌”運動的起點。事后不久,李雙澤出發(fā)前往菲律賓,數(shù)月后返回臺灣,致力于新歌創(chuàng)作。
自20世紀(jì)50年代起,隨著美軍駐守臺灣、臺灣美軍俱樂部的興建與“美軍電臺”的創(chuàng)辦,美國流行音樂排行榜上的熱門音樂也涌入臺灣,搖滾樂和英美民謠相繼流行,其中一些歌曲帶有反抗意識和人道訴求,為戒嚴(yán)時期的臺灣青年提供了一定的精神養(yǎng)料,但它們的流行也帶來諸多問題。李雙澤以當(dāng)頭棒喝的方式,喚醒了對這一現(xiàn)象未加反思的人。“淡江事件”之所以成為一樁標(biāo)志性事件,并非因為它是李雙澤個人不滿的宣泄,而是因為它符合臺灣當(dāng)時民族主義、回歸鄉(xiāng)土的社會潮流,反映了20世紀(jì)70年代青年對本民族新的文化形式、文化內(nèi)容的期待。事件之后,李雙澤進(jìn)一步指出,西洋音樂的流行表現(xiàn)出在文化層面上缺乏自我認(rèn)識,疾呼:“我們民族的歌到底淪落到怎樣一個地步了?”16在這一努力下,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guān)注這一問題。20世紀(jì)60年代一度熱衷英美歌曲的陳映真在1977年也撰文指出西洋民謠“畢竟是他人的東西”,不能滿足人們“對自己民族心聲的饑餓”。17
青年撰稿人毛鑄倫曾談道:“李雙澤所做的事,使我乍然覺悟,長此以往地……借美國人的東西發(fā)泄中國人的情緒的現(xiàn)象,包含了太多可怕的意義和后果,它會使我們?nèi)绶怯顾拙褪菓卸瑁趸蚨呒鎮(zhèn)洹V袊巳狈ΜF(xiàn)實的與本土的情感反映,這是可悲與危險的。”18聽李雙澤的歌,他體會到“像被電擊般地感動”,由于對美國歌曲的崇拜“所造成抑壓內(nèi)在的情緒,也就在那片刻中悄悄地解開,整個心靈因輕松而愉快起來”。19李雙澤有意識地通過新歌創(chuàng)作去同自身所處的時代與人相連接,用帶有民族意識的歌聲明確身份認(rèn)同,推動主體的重塑,這在和毛鑄倫一樣的知識青年中尤見成效。
李雙澤
事實上,李雙澤本人同樣走過一條崎嶇的路,他短暫的一生,折射出當(dāng)時臺灣左翼青年主體在白色恐怖與新殖民主義內(nèi)外夾擊之下痛苦成形的過程。李雙澤一度熱衷于英美新民謠,后來轉(zhuǎn)而創(chuàng)作“自己的”歌,這一轉(zhuǎn)變被他的師友稱作“覺醒”“覺悟”20,其過程并非一朝一夕,而是伴隨著他者的祛魅與自我主體的緩慢生成。李雙澤在繪畫領(lǐng)域的祛魅經(jīng)驗,實際上較音樂更早。臺灣當(dāng)代美術(shù)界深受歐風(fēng)美雨浸淫,自20世紀(jì)50年代末,現(xiàn)代主義開始盛行,在手法、透視角度、用色上大多奉西方繪畫為圭臬。畫家為了贏得國際買家的青睞,有的追求全盤西化,有的則回頭翻檢民族的、傳統(tǒng)的形式,并用“現(xiàn)代”的手法重新包裝,致使繪畫與現(xiàn)實生活脫節(jié),畫壇陷入虛假繁榮。李雙澤自中學(xué)開始學(xué)畫,一度深陷當(dāng)時流行的印象派窠臼,進(jìn)入大學(xué)后,在建筑系老師顧獻(xiàn)樑的指導(dǎo)下,逐漸走上寫實路線,開始摸索自己的風(fēng)格。21
大學(xué)期間,李雙澤一度醉心美國民謠,同胡德夫等人獻(xiàn)唱于臺北的民歌咖啡廳,他尤其擅長演繹鮑勃·狄倫(Bob Dylan)的歌。從1972年起,李雙澤在《淡江周刊》等雜志發(fā)表有關(guān)西洋搖滾樂、民謠的系列文章,此時他已在思考英美搖滾樂與民謠的生產(chǎn)傳播機制及其為戒嚴(yán)時期的臺灣青年所打開的空間,并開始關(guān)注英美歌曲流行所帶來的問題。22歌曲作為一種音樂藝術(shù)形式,必然是特定語言、文化與意識形態(tài)的產(chǎn)物,李雙澤很快便不滿足于只唱西洋歌曲,1973年底,他開始與胡德夫“一起努力著要做自己的歌,要唱自己的歌”23。
李雙澤對狄倫的情感其實相當(dāng)復(fù)雜,既受其滋養(yǎng),又渴望擺脫其影響。在李雙澤看來,狄倫及其所代表的英美民謠是英美現(xiàn)代藝術(shù)中最具“生命力和連貫性”的,能夠使人理解“年輕人所思所行”。24與此同時,李雙澤也清楚地看到狄倫的局限,他真正服膺的是狄倫的精神導(dǎo)師、美國左翼民謠之父伍迪·格思里(Woody Guthrie)。格思里一生坎坷,身背一把吉他走遍美國,為社會最底層的民眾歌唱,他不僅是民謠歌手,也是民眾的代言人。25而狄倫則是一個反叛者,這讓他很難真正為民眾發(fā)聲,他追求個人自由,擅長“標(biāo)題音樂”,卻屢次試圖撕掉“抗議歌手”的標(biāo)簽,他只代表他自己。26
李雙澤復(fù)雜的狄倫情結(jié),集中體現(xiàn)在他1976年撰寫的自傳性短篇小說《安·卡芮絲曼》中:“我”原是一個因為“終于到了紐約”27而熱淚盈眶的臺灣青年,如朝圣般住進(jìn)紐約格林威治村,在街頭彈唱狄倫的歌。出于對迪倫共同的愛,“我”同一位美國女孩發(fā)生了一段浸潤著波西米亞氣息的異國之戀,但“我”在歐美游歷中日益轉(zhuǎn)變,“我真的還是喜歡狄倫—只是我不愿唱狄倫的歌了”28。“我”最終告別戀人,重返臺灣。小說不曾透露“我”之轉(zhuǎn)變的原因,但結(jié)合李雙澤《方霜》一文中歐洲青年也唱英美歌曲的內(nèi)容,29可以推知他對英文歌在不同地區(qū)流行背后的世界經(jīng)濟政治與軍事格局逐漸有所認(rèn)識,開始反思英美民謠傳播背后隱含的新殖民形態(tài)。
正如小說所提示的,李雙澤在歐美的游歷無疑加速了這一祛魅過程。李元貞曾談到李雙澤出國前后的變化:“出國前的我們,……向往出國,以為西方樣樣都比我們優(yōu)秀,西方的技巧和思想是唯一的文化準(zhǔn)則。等到出國后,我們看清了國際現(xiàn)30勢,所謂文化的準(zhǔn)則是跟政治勢力結(jié)合的,是跟帝國主義的經(jīng)濟體系相結(jié)合的,美感也是依附在大拳頭之下的。”31如前所述,李雙澤出國前已有所反思,未必信奉“西方的技巧和思想是唯一的文化準(zhǔn)則”,但海外的游歷顯然令他正在萌生的民族意識進(jìn)一步向縱深發(fā)展。“上國”的所見所聞不斷刺激著他的神經(jīng),他一面以詼諧的口吻質(zhì)疑“美國的月亮比臺灣的大”32,一面以諷刺的筆觸刻畫一組漂泊海外的臺灣同鄉(xiāng)群像,如對印象派情有獨鐘的美術(shù)老師(《陳老師》)、選擇留在西班牙鍍金的青年(《阿B的》)、甘愿在美國中餐館端盤子的數(shù)學(xué)博士(《假如蘋果is長在松樹上》)等。中西落差所造成的集體性精神創(chuàng)傷與時代病,促使他返身思考臺灣社會的問題。而西方社會中的一些閃光之處,他也拿來借鑒,以期對臺灣社會有所助益(《我所看到的歐美青年》)。
同時,海外游歷充分打開了李雙澤的視野,異域的經(jīng)驗讓他格外留心第三世界弱小民族的生存狀況。無論是作為歐洲境內(nèi)的“非洲”的西班牙33,還是有著多難歷史的菲律賓,都令李雙澤心有戚戚。他深入其中,了解其政治、經(jīng)濟、歷史狀況和社會現(xiàn)實,撰寫《陽光下的陰影·西班牙點滴》《菲律賓探幽》《菲律賓站起來!》等系列文章,討論西班牙的貧富差距、佛朗哥的獨裁統(tǒng)治與菲律賓遭受殖民壓迫的歷史與現(xiàn)實等議題。他最出色的小說《終戰(zhàn)の賠償》(獲1978年吳濁流文學(xué)獎)更觸及了殖民經(jīng)驗的復(fù)雜性及其加諸民族性的多重創(chuàng)傷等深層問題。
西班牙、菲律賓固然在歷史與現(xiàn)實的糾葛中舉步維艱,發(fā)達(dá)的西方“上國”亦非天堂。李雙澤的小說《阿金外史》反映美國年輕一代的精神危機、家庭關(guān)系淡薄,以及傳媒淪為資本權(quán)力附庸等問題。就藝術(shù)領(lǐng)域而言,歐美的游歷則讓李雙澤意識到西方不斷涌現(xiàn)的藝術(shù)理論、繪畫潮流及其背后一整套藝術(shù)生產(chǎn)方式不僅受意識形態(tài)、價值觀和社會風(fēng)氣制約,更被資本所挾持,因此遠(yuǎn)非理想的范式。34
20世紀(jì)70年代的臺灣,既背負(fù)著殖民的歷史,也面臨著新殖民主義的入侵,這樣的歷史與現(xiàn)實不斷影響臺灣的知識文化生產(chǎn)。那么,是否存在替代性的知識文化生產(chǎn)方式,去整理自身經(jīng)驗、檢視并清創(chuàng)殖民傷口?這是時代拋擲在李雙澤一代左翼青年面前的問題。而同西班牙、菲律賓的相遇催生出李雙澤一種尚在萌芽狀態(tài)的第三世界意識,他開始擺脫將西方(特別是美國)作為普世性范式,即繞過西方,同更有參照意義的鏡像建立對話,探尋第三世界不同民族的經(jīng)驗與方法。35
海外游歷為李雙澤自我主體的確立提供了多元的參照系,也為他的新歌創(chuàng)作做了精神上的積蓄與準(zhǔn)備。在這一背景下發(fā)起的“唱自己的歌”運動,實際是從解殖民的立場出發(fā),以覺醒的民族意識與社會意識,努力突破既有文藝形式及生產(chǎn)方式的一次嘗試。所謂“自己的”歌,對李雙澤而言,首要的涵義是用中華民族的語言唱的歌。李雙澤曾談道:“先唱真正自己的民族之歌來喚醒民眾,然后,再來一個民族大合唱!!”36李雙澤將覺醒后的民族意識傾注到創(chuàng)作中,召喚每一個歌唱者“自己的”聲音,匯成整個民族的合唱。
其次,所謂“自己的”也意味著是現(xiàn)代的,與現(xiàn)實密切相關(guān)。《補破網(wǎng)》《思想起》等傳統(tǒng)民歌本身已經(jīng)蘊含著與生命美學(xué)意識相關(guān)的民族精神,但新的時代要求新的藝術(shù)形式。楊弦、余光中的中國現(xiàn)代民歌運動所標(biāo)榜的“現(xiàn)代”,主要是指有別于傳統(tǒng)民歌并面向年輕人,但其歌詞的意象、情感模式仍指向過去。李雙澤的歌則集中于當(dāng)下和未來,歌詞中流露出強烈的社會意識,如歌曲《我知道》《我們的早晨》等。也因此,“唱自己的歌”運動盡可能地走入人群,到溜冰場、草地、工廠、社區(qū)演唱,讓歌唱不再只是自我的抒發(fā),而是成為一種面向社會、介入社會的力量,用歌聲去培育與現(xiàn)實緊密相關(guān)的文化,去影響與滋養(yǎng)現(xiàn)實中的人。37
李雙澤的歌常使用第一人稱,“我”與“我們”有時是如李雙澤一樣的知識青年,如《少年中國》《老鼓手》《送別歌》;有時是泛指,即與前輩祖先(“他們”)相對的當(dāng)代人,如《愚公移山》《美麗島》;有時則是特指,即學(xué)生、工人等特定群體,如《我們的早晨》。這里的第一人稱并不指向個人心緒,而是以群體的代言人出現(xiàn),嘗試連接知識青年和構(gòu)成人群大多數(shù)的中下層勞動者。
李雙澤“自己的”歌,說到底是與自己及周遭環(huán)境、時代有關(guān)的歌,其中包含了他理解的“中國”與“現(xiàn)代”的結(jié)合,以及他的民族意識與社會意識,同時也隱含著左翼關(guān)懷。游學(xué)歸來的李雙澤曾在朋友中秘密傳唱《我的祖國》,并說這是我們應(yīng)該唱的歌。38《我的祖國》從“一條大河波浪寬”唱起,歌唱自然風(fēng)光,也歌唱勞動人民開天辟地的豪情。在《美麗島》《送別歌》中,李雙澤用類似的感覺結(jié)構(gòu)連接臺灣的自然風(fēng)土和歷史經(jīng)驗,以積極樂觀的曲調(diào),歌唱土地、山河、歷史、大地上的人民,重建關(guān)于鄉(xiāng)土、家園的認(rèn)識,再配以富有感染力的節(jié)奏,喚起聽眾的民族自豪感,在個人情感中激發(fā)民族認(rèn)同,推動主體的新生與重構(gòu),與現(xiàn)代主義如影隨形的虛無、失落,在這樣的歌聲中被一掃而空。
李雙澤稱自己創(chuàng)作改編的歌曲為“新歌”,新歌之“新”,不僅因為是新近創(chuàng)作出來的,也因為寄寓了塑造新的青年群體、新的民族意識乃至新的文化形態(tài)的期望。新歌所具有的現(xiàn)實感與積極昂揚的樂觀精神,讓它們既是現(xiàn)實主義的,又閃耀著理想的光芒。新歌的質(zhì)地難免稚嫩、粗糲,它們畢竟是啼聲初試之作,也因為李雙澤戛然而止的生命中斷了充分發(fā)展的可能。但在其稚拙的表現(xiàn)形式與貼近鄉(xiāng)土、大眾的內(nèi)容以及或許過分樂觀的理想主義之間,實際上存在某種一致性。不僅如此,新歌也流露出一種面向聽眾的敞開的聲音,反映出一名“用力敲鐘”的藝術(shù)工作者走進(jìn)大眾的決心與努力。
03
《夏潮》上的新詩與“唱自己的歌”運動
“唱自己的歌”運動以“淡江事件”為起點,又以李雙澤的新歌為重要果實,但其展開實際上匯集了臺灣當(dāng)時文化知識界的諸多力量,尤其與《夏潮》雜志的推動密不可分。
在20世紀(jì)70年代后半期關(guān)懷現(xiàn)實、回歸鄉(xiāng)土文化思潮推動的文化實踐場域中,《夏潮》雜志處在一個重要位置,其影響力通過與雜志關(guān)系密切的王津平、蔣勛、尉天驄、李利國等人,廣泛涉及《淡江周刊》《雄獅美術(shù)》《中國論壇》《仙人掌》《中華雜志》等,并聯(lián)合《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等主流報刊,撐起寶貴的、富有開拓性的文化空間。《夏潮》著意推動左翼視角下的社會文化議題的討論,努力在歷史與現(xiàn)實的雙重維度實踐民族主義、反西化、反現(xiàn)代主義的立場。在歷史維度上,注重發(fā)掘日據(jù)時期的文學(xué)和歷史,整理中國近代史尤其是國民革命的歷史,嘗試從歷史文化經(jīng)驗中探索前進(jìn)方向39。在社會現(xiàn)實層面上,則突破冷戰(zhàn)的思維框架,聚焦臺灣社會,尤其關(guān)注弱勢群體如勞工階層的問題、階級及環(huán)保議題,抨擊崇洋媚外現(xiàn)象,關(guān)懷青年一代成長;同時放眼世界,關(guān)注第三世界與弱小民族的問題,圍繞越戰(zhàn)、菲律賓、拉丁美洲等議題展開討論。
就詩歌而言,《夏潮》始終回蕩著現(xiàn)代詩論戰(zhàn)的余音,總體上延續(xù)了現(xiàn)代詩論戰(zhàn)中唐文標(biāo)面向大眾、強調(diào)社會意識的現(xiàn)實主義詩歌路線。唐文標(biāo)與蘇慶黎、陳映真等人交往甚密,他不僅是《夏潮》的主要供稿人之一,還為雜志提供早期的創(chuàng)作經(jīng)費和場地支持。40《夏潮》系統(tǒng)地接續(xù)了唐文標(biāo)在現(xiàn)代詩論戰(zhàn)中的主要觀點,包括詩與現(xiàn)實的關(guān)系、詩與時代的關(guān)系、文學(xué)為什么人等問題。41
唐文標(biāo)之外,陳映真對現(xiàn)代詩的弊端也早有覺察。早在1967年,陳映真就撰寫《期待一個豐收的季節(jié)》一文,發(fā)出批判現(xiàn)代詩的先聲。隨后他因入獄錯過了現(xiàn)代詩論戰(zhàn),出獄后他有針對性地撰寫了《走出泥沼,展開新頁!》(1977)、《現(xiàn)實主義藝術(shù)的新希望》(1978)、《試論蔣勛的詩》(1980)、《試論施善繼的詩》(1980)、《試論吳晟的詩》(1983)等文,持續(xù)推進(jìn)有關(guān)現(xiàn)代詩的討論。與唐文標(biāo)相比,陳映真更側(cè)重新詩建設(shè)。1978年7月,他參加了《夏潮》雜志“期待一個豐收的季節(jié)”新詩討論會,1979年夏又在《民眾日報》副刊主持“新詩的再生”座談,致力于推動新詩內(nèi)容和形式上的雙重蛻變。42
在唐文標(biāo)、陳映真的影響下,《夏潮》的詩歌批評總體上強調(diào)詩應(yīng)反映時代,反映大眾的精神、情感和身心狀態(tài),重視詩與生活的深度關(guān)聯(lián)。43《夏潮》“詩選”欄目選登的新詩以現(xiàn)實主義為主,側(cè)重彰顯民族意識與社會意識,44為帶有左翼關(guān)懷的新詩提供了理論支持與難得的發(fā)表平臺,造就了詹澈、施善繼、蔣勛、葉香等一批詩人45。“農(nóng)民詩人”詹澈的早期代表性敘事長詩《她不是啞巴》便發(fā)表于《夏潮》。詹澈通過與《夏潮》關(guān)系密切的林華洲、施善繼讀到艾青等大陸詩人的新詩,受艾青影響頗深,他本人后來也曾任《夏潮》編輯。46《她不是啞巴》刻畫了雅美人白云的悲慘命運,反映臺灣少數(shù)民族在現(xiàn)代社會的境遇。全詩感情充沛,口語化的表達(dá)融合直抒胸臆的吶喊,體現(xiàn)出對邊緣群體的關(guān)切。
盡管如此,批評理論與創(chuàng)作實踐之間仍存在落差,這股面向鄉(xiāng)土與大眾的詩歌潮流并未成為詩歌創(chuàng)作的主流,《夏潮》編輯部在1978年表示,現(xiàn)實主義新詩創(chuàng)作“在量和質(zhì)上都還未臻理想”47。此外,詩作為特定文類,在連接大眾、連接時代方面并未表現(xiàn)出特別的優(yōu)勢。于是,《夏潮》雜志對新詩的“改造”,轉(zhuǎn)而借助詩與歌的結(jié)合,在雜志推動的“唱自己的歌”運動中推進(jìn)。現(xiàn)代詩論戰(zhàn)中反對現(xiàn)代詩的聲音逐漸與“唱自己的歌”運動匯流,構(gòu)成70年代鄉(xiāng)土文化潮流中一股不容忽視的力量。
1977年3月,淡江學(xué)院舉辦“中國民俗歌謠之夜”露天演唱會,演出曲目以傳統(tǒng)民歌為主,陳達(dá)即興說唱的恒春民謠為其壓軸。這次演唱會承接前不久的“淡江事件”,嘗試唱響中國民謠“自己的”聲音。《夏潮》相關(guān)人士參與了這場演唱會,并在該雜志發(fā)表明立國的文章,檢討演唱會的得失,呼喚音樂“走出個人,走入人群”48;陳映真撰文號召“我們年輕的文學(xué)界應(yīng)該開始創(chuàng)作歌辭,我們年輕的音樂界應(yīng)該為新辭譜曲”49。演唱會舉辦時,李雙澤人在菲律賓,但陳映真的倡議或許成為他返臺后創(chuàng)作新歌的動力之一。
作為一名青年撰稿人,李雙澤先后在《夏潮》發(fā)表十余篇文章50,其他文章見于同《夏潮》關(guān)系密切的《淡江周刊》《雄獅美術(shù)》《仙人掌》等雜志。他所創(chuàng)作的十余首新歌大多改編自新詩,其中三首原詩發(fā)表于《夏潮》雜志51。此外,李雙澤的師友,參與和推動“唱自己的歌”運動的王津平和梁景峰均為《夏潮》雜志撰稿人,王津平更是《夏潮》的核心成員。李雙澤去世后,《夏潮》雜志刊發(fā)大量紀(jì)念詩文,并通過發(fā)表評論文章、召開座談會,協(xié)助組織“李雙澤紀(jì)念畫展”“大家一起唱”李雙澤紀(jì)念演唱會等活動,52繼續(xù)推動“唱自己的歌”運動。1977年10月6日,淡江校友會舉辦“紀(jì)念李雙澤民歌演唱會”,鄭盈湧為此撰寫《我們的歌·我們的根》一文,在《夏潮》第4卷第4期發(fā)表。
除了舉辦與李雙澤相關(guān)的活動,《夏潮》雜志也嘗試調(diào)用多方力量,為“唱自己的歌”運動開辟發(fā)展路徑。20世紀(jì)60年代末,音樂工作者史惟亮、許常惠曾帶隊從事臺灣民歌采集工作,以重建民族音樂的信心。53《夏潮》雜志對此頗為看重,并期待更多音樂工作者參與新民歌創(chuàng)作,以獲得更多理論工具和創(chuàng)作資源。史惟亮去世后,《夏潮》將他作為雜志封面人物,以志紀(jì)念,同期還刊登音樂工作者游昌發(fā)《紀(jì)念史惟亮先生》54一文。1977年11月,《夏潮》刊登游昌發(fā)同《夏潮》社長鄭漢民的對談“讓我們唱自己的歌”。但交流有時也表現(xiàn)為沖突與碰撞,次年6月,《夏潮》組織第一次民歌座談會,邀請學(xué)院與非學(xué)院的民歌工作者對話,討論民歌與中國音樂的出路。會上,學(xué)院與非學(xué)院兩派壁壘森嚴(yán),陳映真表示,若音樂家不愿為大眾創(chuàng)作民歌,也沒有關(guān)系,“讓我們自己來”55。不過,《夏潮》依然以彈性的態(tài)度去兼容不同的聲音,第5卷第5期“夏潮廣場”上刊登音樂工作者李哲洋的爭鳴文章《布農(nóng)族合唱曲的是非》,并邀請他參加雜志組織的第二次民歌座談會。
第一次民歌座談會記錄所附《夏潮》編輯按語透露:“寫詩的朋友決定今后好好地寫歌詞。他們將盡量反應(yīng)著現(xiàn)今大多數(shù)人共同的生活體驗和希望。”56同期,《夏潮》刊登了“時代歌謠創(chuàng)作獎公開征求歌詞”公告,發(fā)動大眾創(chuàng)作“時代歌謠”。時代歌謠征集活動獲得熱烈反響,同年9月,時代歌謠評審結(jié)果由陳映真、施善繼、王津平、蘇慶黎等評委揭曉,14篇作品從120篇投稿中脫穎而出,獲獎?wù)叨酁槲膲厝耍灿姓渤骸⒄餐窬仍凇断某薄飞习l(fā)表過詩作的年輕詩人,以及陳揚山等音樂愛好者57。獲獎歌詞分成情歌、兒歌、工作歌、愛國歌四類,作為“夏潮時代歌謠創(chuàng)作獎”入選作品,登在《夏潮》“詩選”欄目58。
《夏潮》第 4 卷第 6 期開始刊載“時代歌謠創(chuàng)作獎”公告,發(fā)動大眾創(chuàng)作“時代歌謠”
1978年11月,《夏潮》組織第二次民歌座談會,小說家黃春明、樂評人李哲洋以及《夏潮》的鄭漢民、蘇慶黎等人圍繞時代歌謠獎歌詞與民歌的大眾化展開討論。黃春明對獲獎歌詞的批評尤為嚴(yán)厲,認(rèn)為“應(yīng)該全部丟棄”,身為評委的蘇慶黎也說“這些歌是不會流行的”。59不過,《夏潮》雜志選登的讀者來信顯示,時代歌謠征集活動及其成果受到部分讀者的肯定。60
作為回應(yīng),《夏潮》雜志隨即表示歡迎“以閩南語、客家語、山地語等歌詞創(chuàng)作的歌曲”,并稱第二階段“公開征求歌譜”已獲致熱烈反響,足見“‘唱自己的歌’的風(fēng)氣已經(jīng)開啟”61。1979年初《夏潮》繼續(xù)征集歌謠,并宣布于3月舉辦“時代歌謠演唱會”。然而,3月的雜志再未付印,《夏潮》就此停刊。李雙澤逝世、《夏潮》停刊,楊祖珺、胡德夫演唱被禁,接連的打擊令“唱自己的歌”運動難以為繼。62
詩與歌作為兩種不同的藝術(shù)形式,既有同源性,又在發(fā)展中形成了各自獨特的屬性。現(xiàn)代派詩人紀(jì)弦曾堅持“詩是詩,歌是歌”,主張詩是少數(shù)人的文學(xué),歌是大眾化的,二者應(yīng)當(dāng)分開。63現(xiàn)代詩的反對派,比如陳映真,則認(rèn)為重新恢復(fù)詩歌的音樂性是走出現(xiàn)代主義之后新詩建設(shè)的一個重要方向。新詩與歌詞在形式上的近似以及新詩音樂性的回歸,不但為詩與歌的結(jié)合與轉(zhuǎn)化提供了可能,也為新詩“附體”民歌、走向大眾創(chuàng)造了條件。
“唱自己的歌”運動的一個局限是主要曲目始終集中在李雙澤的新歌系列,缺乏有效的再生產(chǎn)與傳播方式。“時代歌謠”征集活動作為這次運動中的重要一環(huán),原本旨在促進(jìn)詩/歌創(chuàng)作同大眾結(jié)合,使大眾成為詩/歌創(chuàng)作主體,從而催生出更多為大眾所喜聞樂見的詩/歌。但遺憾的是,這一活動未能充分推行,其開展過程也從側(cè)面反映出左翼知識分子如何連接大眾,在20世紀(jì)70年代的臺灣仍是一個難題。
綜上,20世紀(jì)70年代臺灣的現(xiàn)代詩論戰(zhàn)、“唱自己的歌”運動以及鄉(xiāng)土文學(xué)運動三者具有一定同構(gòu)性,它們既有承繼,又相互補充,呈現(xiàn)出西化與鄉(xiāng)土、現(xiàn)代與傳統(tǒng)之間的張力。現(xiàn)代詩反對派所否定的“橫的移植”與“唱自己的歌”運動所提倡的“不唱西洋歌”構(gòu)成對位關(guān)系,“自己的歌”則與現(xiàn)代詩反對派呼喚的“新詩”及后來的“鄉(xiāng)土文學(xué)”對位,目的皆在確立植根于自身文化土壤且關(guān)懷現(xiàn)實的文藝形式。在這一過程中,《夏潮》雜志起到的作用不容忽視,它不但與70年代臺灣重要的社會文化事件緊密相關(guān)—延續(xù)現(xiàn)代詩論戰(zhàn)反對派的聲音、推動“唱自己的歌”運動、成為鄉(xiāng)土文學(xué)論戰(zhàn)的主戰(zhàn)場,而且將不同思想脈絡(luò)下的知識人以及面向社會現(xiàn)實的思考者串聯(lián)起來,在一連串的探索中,共同開拓70年代后期臺灣的知識文化空間。
“唱自己的歌”運動反映凝聚在《夏潮》周圍的泛左翼知識分子在回歸鄉(xiāng)土、關(guān)懷現(xiàn)實的思潮背景下,嘗試突破國民黨文藝體制以及英美歌曲流行背后的新殖民主義。借助這次運動,《夏潮》知識分子的思考在社會空間初步落地,從詩到歌,從校園到社會,將新詩的大眾化向前推進(jìn)了一步,也將“唱自己的歌”運動推向民間,力求重建詩與歌、音樂與鄉(xiāng)土及社會的關(guān)系,探索知識分子及青年連接大眾、介入社會的可能。
李雙澤的“覺醒”之路銘刻著20世紀(jì)70年代特有的印記,他旺盛的生命熱情,對繪畫、音樂、文學(xué)、攝影、建筑等藝術(shù)廣博的愛好,以及處在萌芽中的第三世界意識,不但塑造了他富有感染力的個性,也為“唱自己的歌”運動的發(fā)生儲備了充沛能量。在這次運動中,李雙澤的《美麗島》與《少年中國》最負(fù)盛名,蔣勛和陳秀喜的詩也由此被更多的人記憶和“傳唱”。盡管此后臺灣通俗音樂類型逐漸被商業(yè)音樂收編,但“唱自己的歌”運動所召喚的民族意識、所培植的音樂土壤、所帶動的創(chuàng)作風(fēng)氣,仍為此后臺灣音樂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更大的機遇,“唱自己的歌”運動的精神也在一些歌手、樂隊那里得到了延續(xù),如胡德夫、楊祖珺、交工樂隊等。《夏潮》停刊后,臺灣左翼知識分子的探索則借此后的《春風(fēng)》《人間》《夏潮論壇》等雜志繼續(xù)展開。
重新檢視李雙澤宛若流星的生命,重新閱讀戛然中斷的《夏潮》雜志,在今天依然有現(xiàn)實意義。二者的實踐蘊含著未及展開而特別值得開掘的問題,包括新時代青年主體的塑造,更開放、更健康的民族意識的養(yǎng)成,以及知識分子參與社會的方式,等等。它們?nèi)缤涣A0袩o限的種子,既保存著20世紀(jì)70年代的印記,也為我們今天重構(gòu)人文思想提供了重要資源。
「 支持烏有之鄉(xiāng)!」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wǎng)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wǎng)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xiāng)網(wǎng)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