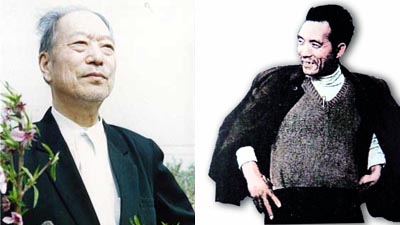今年3月17日,習近平來到開封,直奔焦裕祿紀念館,并發表感言說:
“焦裕祿同志的形象一直在我心中”、“焦裕祿精神是永恒的。焦裕祿精神和井岡山精神、延安精神一樣,體現了共產黨人精神和黨的宗旨,要大力弘揚。”、“學習焦裕祿時我上初中,當時政治課老師讀報,讀著讀著便哽咽了,聽著聽著我們也流淚了。焦裕祿精神影響了一代人。”、“我希望通過學習焦裕祿精神,為推進黨和人民事業發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強大正能量。”
1990年深夜習近平讀完《人民呼喚焦裕祿》一文,揮筆寫下《念奴嬌·追思焦裕祿》一首,其中寫道:“思君夜夜/肝膽長如洗/路漫漫其修遠矣/兩袖清風來去/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今年習近平試圖通過“呼喚焦裕祿”,為全黨樹立一個學習的榜樣,來拉開今年黨員走群眾路線運動的大幕。
但是當下中國,斗爭十分復雜。當習近平“呼喚焦裕祿”之際,《南方周末》于2014年5月30日刊出一篇文章,題為《展現真實的焦裕祿》,再度通過造謠的方式,極力貶低焦裕祿,進而將焦裕祿對蘭考的貢獻一并抹殺,對新中國前三十年予以全面否定。
《南方周末》 “史貴求真”還是“史貴造謠”?
該文出自一個號稱“近代史研究員”之手,但行文卻非常輕薄草率。全文要展現“真實的焦裕祿”,所引用的資料悉數出自一位名叫“任彥芳”的人。《南方周末》稱:任彥芳“是一位焦裕祿研究專家。”“任彥芳參與劇本創作組,到蘭考調查、搜集焦裕祿的事跡資料,采訪了與焦裕祿有過接觸的干部群眾,掌握了豐富的資料。”
任彥芳是什么人呢?是一個對蘭考歷史根本不懂的人。此人寫過一本題為《焦裕祿身后》的書,在這本書中,任彥芳說焦裕祿治理后的沙丘上種的是“泡桐樹”,實際上焦裕祿種的是洋槐樹;任彥芳說周化民在1965年跑遍了十二個公社,實際上蘭考到1975年只有九社一鎮;任彥芳稱樊哲民為縣人大的樊哲民,實際上樊時任縣委農工部副部長;任彥芳稱劉俊生是宣傳部干部,實際上劉俊生是縣委辦公室干事;焦裕祿去世后,由程世平主持縣委工作,任彥芳卻把蘭考最高機關的重大人事安排寫成“焦裕祿去世后,蘭考由縣委副書記、縣長張欽禮主持工作”。
《南周》該文先將任彥芳塑造成一個與焦裕祿很熟的形象,稱“他的母親張學玉與焦裕祿是鄰居”,任彥芳自己以前的文章中也表示過,他和焦裕祿談過多次話,于是《南周》該文接著就斷定任彥芳的資料“十分珍貴”。從上述的一些常識錯誤辨析中,我們已經發現,任彥芳完全不懂蘭考歷史。
那么任彥芳跟焦裕祿熟嗎?
焦裕祿1962年冬來蘭考時,其家與其他縣委領導人,包括任彥芳的繼父孟照芝都住在縣委后院的排房里,是有一段鄰居關系。1963年春,焦裕祿就搬走了。任彥芳1962年10月探親,焦還未到蘭考,1963年冬,任彥芳第二次到蘭考探親時,他家與焦裕祿早已不是鄰居了,在這僅有的幾天里,他見到焦裕祿的可能性有多大?焦裕祿身為肩負重任的縣委書記,蘭考災情嚴重,工作壓頭,不下鄉就開會,我們天天與他在一起工作、下鄉,從沒見過他身邊帶著個并不相識的外地青年,這任彥芳能與焦裕祿有多次交談,從何說起?那時工作紀律很嚴,干部請假時間不會太長,任彥芳即使不招即到,沾著不丟,又能有幾天與焦見面時間?哪里會有“逐漸熟悉起來的”機會?
任彥芳與焦裕祿的情結,只因為1963年冬到蘭考探親的幾天中,具有一點與焦裕祿見面的可能,見不見還在兩可,卻能變得比山高,比海深,以至使他發展到“與蘭考息息相關”“命運相連”的程度,并不是“大作家”“大詩人”的多愁善感使然,應該是他所稱謂的“蘭考上空爆炸的精神原子彈”,對他的強烈吸引力。[1]
就全文引述這樣一個人的資料,《南方周末》還好意思在小標題上寫上“史貴求真”四個醒目大字。對《南方周末》此文而言,恐怕是“史貴造謠”更為貼切。
請問《南周》 為何要搜肚刮腸證明焦裕祿被夸張、拔高?
《南方周末》是怎樣“求真”的呢?它使用一個對蘭考歷史半知半解、跟焦裕祿見面與否都是未知數的人的“一手資料”,來推翻其他扎實考證的史實。
該文中,斷定宣傳焦裕祿過程中存在“拔高、夸張和隱瞞”的情形,并舉了一例,即以往的宣傳認為焦裕祿逝世前病床枕邊放著《毛澤東選集》和劉少奇《論共產黨員修養》兩書,“實際上并無此事,焦裕祿的《毛選》是放在家里的。”
對此事的否定來自任彥芳采訪焦裕祿女兒焦守鳳的孤證,拿這個孤證來做結論是很不嚴肅的事情,更說不上是“史貴求真”。對這個事情的判斷,作者為何不參考焦裕祿夫人、干部朋友、護士等人的回憶呢?而且我們發現,在其他時期其他人對焦裕祿的女兒焦守鳳、焦守云做的采訪中,所回憶的內容也與任彥芳不符。
焦裕祿夫人回憶:焦裕祿夫人徐俊雅在回憶文章《永遠的懷念》中說:“老焦在身體極度虛弱,生命的最后一息,還要堅持每天學習毛主席著作,……”(化漢三《難以忘卻的懷念》1992年12月)
焦裕祿的干部朋友回憶:“省委、地委的負責同志,曾多次去醫院探望他,有時還見他拿著毛主席著作,在用心地學習。”(《焦裕祿在蘭考》中共蘭考縣委編寫組 1964年4月)
焦裕祿的護士醫生回憶:2014年5月14日是焦裕祿逝世50周年的紀念日,這天《河南日報》發表了記者采訪在樊鏡珍(焦裕祿生命最后時刻照顧焦裕祿的護士)等人的新聞稿,并清晰記載:“焦裕祿去世后,樊鏡珍整理物品時,在他的枕下發現兩本書:一本是《毛澤東選集》,一本是《論共產黨員的修養》。”
時任河南醫學院內科教研組副主任的段芳齡回憶說:“……他似乎已經知道患的是不治之癥,但他仍然堅持學習毛主席著作。他枕頭下的兩本書 《毛澤東選集和《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是他必讀書籍。”(段芳齡《他頑強地和疾病作斗爭》)
焦裕祿的女兒回憶:《焦裕祿在蘭考》一書收錄了焦守鳳《回憶爸爸》一文,該文回憶,焦裕祿曾對焦守鳳說:“小梅,你從我手里繼承的只有黨的事業,別的什么也沒有……我留給你的,只有一部《毛澤東選集》。不過我手邊的這一本,現在還不能給你,當我活著時,我還要學習毛主席著作……《毛澤東選集》就作為我留給你的紀念品。你要好好學習毛主席著作,那里邊,毛主席會告訴你怎樣工作,怎樣做人,怎樣生活……
1990年,焦守鳳接受記者王鋼采訪時說,父親說:“爸爸工作幾十年,也沒啥好留給你的,這套《毛澤東選集》、這本《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給你,毛主席會教你怎樣工作,怎樣做人。……”(王鋼:《爸爸的凝視---訪焦裕祿的女兒焦守風焦守云》 河南日報1990年5月16日)
請注意,這里焦守鳳轉述焦裕祿說的是“這套《毛澤東選集》、這本《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給你”,“這套”、“這本”這兩個詞恰好證明了《毛澤東選集》和《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這兩本書是存在于焦裕祿身邊的。
二十多年后的2012年,一篇采訪焦裕祿二女兒焦守云的通訊報道又提到了這件事:“在彌留之際,焦裕祿把大女兒焦守鳳叫到了身邊,把一本《毛澤東選集》和一本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交給她說:“你要好好學習,書里邊會教你怎么工作,怎么生活。”(《天上一顆星地上一個丁》作者:謝中 來源:《刊授黨校》2012.7)[2]
從焦裕祿夫人、干部朋友、護士以及兩個女兒的回憶中,對焦裕祿臨終前學習兩本書這件事情,是可以相互印證的。
南周偏偏采信來歷不明的任彥芳的孤證,而且據此孤證竟然能夠斷定對焦裕祿的宣傳中存在“拔高、夸張和隱瞞”,極不嚴肅,實質上是以“求真”的態度虛無歷史,貶低共產黨員的形象。另一方面,《南方周末》如此搜腸刮肚貶低抹黑焦裕祿,卻始終找不到任何有力的證據,不得不采信任彥芳這個孤證,這是搞歷史虛無主義的硬傷,也是南方系的悲哀。
請問《南周》 焦裕祿如何成了悲劇?
《南方周末》文章認為,焦裕祿到一到蘭考就抓階級斗爭、兩條路線的斗爭,在生產救災、除三害和種麥中,也是集中力量抓兩條道路的斗爭。并摘錄任彥芳的一句話來進行佐證:“他拼上老命,去鞏固集體經濟。他如果不這樣努力去做,而是有所抵制,有所懷疑,那反而不是焦裕祿了。”
作者的用意可謂十分惡毒,將全身心投入治理蘭考三害、生產自救的焦裕祿描述成一個堅決執行上級左傾路線、主抓階級斗爭的官僚形象。并故作同情地加了一個小結稱:“焦裕祿不可能超越歷史”。這個小結更具有強烈的政治針對性,意指當時的所有干部都是盲目執行上級左傾路線、寧左勿右、不顧群眾的經濟工作、主抓階級斗爭。
這是嚴重的栽贓。請看下面的事實:
焦裕祿在蘭考狠抓“除三害”,親自主持制定《關于治沙、治堿、治水三五年的初步設想》(草案),決心改變蘭考貧窮落后面貌。并說過三害不除,“死不瞑目”。這里并沒有提階級斗爭。
焦裕祿親自樹立的蘭考四面紅旗,都是在生產自救、除三害方面的典型,沒有一個“階級斗爭”方面的典型。
焦裕祿沒有寫完的那篇文章《蘭考人民多奇志,敢叫日月換新天》里,也根本沒有提階級斗爭。
上述事實明白無誤地說明,“焦裕祿到蘭考花的精力最大、用的時間最長、費的心血最多、他感到壓力最重的事情”是除去三害,改變蘭考貧窮落后面貌,讓蘭考人民過上好生活,而不是什么階級斗爭。
在“焦裕祿主抓階級斗爭”謠言的基礎上,文章進行進一步的演繹,因為抓階級斗爭所以沒有治理好三害,沒有給人民帶來幸福,到文章最后,作者認定焦裕祿是個悲劇:“雖然主觀上把全身心獻給了蘭考人民,但是夢想并沒有實現。”因為“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政治體制和僵硬的集體經濟體制下,無法改變農民貧困的命運。”并以蘭考縣委書記刁文的話來為文章做點睛之筆“焦裕祿一心為人民,把他累死了,可蘭考并未翻身。我們沒有老焦那樣的精神、能力,(卻)讓蘭考扔了要飯棍。關鍵是路線、政策,是包產到戶聯產承包責任制。這是合乎生產力發展的體制。可見,沒有好的合民心民意的體制,再有焦裕祿拼命也不行啊!”
焦裕祿和焦裕祿繼承者的成績被南周吃了?
蘭考縣一九六五年糧食已經初步自給了。一九六五年蘭考縣連續旱了六十八天,從一九六四年冬天到一九六五年春天,刮了七十二一九六五年次大風,卻沒有發生風沙打死莊稼的災害,十九萬畝沙區的千百條林帶開始把風沙鎖住了。這一年秋天,連續下了三百八十四毫米暴雨,全縣也沒有一個大隊受災。
應該承認,焦裕祿在治理風沙、干旱方面取得了許多成績。但是由于焦裕祿在蘭考時間太短,蘭考的惡劣環境是千百年時間造就的,短期內無法徹底根治。對蘭考環境特別是鹽堿地的根本改造是焦裕祿逝世后,在張欽禮主政蘭考期間,用黃河水灌淤的方法完成的。
從1973年到1977年,是蘭考人聚精會神搞建設的四年。僅1973年,全縣共挖大小排水河道125條,配套支渠154條,拆除阻水工程164處,共完成1171萬土方,基本達到排水暢通。全縣治沙造林共計19萬畝,占沙荒面積的80%治理鹽堿地22.7萬畝,占鹽堿地的86.3%。至此,蘭考的"風沙、內澇、鹽堿"三大災害再也不能為非作歹了。1973年秋,省委書記劉建勛、中商部部長姚依林等領導人花了5天時間考察了蘭考的路、河、橋、閘、林、田,看到昔日逃荒要飯的重災區的確成了魚米之鄉、錦繡江南。
張欽禮帶領的干部們,為了治沙治水,付出了多少心血、汗水和病痛。這批跟著焦裕祿、張欽禮一再受批斗的干部都是與普通農民一起勞動的。群眾身上有多少泥,他們身上就有多少泥。久而久之,這些干部的腿上就成了"一無二有":腿上無汗毛,膝蓋骨以下有數不清的血口子。腿上的汗毛是被黃河泥粘掉的。[3]
延續焦裕祿路線的張欽禮同志帶領蘭考人民將蘭考徹底改造成功,這就是焦裕祿的勝利,何來悲劇之說?而《南周》竟來了一句“焦裕祿一心為人民,把他累死了,可蘭考并未翻身。我們沒有老焦那樣的精神、能力,(卻)讓蘭考扔了要飯棍。”敢情張欽禮執行的不是焦裕祿的精神和路線,而提前搞包產到戶了?或者再南周們眼中,根本沒有為民付出幾十年心血的張欽禮這個人。包產到戶是在張欽禮已經治理了蘭考風沙、內澇、鹽堿地之后的事情,任彥芳和刁文們怎么能夠貪天之功,將焦裕祿張欽禮的畢生心血據為己有,孤立地記到包產到戶的功勞簿上,從而把焦裕祿認定成一個悲劇,進而將前三十年的成績一并抹殺?
習總講不能否定前三十年,《南周》依舊通過造謠的方式,而且是定點造謠的方式,試圖打倒習總心中的偶像,攪亂今年的黨員群眾路線、共產主義信仰學習活動,這是赤裸裸地向共和國示威。
附:南方周末:展現真實的焦裕祿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1041
任彥芳研究焦裕祿的機緣
任彥芳是一位多產的作家、詩人,也是一位焦裕祿研究專家。他之所以能以焦裕祿作為自己的創作和研究對象,得益于兩個機緣:一是他的繼父孟昭芝與焦裕祿同在蘭考縣委工作(孟任縣委副書記),他的母親張學玉與焦裕祿是鄰居,他們對焦裕祿熟悉了解,任彥芳也因此有機會見過焦裕祿,并和焦交談過。
另一機緣是,任彥芳的工作單位長春電影制片廠,當年曾準備拍攝宣傳焦裕祿的影片,其后文化部將拍攝任務轉交給北京電影制片廠,任彥芳參與劇本創作組,到蘭考調查、搜集焦裕祿的事跡資料,采訪了與焦裕祿有過接觸的干部群眾,掌握了豐富的資料。
焦裕祿傳記資料十分珍貴
《我眼中的焦裕祿》大體包括以下幾類內容:一是檔案文件,書中錄出中共蘭考縣委文件和焦裕祿的手稿;一是回憶錄,包括任彥芳本人與焦裕祿見面交談的回憶,任母、任的繼父對焦裕祿事跡的敘述;一是采訪記錄,這是他人的回憶,口述記載;還有焦裕祿在蘭考475天日志,這是經過調查后編寫出的研究資料。
除了檔案手跡外,其他回憶錄和采訪記錄,基本上都保存在任彥芳的日記和采訪筆記中,事過近半個世紀的時間,也具有見證焦裕祿事跡和精神的原始資料性質,都十分珍貴。
史貴求真
以往宣傳焦裕祿,也發表過不少文章和作品,但像過去宣傳各種典型人物、典型事跡一樣,難免拔高、夸張和隱瞞之處,在焦裕祿宣傳中也存在失真的情況。比如,描寫焦裕祿逝世時,說他病床枕邊放著《毛澤東選集》和劉少奇《論共產黨員修養》二書,這是“文革”前宣傳毛澤東和劉少奇兩個主席的政治需要。實際上并無其事,焦裕祿的《毛選》是放在家里的。現在有的文藝作品又按照今天的需要塑造(改造)焦裕祿,把竭力維護集體經濟的焦裕祿,寫成支持“借地”,讓生產隊以小片荒的名義,將“借地”分給社員,這背離了當時真實情況。
《我眼中的焦裕祿》一書,特別強調,敘述、宣傳焦裕祿必須求真。史貴求真,任書以檔案文件和大量采訪資料為依據,力求向讀者展現焦裕祿所處時代的真實性、當年蘭考的真實狀況和焦裕祿本人的真實面貌。
真實的蘭考
焦裕祿在蘭考工作了一年多。任彥芳在書中介紹了焦裕祿來蘭考縣時該縣的嚴重災荒困難背景。蘭考是黃河故道流經的地方,這里水患、風沙、鹽堿給全縣36萬人帶來嚴重災難。由于“大躍進”的折騰,造成的災難越發嚴重了。蘭考縣1949年前糧食年產量達到1.0902億斤,1956年為2.0151億斤,而1962年下降到0.6825億斤(一說6000萬斤)。36萬人中,一般干部都處在半饑半飽狀態。20萬人因災缺糧,人民忍饑挨餓,吃糠咽菜,浮腫死亡。任彥芳繼父孟昭芝(蘭考縣委副書記)說:1960年,蘭考“各村都有餓死的人,人人都有浮腫,婦女沒有月經。”
因饑餓,許多人乞討,外出逃荒。書中說,李雪健主演的電影《焦裕祿》中蘭考車站一群孩子向焦裕祿乞討的情景是真實的。“1962年麥子絕收,被風打死,秋季又是大水災,蘭考人跑了三分之一。”1962年12月4日,焦裕祿來到蘭考縣時,三年困難的境況尚存,至1963年春,外出謀生者達3.8萬人。
由于“大躍進”,“大煉鋼鐵”,砍伐森林,蘭考縣攔風沙原來栽的泡桐被砍,風沙、鹽堿、水患“三害”肆虐,蘭考農村處于貧窮困苦之中。
真實的時代
焦裕祿到蘭考的時間也很重要。1962年底,正是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之后。
1962年初,中國共產黨為總結“大躍進”,人民公社化的教訓,召開了從中央到縣各級領導骨干共七千人的會議。劉少奇對造成三年困難的原因是“七分天災”的說法提出質疑,認為可能人禍是許多地方困難的主要原因。為了克服困難,糾正幾年來反“右傾”斗爭中對干部的錯誤批判和處分,當時一定程度上允許包產到戶。毛澤東對此不滿,當年9月,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批判“黑暗風”、“單干風”、“翻案風”。
任彥芳在書中說,蘭考縣出席七千人大會的縣委書記王金璧,回縣后沒有如實向縣委傳達中央七千人大會的內容,但他卻傳達鄧子恢挨批評的事(鄧同意包產到戶)。顯然,當時,盛行的是“寧左毋右”。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焦裕祿到任蘭考,不可能不按照當時左的方針辦事。任書中說:焦一到蘭考,就抓兩個階級、兩條道路斗爭,鞏固集體經濟,剎單干風。焦時時刻刻不忘依靠貧下中農。在生產救災、除“三害”(水患、風沙、鹽堿)和種麥中,都集中力量揭階級斗爭的蓋子,抓兩條道路的斗爭。任書說:“他拼上老命,去鞏固集體經濟。他如果不這樣努力去做,而是有所抵制,有所懷疑,那反而不是焦裕祿了。”作為一個基層領導,縣委書記,焦裕祿不可能超越歷史。
求實的焦裕祿
可貴的是,在“左傾”肆虐的時代,作為基層縣級領導人的焦裕祿,沒有機械執行上級方針政策,而是盡可能結合實際,關心群眾生活。
任書收錄1963年12月25日焦裕祿在公社書記會議上的講話:“應把糧食統銷,安排社員生活作為最中心的任務,其他工作和統銷相矛盾的一律向后推一下。”“給群眾休養生息的機會,更好地集中力量把生活安排好,把副業生產抓好。”焦還在一次會上,針對在火車站勸阻外流人口一事說:“我們揚湯止沸,不如釜底抽薪,我們要從根本上解決外流,就要把家里生產生活安排好,讓他們不再想外流。”
關于“借地”,這是困難時期,地方政府放松強迫集體化的權宜措施,讓一部分地借給農民種,收獲歸自己,民眾稱這是“救命政策”。按照批單干風的方針,要把“借地”收回。蘭考縣一些地方,采取了“明抽暗不抽”,“挪用借地,抽回東地借還西地,上級催得緊就收”等辦法。焦裕祿對抽回借地是執行的,但不一刀切,采取靈活作法。任書評點說:“這一點,在當時需要何等的膽識!”
敢于向人民承認錯誤
焦裕祿主持討論并親手修改過的一篇縣委上報省委地委的報告中說:“蘭考有36萬勤勞的人民,116萬畝可耕的土地,最適宜種植小麥、大豆、花生、紅薯等農作物,次宜種棉,河灘洼地宜種葦、蒲,河岸堤旁及沙堿地均可造林、曬鹽、熬堿,并盛產泡桐、杞柳,聞名中外。但是近幾年來,每年收獲卻養活不了自己……”由于錯誤的“以蓄為主”的方針,“內澇成災,加重了地表堿化程度,擴大了堿化面積”;“毀林悶(燜)炭”,“毀林作薪”,防風固沙的農田防護林遭到了嚴重破壞,致使風沙重起”。
任彥芳的繼父回憶:討論這個文件時,有人主張不要提工作中的錯誤。焦裕祿說:“你不敢承認我們瞎指揮犯了錯誤,你就得不到蘭考人民的信任。……這是過去縣委犯的錯誤,也是中國共產黨的縣委嘛,你就要承擔過去的縣委的錯誤,這樣蘭考百姓才相信你,才不會再犯同樣的錯誤。我們要向蘭考百姓父老認錯啊。”
任書評點說:“這個報告敢于向人民說出真相”。
焦裕祿的品格精神
任彥芳《我眼中的焦裕祿》一書中,大量資料對于焦裕祿的精神品格有贊頌,有例證,難以盡述。讀后最突出的印象,就是他的刻苦自勵,將全部身心奉獻給了改變蘭考貧窮落后的偉大事業。
焦裕祿對待自己和家人嚴格要求。他身為縣官,不貪不沾。連自己的孩子因別人領進劇院,未花錢看了電影看了戲,他也讓孩子補交票款。自己的衣服破了即補,艱苦樸素到了極致。他生活貧苦,工作那么多年,不僅沒有奉養老人,相反,“他回家看多年不見的老母親還借了300元。他說要用他的工資還清。”然后省吃儉用,積攢余款,“他還了100元后,便因病住院了。整兩個月后,5月14日,焦裕祿去世。他去世時還欠200元。”這就是焦裕祿的經濟賬。
而他對于人民的生活,無比的關切。訪貧問苦,無衣無食者,有病者,危難者,他竭盡全力予以救濟,排憂解難。
他對解決蘭考的風沙、內澇、鹽堿災害,心急如焚,一心撲在“除三害”改變蘭考面貌的事業中。沙塵滾滾,他勞碌在田邊地頭;逢天下雨,他去考察水澇的具體情形。
“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焦裕祿是真正無愧的踐行者。
焦裕祿的悲劇
焦裕祿是個英雄,是個革命英雄,仔細思索,他又是一個悲劇英雄。他主觀上把全部身心獻給蘭考人民,為他們謀求幸福,然而,他有生之年沒有讓人民獲得幸福。他曾說:“我就不信水澇鹽堿得不到治理。”但他生前,他的夢想沒有實現。
焦裕祿逝世后15年,蘭考縣委書記刁文說:“焦裕祿一心為人民,把他累死了,可蘭考并未翻身。我們沒有老焦那樣的精神、能力,(卻)讓蘭考扔了要飯棍。關鍵是路線、政策,是包產到戶聯產承包責任制。這是合乎生產力發展的體制。可見,沒有好的合民心民意的體制,再有焦裕祿拼命也不行啊!”
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政治體制和僵硬的集體經濟體制下,無法改變農民貧困的命運。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
注:
[2]總書記,蘭考可以這樣說——圍繞焦裕祿、張欽禮周圍的謊言和真相
相關文章
「 支持烏有之鄉!」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