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文摘自:《李玲:有為政府、有效市場、有機社會——中國道路與國家治理現代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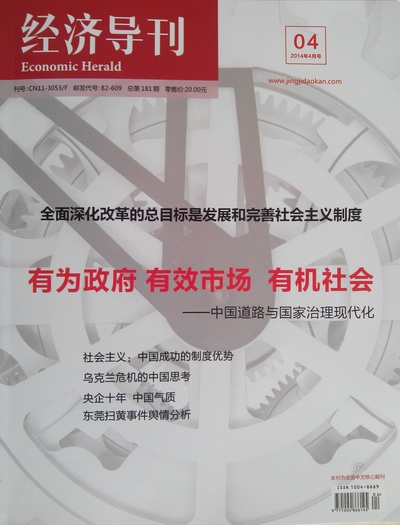
社會無非是人的聯合,但關鍵是什么人的聯合。“社會”既可以是少數人組成的特殊利益集團,他們人數很少,但是掌握巨大的資源和政策影響力,甚至可以左右政府政策。“社會”也可以指由最大多數人民組織起來,有序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進行自我管理和治理的主體。但是,后者要組織起來和發揮影響,比前者困難得多。
被稱為“利益集團鞭撻者”的美國政治學家奧爾森認為,行會、工會、卡特爾以及議會院外集團等“分利集團”,只關心自身的福利,而不關心社會總福利。一旦他們獲得政策影響力,就可能阻礙技術進步、資源合理配置,典型的例子是美國的農業和軍火集團。印度一直奉行自由貿易政策,但并未由此獲得繁榮與發展,主要是由于種姓制度確立的分利集團起抑制作用。二戰后德國和日本迅速發展,則得益于戰爭徹底打碎了利益集團。值得一提的是,奧爾森認為,中國改革之后之所以經濟快速發展,正是因為改革前的一系列政治運動打破了利益集團,使得改革初期具有十分公平的起點。
既然利益集團可以組織起來,那么人數更多的人民大眾為什么不能組織起來呢?奧爾森另一篇著作《集體行動的邏輯》中指出,普通勞動者利益分散,人數越多,搭便車的沖動就越大,從而無產者是最難組織起來的。
中國社會結構的古今變遷,是說明國家和社會關系的典型例子。中國封建社會存在著周期性的皇權、地主士紳、小農三者關系的變遷。皇權代表國家,而受過儒家教育、對政權認同的地主和士紳是政權的依靠,由他們主持的、以宗法關系為基礎的鄉村社會自治,提供了基層的公共產品,是封建社會長期穩定的原因之一。但是一旦承平日久,地主士紳以及同他們聯系的官僚體系,通過土地兼并、高利貸和壟斷商業經營盤剝小農,就形成特殊利益集團,威脅王朝穩定。周期性的農民戰爭,以及王朝初期均田免賦的政策,便是抑制和打碎這種利益集團的措施。商鞅、王安石等歷史著名的變法,針對的也是這種“不作而食,不戰而榮,無爵而尊,無祿而富,無官而長[六]”的寄生性的分利集團。
總的來說,中國傳統社會具有鄉村自治的傳統,成為維護大一統帝國基層穩定的力量。以至于直到現代,許多人依然推崇這種自治傳統,其中最有影響的當屬蔣介石作為其治國方略發表的《中國之命運》,他寫道:
中國固有的社會組織……其自治的精神,可以修齊舉的實效,而不待法令的干涉。其互助的道德,可以謀公眾的福利,而不待政府的督促。……五千年來……社會的風氣仍能精誠篤實,勤苦儉樸,崇禮尚義,明廉知恥,我們中華民族所以能久于世界,此實為其基本原因[七]。
這段對鄉村自治田園詩般的描述,同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所寫的土豪劣紳惡行,完全是兩個世界。那么誰錯了呢?蔣介石看到了鄉村自治對于穩定農村的作用,但他沒看到,這種穩定是一種消極的辦法。在穩定的同時也使農村長期保持自給自足的生活方式,無力集中資源實現技術進步,造成了封建社會的停滯。一旦進入工業化、城鎮化的時代,在工商資本和金融資本的沖擊下,這種制度就迅速瓦解。從清末到民國,農村又上演了土地兼并的循環,不同的是,這次豪強地主和新興的工商資本(以及外國資本)相結合,對農民的盤剝更加嚴重。而蔣介石相信“鄉村自治”,根本沒有把土地問題和農村政權建設擺上他的日程表,征稅、征兵只能依靠土豪劣紳,苛捐雜稅多如牛毛,進入蔣先生口袋的卻有限。四川一份調查推測,保甲長把1/3的攤派金裝入自己腰包。1945年初《大公報》記載,農民的負擔五倍于政府下達的稅負[八],中間差額就被地主豪強拿去了。這逼得國民黨為了打仗不得不借助美援、印鈔票,結果得罪了從中產階級到農民的各個階層,注定了失敗下場。從這個意義上說,國民黨敗就敗在利益集團林立、基層社會潰敗和國家治理能力缺失。而這就是今天一些人懷念的“政府放權、社會自治”的“民國范兒”。
民國時期,一些主張改良的進步學者希望通過組織農村合作化,重建一個新社會,其中就有毛澤東的摯友梁漱溟。1938年1月,他帶著《鄉村建設理論》來到延安,同毛澤東徹夜長談。梁認為,應該把農民組織起來,作為新社會的基礎。這同毛澤東的認識是一致的,毛澤東也認為“分散的個體經濟……不是民主社會的基礎,這是馬克思主義區別于民粹主義的地方”[九]。但與梁漱溟主張和平地把農村組織起來不同,毛澤東認為只有在革命的基礎上,才能打破固有的社會結構,真正把農村和農民組織起來。
梁漱溟同晏陽初等一大批學者,在各地進行了農村組織和鄉村建設實驗。但是在利益集團已經形成的情況下,鄉村合作組織也被俘獲為利益集團的工具。以高利貸為例,1936年薛暮橋在《中國農村問題》一書中指出,“銀行資本決不愿同地主豪紳發生沖突,而是聯合起來剝削貧苦農民。銀行放款要通過富農掌握,未到手時便扣去抵償佃租和利息,再用三分四分的高利轉借給貧苦農民”。從而,合作社也成為剝奪農民的工具[壱拾]。
鄉村建設實驗的失敗、中國革命的成功,證明了毛澤東的觀點。中國共產黨和那時的各種利益集團都沒有利益糾葛,從而可以放手發動群眾,給農民切切實實的利益,贏得了農民的擁戴。新中國成立之后,又通過人民公社把工農組織起來,在資本和技術短缺的情況下迅速實現工業化,保障了基本民生。有人認為這個時代的“全能政府”擠占了社會的空間,這個認識不準確。實際上,當時政府的許多職能是下放給企業、社區和公社的,連國防和警察這種國家職能,在基層也主要不是依靠財政供養的正式隊伍,而是靠自治組織供養的聯防隊、民兵。一部分城市和全部農村的醫療、教育,主要也不是由財政支出,而是由集體經濟保障的。
這個時期是現代化第一次影響到中國的農村和基層。中國共產黨把工農組織起來,開始形成中國特色的“市民社會”,我們將其叫做“人民社會”,其特征是國家-社會的合作關系,優于西方社會國家和市民社會之間的對立。國家和社會對立,雙方博弈往往關注短期利益,資本家可能形成利益集團,但工會也可能形成利益集團,妨礙國家競爭力。新中國的國家-社會一體化格局,國家和人民具有共同利益和目標,國家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人民則主動響應國家號召,為長遠利益而做出暫時犧牲,超出了奧爾森的所謂“集體合作的困境”,可謂是一種更高層次的合作。中國的“人民社會”超越了西方的“市民社會”。
為什么能做到這一點?
首先,中國經過長期的革命,打破了土豪劣紳、買辦資本、官僚資本,在農村實現了土地平均分配,在城市實現了生產資料全民和集體所有,從而為建立真正的自治奠定了平等的社會基礎。這和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的觀點——美國立國之初就有鄉村自治的傳統,是因為最初從歐洲來到美國的殖民者收入、教育水平都差不多,沒有任何貴族和利益集團[壱拾壱]——是一致的。但是中國沒有發現新大陸這種得天獨厚的條件,就只能通過革命重新塑造一個公平的起點了。
其次,新中國建立了強有力的國家,從而可以有力抑制利益集團的形成。而且國家通過一系列政策,打破原有精英的各種特權,把資源向普通工農分配,維護了公平的社會,為自治奠定了經濟基礎。
第三,新中國的成功,還有賴于國家對外部環境的治理。堅持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團結第三世界,打破了美蘇兩個大國共治世界的圖謀,從而避免國內的社會自治受到外部勢力干擾。
這就是為什么毛澤東說“我們是馬克思加秦始皇”。是秦始皇,建立了大一統的、單一制的民族國家,實現了富國強兵;是馬克思,把一盤散沙的勞動者組織起來,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今天人們在批評“強政府”時可曾想過,從1840年鴉片戰爭以降,中華民族在那風雨如磐的漫漫長夜,最期待的就是有一個能夠外御列強、內抑豪強的“強政府”?一個能夠有效治理國家、維護社會公平的“強政府”?
相關文章
「 支持烏有之鄉!」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