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時候,死人就是比活人有用。某些人為了自己的不可告人的目的,經常會向摸金校尉學習,并且青出于藍而勝于藍。他們從陰司水牢中拉出那些早已被歷史拋棄和懲戒的僵尸粽子,然后為他們穿衣打扮、拍脂摸粉,焚香祝告,給它們舉幡招魂,將這些粽子既有的各種遺毒和陰氣消化吸收和轉化創新,最終發揚光大,將其打造成為他們的目的服務的活死人。
近日,《武訓傳》在批爛批臭60年后再次重新發行,又一個為某些人服務的活死人出現了,從此不斷抖落身上的尸粉灑向人間,荼毒生靈,貽害無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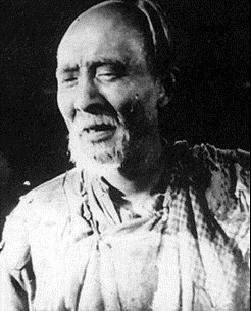
電影《武訓傳》的來龍去脈:
1948年7月當時的中國電影制片廠(“中制”)正式投拍此片。中國電影制片廠當時經營困難,經費上難以為繼,1948年11月初,在影片拍攝了大約三分之一的時候,影片便徹底停拍。1949年2月,昆侖影業公司以低價購得此片的拍攝權和底片、拷貝。孫瑜則加入昆侖公司繼續完成此片的拍攝。
1950年 《武訓傳》拍竣,年底公映。
據統計,在這幾個月中,各地報刊發表的有關文章共計55篇。在這55篇之中,只有賈霽、楊耳、鄧友梅等少數人對武訓和影片持批評態度。
1951年5月20日 《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的社論,該文經毛澤東修改審定。文章指出“《武訓傳》所提出的問題帶有根本的性質。像武訓那樣的人,處在滿清末年中國人民反對外國侵略者和反對國內的反動封建統治者的偉大斗爭的時代,根本不去觸動封建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并為了取得自己所沒有的宣傳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對反動的封建統治者竭盡奴顏婢膝的能事,這種丑惡的行為,難道是我們所應當歌頌的嗎?向著人民群眾歌頌這種丑惡的行為,甚至打出“為人民服務”的革命旗號來歌頌,甚至用革命的農民斗爭的失敗作為反襯來歌頌,這難道是我們所能夠容忍的嗎?承認或者容忍這種歌頌,就是承認或者容忍污蔑農民革命斗爭,污蔑中國歷史,污蔑中國民族的反動宣傳為正當的宣傳。”從此在全國展開對《武訓傳》的錯誤思想的批判,并被禁映。
1951年夏,由《人民日報》社和中央文化部發起,組織了一個十三人的武訓歷史調查團,赴山東堂邑、臨清、館陶等縣,先后進行了二十多天的調查。《武訓歷史調查記》是根據這次調查的材料由幾個人起草、經毛澤東閱改而成的。調查記分作五個部分。一、和武訓同時的當地農民革命領袖宋景詩;二、武訓的為人;三、武訓學校的性質;四、武訓的高利貸剝削;五、武訓的土地剝削。
1951年07月23日《人民日報》發表《武訓歷史調查團》。
周揚把對《武訓傳》的批判提到了理論的高度:“政治上反人民,思想上反歷史,文學上反現實主義。”周揚認為,“因為新中國是革命是武裝斗爭的成果,如果強調改良主義的合理性和正當性,當然,就等于質疑了革命的合理性和正當性。”至此,周揚完全道出了這場批判運動的本質。周揚于1954年在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擴大聯席會議上有一個著名的講話《我們必須戰斗》,他說“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第一次大規模對資產階級思想批判的運動。”,“它宣傳了資產階級的社會改良主義和個人苦行主義,實際就是宣傳的對封建統治者卑躬屈節的投降主義,而對人民斗爭的正確的歷史道路則作了不能容忍的歪曲和誣蔑。”
1986年4月29日,國務院辦公廳下發了《關于為武訓恢復名譽問題的批復》,為武訓平反。
2000年 “電影101工作室”在上海虹口圖書館放過一次《武訓傳》的錄像帶。
2005年 在紀念趙丹誕辰90年回顧展上,趙丹之女趙青在相關部門批準下,從中國電影資料館借出拷貝,在上海影城放映,被媒體稱為“五十多年來重見天日”。
2009年5月20日 《中華讀書報》發表《“武訓復出”,彰顯天地良心》,由瞿旋創作、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武訓大傳》在京舉行新書發布會。在高調推出“武訓”的同時,出版社當場與北京小馬奔騰影視公司簽約影視版權,著名導演高希希將執導電視連續劇《武訓大傳》。
2010年6月1日,騰訊網制作專題:共和國辭典33期:武訓。
http://news.qq.com/zt2011/ghgcd033/index.htm
2012年03月22日 《新京報》:“新中國首部禁片”《武訓傳》修復出版,在線上線下出售。
新京報:《武訓傳》“重見天日”幕后尋蹤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2-03/22/content_325667.htm?div=-1
2012年3月27日鳳凰網制作專題: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解禁。
http://news.ifeng.com/opinion/special/wuxunzhuan/
批判武訓傳的歷史背景:
新中國初期對武訓傳的批判和80年代對河殤的頌揚都有其政治背景。只不過,前者是正向革命為了否定封建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統治意識形態,鞏固工人農民通過暴力革命完成翻身做主人獲得的人民政權;而后者是逆向革命出于徹底否定文革,制造傷痕文學從而告別革命,開啟一個一切向錢看的時代。
新中國初期對電影《武訓傳》的強勢批判,絕對不是空穴來風或一時興起的,批判《武訓傳》的重點不在武訓本人,而在于批判那些宣揚武訓的人和宣揚武訓精神的思想。中國共產黨雖然通過軍事和政治手段已經在1949年取得政權,但是新中國還面臨著政權的鞏固與建設的艱巨任務,同時存在著各種各樣或明或暗的舊有的破壞勢力,社會主義革命還沒有完成。一、中國共產黨內部面臨著是盡快由新民主主義革命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階段,還是長期停留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補一段資本主義的課的巨大爭論。各種舊勢力也希望繼續延續他們的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維護他們的特權;而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是要建設一個社會主義的新中國,真正實現人民當家做主,而不是繼續忍受剝削壓迫。二、在軍事上失敗的封建地主階級和國民黨反動派不甘心失敗,大肆利用各種文化和經濟手段不斷進行顛覆和滲透,意圖重新恢復原有統治。三、中國共產黨盡管獲得大多數新中國人民的擁護,但這馬列主義的社會主義思想并沒有完全在社會上的得到廣泛的傳播,社會上還存在著大量的陳舊的腐朽思想。封建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文化不會自動消亡,必然會繼續在各種領域中存在和發展。
同一時期,在全國展開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三反運動”在槍斃了被資產階級糖衣炮彈倒下的張子善、劉靑山,教育了全黨干部,1952年接著又開展一場“五反”運動,擊退了資本家的進攻。在合作化問題上,與劉少奇開展了針鋒相對的斗爭,又在黨內發動了對新稅制的批判,提出了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結合這些史實看夾雜在這些運動之中的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就顯得自然而必要了。
《武訓傳》所宣揚的不過是剝削制度下的小善,同剝削階級向人民群眾施以小恩小惠的虛偽慈善;而中國共產黨人在已經取得政權的條件下,完全有能力和手段,通過生產資料所有制的變更,真實消除剝削壓迫,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
為什么給《武訓傳》解禁,并大力宣傳?
從《武訓傳》的從開始公映到引起全國性的大辯論,從被封再到平反和解禁,始終伴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文化領導權的爭奪,以及關于階級斗爭思想的抑與揚,改良與革命的爭論,這種辯論將長時間伴隨著中國社會政治和思想的變化,可能在有階級和階級斗爭存在的時期內都是存在的。
隨著國內資產階級的再次出現和不斷成長壯大,大量工農群眾再次淪為被雇傭、被剝削和壓迫的弱勢群體,生產關系的變化必然需要一種解釋和維護這種階級關系和統治秩序的文化,舊有各種階級社會的腐朽思想死灰復燃,從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引進的各種同樣陳腐的毒藥同當年的鴉片一樣打著“福壽膏”的招牌來到風雨如磐的中國社會,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不斷的在各種領域成為輿論主流,在中國的文化輿論界出現了這樣一種局面,過去有的、過去沒有的和中國的外國的各種腐朽的反動思潮同時匯集。
中國自古有修史的傳統,中國人做事無論是小到處理家庭事務和鄰里關系,還是大到治理國家和國際事務,都會參考歷史中的事例和其中的規律。所謂禮失求諸野,政失求諸史,歷史觀的改變就是在改變中國人價值觀。
在社會主流思潮已經被資產階級思想意識形態占領的當下,《武訓傳》的僵尸復活是一件必然的事件,因為武訓的“利他”,實際上只是麻醉了被壓迫人民的反抗意識,而有利于當今資本家老板繼續低成本的剝削壓迫工農大眾,這個電影要告訴我們的是這樣的歷史:窮人在地主官僚統治之下受苦受難,僅僅是因為“不認字吃虧”,辦一個義學就可以解決問題;這就是說,不需要階級斗爭,不需要進行革命,只要磕頭募捐,便可以解決問題。而今天的工農大眾也應該逆來順受,只有靠資本家的施舍才能改善自己的境況,而不是通過組織起來依靠反抗實現本階級的政治和經濟訴求。
所以自然地資產階級最希望控制無產階級的價值觀取向,以利于的自己統治,無論是軍事的高壓統治,還是經濟的剝削和政治上的壓迫,都沒有將被統治者的思想文化按照統治階級自己的意愿去改造最根本和徹底,一個階級在思想被統治,那么他只能是自在的階級,不可能成為自為的階級,逆來順受是這個群體的最常見的表現,個別自發的反抗可能還會被同階級的人所反對和破壞。群眾成了一盤散沙,也就不會有真正有力量的反抗,,統治階級的統治就是最安全的統治。
主流媒體大搞歷史虛無主義,讓其肆意蔓延和泛濫,將從古到今的所有英雄人物和正面人物全部進行抹黑,或者對其解構后抽象肯定,具體否定,無限擴大他們的缺點和錯誤,將其占主要部分的優點和正確方面沖淡和抹殺。但是他們對待自己的喜歡的符合自己的利益的歷史人物,卻是接近編造虛構之能事一定要樹起來,在這方面,雖然口頭上他們否定意識形態的斗爭、不承認階級斗爭,但是實際行動中卻是階級斗爭年年講、月月講、日日講,對于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一天沒有放松過。不論武訓原型如何,他必然被按照當時的資產階級意識去被塑造和解讀。
新中國社會主義制度下是如何解決教育問題的
即便是回到《武訓傳》批判的歷史爭論的細節當中,剝削階級壟斷了教育資源,絕大多數中國人民處于文盲、半文盲的狀態,共產黨人如何解決教育問題?是向封建地主階級下跪求的施舍,還是通過革命建立社會主義制度,通過國家行政手段平均教育資源?這一點我們可以對比舊中國和建國前30年的教育情況即可得知。
中國教育大事典1949-1990及新中國五十年統計資料匯編數據顯示,在毛晚年,中國普及基礎教育取得巨大成就。小學入學率即由1963年的57%,大幅提升至1976年的96%(同期印度小學入學率為1961年40%,上升至1978年58%)。毛澤東不但大增基礎教育,還大幅度提升初中及高中普通中學學額,普通初中招生數從1963年263.5萬大升至1976年2344.3萬,增加了近10倍。普通高中招生數從1963年43.3萬大升至1976年861.1萬。增加了20倍。文革期間,教育不僅沒有荒廢,而且使很多貧寒子弟獲得受教育的機會。新中國五十年統計資料匯編數據顯示,1963年前普通教育開支約占教育總開支45%,1963年后大幅提升至1969年的95.4%。1976年毛去世時為67.1%)。為推行現代化所必先實施的全民普及教育鋪平道路。
談到教育不能不談‘工農兵大學生’。由于建國初期能夠受到良好教育的多為國民黨時期的上層家庭。因此,大學里的新生也多為這個群體中產生的。而那些社會社會底層的工農子弟,卻無法享受到高等教育。存在著明顯的不公平現像。這是毛澤東倡導讓工農兵進入大學的原始動因。有人說是政治掛帥,雖然不能完全否定這種說法,但是,工農子弟能夠有機會上大學,無論如何也不能說是件壞事。雖然這樣的政策客觀上使那些‘上層子弟’受到排擠,但也并沒有完全杜絕他們。文革后,工農兵大學生受到冷嘲熱諷,似乎他們都是些不學無術之人,而事實上,這些人在各自崗位上都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著名的J10戰機的總設計師就是這樣的又紅又專的人才。
有些人論述毛主席晚年政績,刻意強調文革給城市一部分知識分子帶來的沖擊,避而不談文革一系列教育革命對當時占當時全國八成人口的農民教育水平的大幅提高,為未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提供了良好的基礎.
改革開放初期大量的廉價高素質勞動力恰恰是在文革時期儲備起來的,這一點與同時期的印度形成了鮮明對比。只不過由于新自由主義的誤導,改革開放的成果被外資和少數先富起來的人占有。反觀后毛澤東時代的三十年,盡管現在大學生比過去多了,但是農村人口的大學生,三十年間下降了50%。[此數字由廣東省社科院社會學與人口學研究所提供]很多貧困家庭無力供養大學生;在人人逐利,劣幣驅逐良幣的大環境下,很多中小學教育資源也逐漸荒廢,農村地區很多90后群體初中未畢業就已經加入到打工洪流中。
附
表一: 中國適齡兒童入學率簡表
年限 入學率(%)
1952 49.2
1953 50.3
1954 51.5
1955 53.8
1956 62.6
1957 61.7
1958 80.3
1959 79.3
1960 76.4
1961 63.4
1962 56.1
1963 57.0
1964 71.1
1965 84.7
1974 93.0
1975 95.0
1976 96.0
1977 95.5
1978 94.0
1979 93.0
1980 93.0
來源:中國教育大事典1949-1990,p324. 劉英杰主編,浙江教育出版社
表二 高等教育學生人數比較(萬人)
1947; 1949; 1965;
印度 26.6; 無數據; 152.8;
中國 無數據; 11.7; 67.9;
來源:中外教育比較史綱
表三: 小學未入學率(占同齡人口的%)
年限 印度 中國
1951 71.5 50.8
1961 59.9 36.6
1973 37.8 7.0
1978 42.1 6.0
1992 8.18(1986年印度公布“國家教育政策”,嘗試推行普及教育)
印度:6-14歲未入學(毛入學率)比例
中國:小學適齡未入學率
來源:中外教育比較史綱
表四: 中國普通中學招生統計表 招生數(萬人)
年限 初中; 高中
1949 34.1; 7.1
1950 50.1; 10.8
1951 80.6; 9.1
1952 124.2;14.1
1953 81.8; 16.1
1954 123.6; 19.5
1955 128.2; 22.1
1956 196.9; 37.4
1957 217.0; 32.3
1958 378.3; 56.2
1959 318.3; 65.6
1960 364.8; 67.8
1961 221.8; 44.7
1962 238.3; 41.7
1963 263.5; 43.4
1964 286.6; 43.8
1965 299.8; 45.9
1966 272.7; 20.7
1967 198.3; 13.6
1968 648.5; 63.0
1969 1023.4; 103.6
1970 1176.3; 239.0
1971 1234.9; 321.3
1972 1247.1; 479.0
1973 1139.0; 452.0
1974 1345.1; 541.1
1975 1810.5; 633.1
1976 2344.3; 861.1
1977 2367.7; 993.1
1978 2006.0; 692.9
1979 1727.8; 614.1
1980 1550.9; 383.4
1981 1412.7; 327.8
1982 1363.1; 279.3
1983 1317.1; 259.8
1984 1302.5; 262.3
1985 1349.4; 257.5
1986 1386.6; 257.3
1987 1394.3; 255.2
1988 1340.4; 244.3
1989 1309.3; 242.1
1990 1369.9; 249.8
來源:中國教育大事典1949-1990, p337,338. 劉英杰主編,浙江教育出版社
中國財政支出方向的比較與簡單分析
1954 1958 1978 1979 2000
教育 教育支出 34.605 143.5 112.66 132.1 361.9
教育支出比例 14.05% 10.62% 10.14% 10.37% 2.28%
引自:新中國歷年財政報告
一個完整的文化教育體系
剛解放時,全國專門從事科學研究的知識分子不超過500人,各種新技術的研究兒乎都是空白,全國大多數人都處于文盲、半文盲狀態,而到70年代,我國已建立起比較完整的教育體系和龐大的知識分子隊伍(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2年版第119頁):
一是在“文革”結束時基本實現了義務教育,教育經費的投入最高曾達國民生產總值的5%,建立了近千所大專院校、數千所的各類中專及完善的基礎教育體系。就小學入學率方面,中國遠超出大多數其他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低收入國家,僅稍遜于先進工業化國家。就中學入學率來說,中國也遠遠超出多數發展中國家。 1977年小學在校人數創記錄1.5億,普通中學在校人數6780萬人。而1977年之后的幾年,大量學校關閉,僅中等學校在校生到1982年已經減少了 2000多萬人,中國教育投資不及非洲的烏干達,失、輟學兒童人數世界第一。
1949-1978年,全國各類高等學校畢業生累計達294.63萬人,中等專業學校畢業生累計達520.65萬人。1949-1965年畢業研究生達1.6萬人,派往蘇聯及東歐國家的公派留學生高達四五十萬,派往西方國家的留學生也是逐年增加。
二是讀中小學、大學幾乎不要錢(大學每月還享受到17-23元的助學金)。這樣的免費教育體系,在今天已經成為千古絕唱。而2004年前的中國,是世界上唯一還在針對初、中等教育征收高昂學費的大國,敲骨吸髓的學費要“傾家蕩產”透支35年收入才可上4年大學,有無數品學兼優的貧困生被大學拒之門外。
三是新中國的四次掃盲高潮。國人的識字率從1949年20%上升到1976年80%。而2002年,根據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對中、印發展的研究報告,我 國文盲約8507萬,其中2000萬左右為15~50歲的青壯年文盲,文盲總數超過世界總數的10%,僅次于印度,居全球第二;目前中國的初級教育,大約 相當于日本1900年的水平,落后100年。
宣傳《武訓傳》宣揚民間辦教育參與公共服務與NGO的關系
武訓的僵尸復活,他還被貼上了另一個重要的標簽,民間辦學,無非是不要政府參與,建設他們的小政府大市場社會,
一方面讓政府退出對經濟的干預和控制,讓所有的國有企業私有化,完全放任國內私企追逐利益最大化中的剝削壓迫工農大眾,完全放任外資不斷的控制中國的經濟命脈,對此問題以后眾多文章批判故不作班門弄斧之舉。
另一方面,讓更多的社會組織來參與社會管理,這是從體制內外的各種精英多年來表達的訴求,社會組織大量出現,都是受到各種思潮的影響,更重要的是受到各種基金會的支持,而這些基金會多來自國外,從各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歷特別是獨聯體國家的相關情況中我們知道,帝國主義從來都是通過各種NGO(非政府組織)和宗教進行大規模的滲透,通過這種組織和活動,宣傳西方的各種自由化思想,制造反政府的輿論,培植反對黨,利用各種機會從事顛覆活動。
可以看看各種宣傳社會組織接管社會功能的檄文:隨著各種力量大力推進政治改革,借機加快發展社會組織,也就是通常所說的NGO,這種社會組織正在內外各種力量的策動和支持下蓬勃的發展,正在形成一種影響中國社會變革的政治力量,而這種力量到底能代表誰?能給中國社會帶來什么?
汪洋思路:放權給社會組織使其承擔社會管理職能
http://www.ghchina.org/show_ax.php?nid=8062
汪洋:大力培育發展和規范管理社會組織
http://gongyi.ifeng.com/news/detail_2012_01/10/11870117_0.shtml
廣東將大力培育發展和規范管理社會組織,將社會組織能夠“接得住、管得好”的事逐步轉移過去。今年上半年將出臺向社會組織放權的指導意見,明確省級第一批轉移職能目錄與購買服務目錄,各地級以上市也要制定出臺市級政府的相應兩個目錄。
汪洋:逐步向社會組織放權 促成良好法治氛圍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1_05/22/6546539_0.shtml
鼓勵社會組織“百花齊放”
http://www.zs.gov.cn/main/zwgk/open/view/index.action?id=52359
鼓勵社會組織推動“萬能政府”轉變為“有限政府”
http://news.gd.sina.com.cn/news/2011/07/22/1162206.html
國務院:鼓勵社會力量及境外投資者辦醫療機構
http://www.gxnews.com.cn/staticpages/20120322/newgx4f6aedcf-4907656-2.shtml 國務院辦公廳轉發發展改革委衛生部等部門關于進一步鼓勵和引導社會資本舉辦醫療機構意見的通知
http://www.gov.cn/zwgk/2010-12/03/content_1759091.htm
新華日報:發展社會組織不妨遵循“蘑菇理論”
http://www.chinanpo.gov.cn/1940/52214/index.html 政府與社會組織之間的管理關系宜松散。政府可以建立資助機制或購買社會組織服務,但界限一定要清晰,切不要在“政府大院”里種“蘑菇”。
溫家寶:政府事務性管理工作可適當交給社會組織
http://www.chinanpo.gov.cn/3201/52105/index.html 要進一步完善政策措施,積極支持發展社會互助團體和組織,鼓勵企業、團體、家庭及個人開展社會互助和慈善活動。
胡舒立:民政部長談“結社”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25437 李立國:現在全國登記成立的社會組織,達到46萬個。受雙重管理體制等原因未登記而在活動的組織,有估計100萬的,也有估計數量更多的。取消雙重管理體制后,這些組織會申請登記,可能導致登記成立的社會組織增加,監管社會組織的工作量增加。
境外NGO在中國15年
http://www.gongyishibao.com/News/201008/129863.aspx
民政部發布報告 稱中國NGO數量以超10%速度增長
http://news.sohu.com/20070529/n250280497.shtml ,報告指出,2006年我國民間組織數量比上年度增加10.6%,目前總量達到35.4萬個。
這些龐大的NGOs之間的復雜聯系,織就了向世界傳播美國“民主”的平臺。
西方通過各種NGO,以所謂人道主義救援、維護人權、推廣民主進程、維護宗教自由和新聞自由等各種借口,對發展中國家進行滲透,培植親西方的代理人。而且由于這些非政府組織具有獨立性、社會性、非營利性并得到美國政府資助,因此 既充當了美國政府的代言人又避免了那種美國政府親自出面,引人反感的尷尬與無奈,極易以非政府組織特有的親和力和獨立形象迷惑受眾,潛移默化地輸出美式 “革命”。“顏色革命”正在改變歐亞大陸上的政治地圖,而美國政府用來調制這些“顏色”的調色板,正是無處不在、形形色色的非政府組織(NGO)。某些國際NGO除了意識形態,還有其利益性和集團性。這種特點決定了其種種行為,有較為強烈的目的性,甚至代表著某些政治集團和利益集團的偏好。正如普京總統指出:一些外國非政府組織的首要目標,實際上是為其母國的利益服務,而不是真心實意地幫助俄羅斯人民。
無論武訓如何的僵尸復活,在人民群眾在一次一次的現實教育面前,已經不斷的覺醒,在人民群眾行動起來后,武訓將被挫骨揚灰,在紅日再放光芒后,武訓必將別打入十八層地獄,永世不得托生。
附文:
西方非政府組織的國家背景
http://www.haodaxue.net/html/66/n-10666.html
來源: 《新聞大學》 作者:劉小燕 、王潔
一、國際NGO:特征與功能
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動下,隨著全球公民社會運動的興起,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Organization,簡稱NGO)發展迅猛。 目前世界上各類NGO達數百萬之多,其中國際性NGO超過35萬個,國際上確認的國際組織90%以上都是NGO。僅美國一國的NGO已經達到160萬個之 多(僅基金會就有4萬個),加拿大各類NGO達107.8萬個(其中7.8萬個慈善機構,10萬個非營利組織,90萬個基層組織)。[1]
截至2005年的統計,世界上享有聯合國經社理事會咨商地位的2719個NGO,發達國家占70%,而發展中國家僅占30%;與聯合國新聞部保持有 “正式”關系的近2000個NGO中,發展中國家僅占16%。在大多數聯合國會議上,至少80%以上的NGO與會者來自發達國家,窮國的聲音很難被國際社 會聽到,發展中國家的利益難以得到平衡和充分保護。也就是說大部分國際NGO網絡的節點在發達國家,成為信息的接受和發送中心。美國和歐洲是國際NGO最 核心的國家和地區。而發展中國家的國際非政府組織又往往與發達國家有密切的關系。其總部一般設在西方,援助的項目資金大部分也來自西方,領導人員可能來自 發達國家,開展活動的理念與方式也源于發達國家。再加上發達國家的國際NGO享有話語權,在議題的設置上有操控權,發展中國家的NGO事實上處于從屬地 位。[3]
現代國際政治,不僅國家行為體在起作用,非國家行為體影響亦巨大。國際NGO作為一種力量,構成了國際政治變革的重要動力。雖然在國際政治中國家仍 然是主角,但國際NGO發揮了約束、限制和影響國家的重要作用。這種影響可以表現為對國家主權的挑戰,對外交政策的干預,對國家形象的塑造(包括正面和負 面的構建),對全球化的應對等。
國際NGO主要以道德理念和價值觀為核心,與國家和其他行為體建立互動關系,形成一種網絡,在志愿、互利、橫向交往和交流模式的基礎上建立起固定的 聯系和組織形式。在此過程中,國際和國內NGO通過“回飛鏢”(Boomerang)模式來對國家施加影響:如果國家與其他國內行為體之間的交流渠道被堵 塞,國內的NGO就會繞過其政府,直接求助國際盟友的幫助,力求從外部對其國家施加壓力,促使本國的政策發生變化。[4]應當看到,NGO具有雙重性,既 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一面。正如英國《新科學人》雜志所評論的:“當它好的時候,會很好,促進社會的良性發展;當它糟的時候,會很糟,它只顧自己,毫 無責任可言。”
二、國際NGO:西方政府對外傳播中扮演的角色
在國家(廣義上的政府)對外傳播主體問題的認識上,西方國家認為政府與非政府組織同樣重要。西方非政府組織(NGO)或配合政府的行為,為政府拉高 聲勢;或補充、代替政府去完成政府不便出面或難以完成的使命。譬如美國對外推進民主一直是美國政府重要的對外戰略目標。美國政府有很多機構直接從事海外推 進民主計劃,如“美國國際發展署”及“美國國務院民主、人權和勞工局”等,這些機構為那些符合“民主標準”的國家提供大量資金,以促進和鞏固全球民主。同 時,美國廣大的NGO在其對外推進民主的進程中也扮演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主要包括國家民主基金、國際事務國家民主研究所、國際私人事業中心、美國國際 勞工團結中心、國際選舉體制基金、自由之家、歐亞基金會、卡特中心等。[5]很多NGO都帶有較強的意識形態偏見和一定的政治利益,有的被西方利用當作對 外滲透、干預和擴張的工具。西方國家將NGO納入自己的軌道,將其當作可變通的實現自己目標的途經。尤其在“顏色革命”中充當急先鋒的美國NGO,如愛因 斯坦研究所,及其所屬“人權基金會”、“民主價值基金會”及“宗教自由基金會”,OTPOR(一個學生團體。塞爾維亞語“反抗”之意),“自由之家”, “國際共和研究所”,“索羅斯基金會”,“開放社會基金會”等。
(一)NGO與“顏色革命”
對別國實施政治滲透,輸出美國的價值觀念,是美國推行霸權政策的慣用手法,也是美國除軍事手段以外推翻別國政府的一貫做法。數年來,美國對這種做法 不斷創新,以“推廣民主”為包裝,以鼓動有關國家民眾開展街頭抗爭的方式,最終達到推翻政權的目的。這種做法被稱為“顏色革命”。在這一過程中,西方國家 利用NGO推波助瀾,有時是赤裸裸的,有時又極其隱蔽。從以下事件中也可見其端倪:
1、在獨聯體等國家資助策動“顏色革命”。由于國際NGO在當前世界中的地位和影響越來越重要,一些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在對外政策中越來越多地利 用國際NGO來推行自己的民主價值觀。在獨聯體國家格魯吉亞的“玫瑰革命”、烏克蘭的“橙色革命”、吉爾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中,雖然各個國家存在內 在的政治、經濟、社會誘因,但西方NGO無疑起了推波助瀾和核心領導作用。
2005年5月18日,美國總統布什強調,美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推行“民主”,進行政權更迭,幾乎耗費了3000億美元資金,而在其他許多國家推動 “顏色革命”,僅僅花費不足46億美元。事實證明,美國政府扶持的一些國際NGO成為西方推動“顏色革命”的急先鋒和馬前卒。這些組織通過指導反對派活 動、組織集會抗議、利用輿論施壓等方式,最終達到了改造他國政權的目的。據美國有關機構統計,在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推動下,20世紀90年代以來,東歐、 中亞地區的NGO增加了四五倍。其中,美國在中亞國家幫助建立NGO的工作更是不斷取得“重大進展”。目前中亞國家的NGO已經超過一萬個。這些組織在前 南斯拉夫、格魯吉亞、烏克蘭和吉爾吉斯斯坦的“政權更迭”中都發揮了核心作用。[6]
除了赤裸裸的金錢援助外,最厲害的一招就是通過NGO控制或影響輿論,為西方實現滲透和演變服務。西方國家一方面支持本國的電臺、報刊和電視臺走向 國際,在發展中國家“落地生根”,樹立“公信力”;另一方面,以新聞自由等為幌子,不斷施壓發展中國家開放媒體管制,資助發展中國家創立所謂的“獨立”電 臺、電視臺和報刊。在西方資助下,中東歐和中亞多數國家都允許西方的電臺和電視臺落地或成立各種“獨立”媒體,在格魯吉亞和烏克蘭“顏色革命”中,許多選 民投票支持親西方人士上臺,正是西方媒體在當地發揮影響力的結果。
2、資助OTPOR等組織推翻米洛舍維奇政權。1999年由美國政府資助的民主黨對外活動組織曾邀請20多個塞爾維亞反對派領導人齊聚布達佩斯,商 討共同推翻米洛舍維奇的方案。最終使米洛舍維奇政權2000年倒臺的,正是一個由青年學生組成的團體—OTPOR(塞爾維亞語“反抗”之意)。該組織由 “顏色革命”推手之一的羅伯特?赫爾維(曾任美國駐緬甸大使館武官,后追隨吉恩?夏普)1998年10月親手組建。他認為,非暴力革命的重點培訓對象是年 輕人。在愛因斯坦研究所和美國另一家NGO的資助下,赫爾維帶領OTPOR的骨干成員,在布達佩斯建立了一家“非暴力抵抗中心”,專門培訓來自其他地區的 “年輕革命分子”。[7]
3、對中東地區和南美洲的NGO“資助”。2002年8月,美在發動伊拉克戰爭前,啟動了一項總額達660萬美元的非政府資助計劃,名義上是資助各 種NGO在伊拉克境內及其周邊地區進行人道主義救援,實際上是利用NGO幫助美國收集情報,為其打擊伊拉克提供便利。美國國際開發署曾向委內瑞拉的一些非 政府組織提供資助,以策動這些組織從事反政府活動。接受資助的,有不少是反查韋斯政府的組織。美國知道這樣做并不光彩,所以在有關資料中隱去了這些受援組 織的名稱。美國暗中資助反政府組織的做法,引起了委內瑞拉官方的強烈反應,委議會要求美方公布真相,并要將美政府告上法庭。[8]
4、向緬甸滲透,策動“藏紅色革命”。2007年9月,緬甸爆發被西方媒體稱為“藏紅色革命”的政治危機。事實正如英國《金融時報》2007年12 月6日文章所披露,美國在這場危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過去3年中,“顏色革命精神教父”吉恩?夏普和他的愛因斯坦研究所,在泰緬邊境地區,培訓了 3000多名來自緬甸各地的反對派,其中包括數百名僧侶。培訓內容除非暴力革命的各種策略和方法外,還包括如何與警察等現政權維護者展開溝通的技巧。此 外,愛因斯坦研究所還為這些人提供物質上的資助,比如為僧侶們提供手機等通訊工具。這都為2007年9月僧侶策動的大規模示威活動作了鋪墊。事實上,愛因 斯坦研究所1989年已開始在緬甸展開秘密活動。當時,美國政府曾一次性撥給該所5200萬美元,作為在緬甸活動的專用經費。愛因斯坦研究所還定期向美國 國會和政府提交報告和計劃,在獲得許可后,由研究所下設的“人權基金會”、“民主價值基金會”及“宗教自由基金會”等具體實施。[9]
(二)NGO與幕后推手
1、通過先資助西方NGO,然后通過其間接資助發展中國家NGO,來實現西方對外滲透。
香港《紫荊雜志》2008年6月載文指出,西方勢力借非政府組織滲透發展中國家主要有三大手段。一是資助、培訓對象國家的各種NGO來施加政治影 響。二是利用NGO的渠道進行軟性滲透。即西方通過各種NGO,以所謂人道主義救援、維護人權、推廣民主進程、維護宗教自由和新聞自由等各種借口,對發展 中國家進行滲透,培植親西方的代理人。三是通過NGO控制或影響輿論,為西方實現滲透和演變服務。事實上,作為殺手锏,西方國家為了消除被援助國政府和民 眾對西方政府直接援助的反感,更擅長通過首先資助西方NGO,然后通過西方NGO,間接資助發展中國家NGO來實現西方對外滲透。
譬如Internews這一投身于支持“世界范圍開放性媒介”的非盈利組織,[10]除了對國家和資本的財政資助的嚴重依賴之 外,Internews與美國國家和主要傳媒集團有緊密關系。其董事中有一位美國在線-時代華納的高級副總裁和一位美國議員。這個機構活動范圍甚廣。從 1992年起到2001年,該機構培訓了超過18000位專業媒介人員,它和2100個以上非政府電視臺和廣播臺有工作關系,在前蘇聯、前南斯拉夫、約旦 河西岸和加沙支持了19個非政府獨立電視網絡的發展,創立和或資助了29個媒介協會,僅在2001年就制作近730小時的電視和廣播節目,其潛在受眾達3 億600萬之多。此外,它還向前蘇聯和前南斯拉夫的獨立電視臺提供了超過1000小時的國際記錄片節目。從其活動的范圍和尺度以及區域重點來 看,Internews毫無疑問是最有影響力的非政府傳媒組織之一,它所促進的正是美國向前社會主義地區和伊斯蘭地區輸出自己認同的民主觀念和美國新聞價 值和實踐的議程。[11]
2、利用NGO力量實現政府難以達到的政治目標,是美國人一貫的做法,并屢屢成功。
很多時候官方講話沒有民間的聲音有效,有些話官方難以啟齒,但給NGO去做似乎順理成章。美國長期以來不屑與蘇丹乃至整個非洲建立更為密切的關系, 所以美國的聲音在這片土地上影響力有限,于是美國啟用了其助手——NGO。達爾富爾夢(DreamforDarfur)便應運誕生。當眾多類似組織在美國 政府的資助下開始運作時,其巨大能量便顯現出來了。讓中國在國際上出丑、陷于尷尬境地,也是西方某些人權組織的既定策略,把北京奧運與蘇丹達爾富爾問題掛 鉤,純屬風馬牛不相及,但他們做到了。2007年3月28日,美國《華爾街日報》登載好萊塢演員米亞法蘿和他的兒子若南法蘿聯名寫的題為《種族滅絕的奧運 會》的文章,是世界范圍內第一次有人公開將北京奧運與達爾富爾問題掛鉤。同時,美國的NGO拯救達爾富爾聯盟(SaveDarfurCoalition) 向兩家美國企業施壓,要求其出售投資蘇丹石油產業開發的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股。[12]國際特赦組織、人權觀察組織、國際公義聯盟 (CoalitionforInternationalJustice)等老牌號NGO與拯救達爾富爾聯盟遙相呼應,在全球范圍內張揚他們的觀點。
3、美國等西方國家利用國際NGO推行自己的價值觀。美國資深政客、共和黨總統參選人麥凱恩,2007年11月在美國《外交事務》雜志上刊文,標榜 自己的外交立場是“必須扶持全球民主力量”。麥凱恩自1992年起,開始擔任美國“國際共和研究所”[13]理事會的主席。美國總統布什在該研究所舉辦的 2005年度“自由獎”頒獎儀式上宣稱,20多年來該研究所“在100多個國家的民主變革斗爭前沿努力工作。正是由于它的作用,今天的世界才變得安全了、 自由了、平靜了。”目前,“國際共和研究所”在全球設有多家機構,并為50個國家的非政府機構提供資金支持。
以在全球推廣“民主”為使命的美國NGO“自由之家”,專門在吉爾吉斯斯坦開辦。其項目總監麥克?斯通,曾“出色”地打贏了導致這場“軟政變”的宣 傳戰。該組織被稱為“老牌顛覆專家”,在12個國家設有分部,主要任務就是在一些國家推動“人權”和“自由”,最終達到顛覆政權的目的。英國《衛報》曾指 出:“作為‘顏色革命’主要建筑師之一的‘自由之家’,不過是中情局的門面而已。”如今,該組織不僅活躍在獨聯體和東歐,還在中東、中亞和拉美設有分部。 另一位大名鼎鼎的美國人馬克?帕瑪,被《紐約時報》譽為“西方最活躍的經濟與政治自由化推動者”,作為“自由之家”的副主席,曾在“顏色革命”戰場上不遺 余力。
“金融大鱷”索羅斯這位前東歐移民的猶太人后裔,已成為美國推進非暴力政權更迭的領軍人物之一。索羅斯直言,“開放社會基金會”(1979年索羅斯 在紐約建立的第一個基金會)的使命就是“幫助打開封閉社會”,搜尋可能的“民主萌芽”,然后采用各種手段扶植其發展壯大。如今“開放社會基金會”的分支機 構已遍布東歐、拉美、東南亞、中東等地的50多個國家,雇員超過1000人,每年花費超過3億美元。2006年6月,索羅斯的“開放社會基金會”悄然進入 中國,出現在中國一家民間組織的資金捐贈者名單上,捐資金額約為200萬元人民幣。人們同時發現,曾在獨聯體國家“顏色革命”中發揮重要作用的一些美國非 政府組織,如“索羅斯基金會”、“民主基金會”、“歐亞基金會”等,也開始進入中國。一些境外非政府組織來華人員,廣泛搜羅中國國內問題和社會矛盾,以 “扶貧”、“技術開發”等名義開展工作。[14]
正如美國研究NGO的著名學者萊斯特、M、薩拉蒙所認為的,蘇東地區存在于政黨之外的政治與社會組織在“蘇東劇變”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與美國花 費數千億美元、犧牲數千美軍生命的伊拉克戰爭相比,借助NGO實行非暴力政權更迭,占領議會大廈和取得整個國家,不費一槍一彈的“顏色革命”成本之低,不 能不說是美國人將戰爭思維用在“軟實力”上的一大創新。
三、結語
上述對國際NGO在對外傳播中的滲透特征的考察,給我們的啟示如下:
第一,如前所述,對國家(或政府)對外傳播主體的認識,政府與非政府組織同樣重要。西方非政府組織(NGO)或配合政府的行為,為政府拉高聲勢;或補充、代替政府去完成政府不便出面或難以完成的使命。
第二,如何借助國際NGO力量,要認識國際NGO的兩個兩面性。第一個兩面性是建設性與破壞性。即國際NGO力量對一個國家的政府可以有不同的兩種 功能:一是NGO力量與國家權力互補,在政府管不過來或難以發揮作用時,它作為積極的建設性力量,對國家與社會事務起促進作用。另一種是作為破壞性社會力 量,成為造成國家與社會動亂的公害(即作為敵對的社會勢力顛覆國家政權,作為社會邪惡勢力為非作歹,擾亂社會安全)。第二個兩面性是經濟利益與意識形態。 某些國際NGO除了意識形態,還有其利益性和集團性。這種特點決定了其種種行為,有較為強烈的目的性,甚至代表著某些政治集團和利益集團的偏好。
因此,政府對外傳播中,如何借助國際NGO力量,是中國急需補修的一門課程,與國際NGO交往,不能單憑感情,而要以務實的眼光,既要看到其中的意 識形態方面的價值追求,又要看到其中的利益紐帶關系。在全球化時代,中國追求的目標應是,將國際NGO對華的積極影響發揮到最大,將其負面影響控制到最 小。
注釋:
[1]數據參見穆紫:《西方勢力借非政府組織滲透中國》,星島環球網www.stnn.cc,2008年6月5日,來源:香港《紫荊雜志》
[2]參見袁正清:《2007年: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之《國際非政府組織:概念、分類與發展》,中國網2007年4月2日
[3]參見袁正清:《國際非政府組織的發展趨勢和特點》,中國網2007年4月2日
[4]參見袁正清:《國際非政府組織的主要活動領域與方式》,中國網2007年4月2日
[5]AlexandraSilver,SoftPower:Democracy–PromotionandU.S.NGO’s:WorkingPaperofCouncilonForeignRelations,March17,2006,http://www.cfr.org/publication/10164/soft_power.html#1.(轉引自方長平《中美軟實力比較及其對中國的啟示》,《世界經濟與政治》2007年第7期)
[6]袁正清:《國際非政府組織的發展趨勢和特點》,中國網2007年4月2日
[7]參見《“顏色革命”主謀干將大揭底》,[大公網訊]2008年3月26日
[8]參見施君玉:《美對外滲透越來越不得人心》,《大公報》2006年9月2日
[9]參見《“顏色革命”主謀干將大揭底》,[大公網訊]2008年3月26日
[10]說明:該組織1982年成立于美國,在歐洲和亞洲都有分支機構,著重關注東歐、俄羅斯、中東和中亞地區的傳媒發展。據該機構網頁,其主要從美國政府若干機構、荷蘭政府、歐洲委員會,以及一些美國大公司和基金會獲得資助,在2001年就有1700萬美元的預算。
[11]參見趙月枝:《帝國時代的世界傳播:國家、資本和非政府組織力量的重新布局?》http://www.studa.net/xinwen/060803/11503780-2.html,2006年8月3日
[12]說明:其中一家擁有23億股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股權的柏克夏海瑟威公司老板就是中國人熟悉的股神巴菲特。
[13]說明:該研究所成立于1983年,總部設在華盛頓,宗旨是在全世界推進“民主”、“自由”、“自治”與“法治”。
[14]參見《“顏色革命”主謀干將大揭底》,[大公網訊]2008年3月26日
西方勢力借NGO向中國滲透
http://world.people.com.cn/GB/14549/7345589.html
香港中文月刊《紫荊》發表文章說,一些非政府組織(NGO)曾經在西方推動蘇東劇變和“顏色革命”中扮演了急先鋒作用。但隨著“顏色革命”的偃旗息鼓和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快速崛起,西方開始把主要矛頭瞄準中國,西方利用NGO對發展中國家和前蘇東地區滲透擴張的手段做法也必然會應用到中國,而且可能還有過之而無不及。
文章摘錄如下:
近年來,隨著全球公民社會運動的興起,非政府組織(NGO)發展迅猛,目前全世界各類NGO保守估計有幾百萬個。僅美國一國的NGO已經達到160萬個之多。NGO日益成為繼主權國家和政府間國際組織之后崛起的又一重要的國際行為主體,在各國國內則被看作是獨立于政府和企業之外的“第三部門”。
NGO近年來發展速度驚人。世界上幾乎每天都有新的NGO在涌現。目前世界上各類NGO達數百萬之多,其中國際性NGO超過35萬個,國際上確認的國際組織90%以上都是NGO。
國際NGO發展還存在嚴重的不均衡狀態。截至2005年的統計,目前世界上享有聯合國經社理事會咨商地位的2719個NGO,發達國家占70%,而發展中國家僅占30%;與聯合國新聞部保持著“正式”關系的近2,000個NGO中,發展中國家僅占16%。在大多數聯合國會議上,至少80%以上的NGO與會者來自發達國家,窮國的聲音很難被國際社會聽到,發展中國家的利益不能得到平衡和充分的保護。
發達國家的NGO不僅數量多,而且機構完備、規模龐大、資金雄厚、人才濟濟,熟悉國際問題和國際組織的工作程序,能夠對國際組織的議程設置乃至最終決策施加很大影響,更擅長在外圍制造輿論、推波助瀾,詆毀發展中國家的政治形象。無論是聯合國系統舉行的NGO活動,還是國際性NGO倡議活動;無論是全球反全球化運動,還是反戰反美示威游行,西方發達國家的NGO都起著決定性主導作用。
發展中國家的NGO近年來雖然發展較快,但規模小、力量弱,缺乏人才和經驗,對國際活動的參與和政治影響非常有限,并且有的NGO由于依賴于西方NGO的資助,最終難免受制于人,或者經常會出現“跟風”的現象,做出損害本國利益的事情。如印度,上世紀九十年代,NGO經費的90%來自國外,外國政府和NGO對印度NGO的援助相當于外國對印度官方援助的25%。
NGO不僅存在嚴重的不對稱,而且還難以做到真正的出污泥而不染,很多NGO都帶有較強的意識形態偏見和一定的政治利益,有的被西方利用來作為對外滲透、干預和擴張的工具。美國研究NGO的著名學者萊斯特.M.薩拉蒙認為,蘇東地區存在于政黨之外的政治與社會組織在1989年蘇東劇變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美國總統布什也曾自豪地宣稱,美國的NGO“在自己存在的20年時間,曾經在100多個國家的民主變革斗爭前沿努力工作”。
西方利用NGO對發展中國家進行滲透主要有三大手段。
一是資助發展中國家的各種NGO來施加政治影響。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開始,西方國家越來越多地開始把援助對象從受援國政府轉向各種NGO或個人,目的是通過援助直接與受援國百姓打交道,了解情況,收集信息,施加政治影響。如1993年到2003年,美國用于幫助獨聯體國家進行“民主改革”的90億美元專項援助,其中3/4都提供給這些國家的企業、NGO和獨立媒體。
近來,西方為了消除被援助國政府和民眾對西方政府直接援助的反感,開始越來越通過首先資助西方NGO,然后通過西方NGO來資助發展中國家NGO的間接渠道來實現西方對外滲透的目的。如在烏克蘭“橙色革命”中,美國國務院公開承認,為推動“民主進程”,曾花費6500萬美元資助美國的卡內基基金會、國際發展基金會和美共和黨所屬的國際共和協會以及民主黨下屬的國際民主協會、人權論壇等NGO,通過這些NGO參與了幕后決策和宣傳。
二是利用NGO的渠道進行軟性滲透。西方通過各種NGO,以所謂人道主義救援、維護人權、推廣民主進程、維護宗教自由和新聞自由等各種借口,對發展中國家進行滲透,培植親西方的代理人。
1999年由美國政府資助的民主黨對外活動組織就曾邀請20多個塞爾維亞反對派領導人齊聚布達佩斯,商討團結一致推翻米洛舍維奇的方案。隨后美國和北約發動了科索沃戰爭,推翻了米洛舍維奇的統治。
2002年8月,美在發動伊拉克戰爭前,啟動了一項總額達660萬美元的非政府資助計劃,名義上是資助各種非政府在伊拉克境內及其周邊地區進行人道主義救援,實際上是利用NGO幫助美國收集情報,為其打擊伊拉克提供便利。
2004年,NGO成為西方在前蘇東地區推動顏色革命的急先鋒。2005年5月18日,美國總統布什發表講話時公開承認,美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推行“民主”,進行政權更迭,幾乎耗費了3000億美元資金,而在其它許多國家推動“顏色革命”,僅僅花費了不足46億美元資金。
最近發生的拉薩事件背后也有西方資助的“藏青會”等各種反華NGO進行滲透的影子。根據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自身公布的數據,2002年至2006年,該基金會向達賴集團提供了135.77萬美元的專項資金援助。今年2月27日(即拉薩騷亂發生前半個月),達賴集團的“九.十.三運動”還向該基金會緊急申請資金,以作為“活動家們應對危險時期的資金”。而該基金會是由美國國會通過法案成立的,資金幾乎全部來源于政府撥款。
三是通過NGO控制或影響輿論,為西方實現滲透和演變服務。西方國家一方面支持本國的電臺、報刊和電視臺走向國際,在發展中國家“落地生根”,樹立“公信力”;另一方面,以新聞自由等為幌子不斷壓發展中國家開放媒體管制,資助發展中國家創立所謂的“獨立”電臺、電視臺和報刊。
在西方資助下,中東歐和中亞多數國家都允許西方的電臺和電視臺落地或成立各種“獨立”媒體,在格魯吉亞和烏克蘭“顏色革命”中,許多選民投票支持親西方人士上臺,正是西方媒體在當地發揮影響力的結果。
西方也一直不斷向中國施壓,要求效仿前蘇東地區開放媒體管制,但一直沒有得逞。因此,在此次拉薩事件中,中國媒體沒有受西方媒體誤導,堅持客觀公正報道整個事件過程。西方的CNN、BBC和ZDF等主流媒體只好赤膊上陣,親自充當西方對華演變的急先鋒。
一些NGO曾經在西方推動蘇東劇變和“顏色革命”中扮演了急先鋒作用。但隨著“顏色革命”的偃旗息鼓和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快速崛起,西方開始把主要矛頭瞄準中國,西方利用NGO對發展中國家和前蘇東地區滲透擴張的手段做法也必然會應用到中國,而且可能還有過之而無不及。這種趨勢已經在拉薩事件中露出了苗頭。(作者 穆紫)
田嘉力:毛澤東時代貧困者為什么上得起大學?
http://www.ycwb.com/gb/content/2005-12/12/content_1036468.htm
社會總是在發展和進步。認為今不如昔注定是荒謬的。但有一個問題我很難找到合理的解釋:毛澤東時代雖然經濟不發達,物質匱乏,人們的生活普遍貧困,卻沒有發生過因貧困而上不起大學的事。而現在,“貧困大學生”卻司空見慣,貧困家庭因子女考上大學、家長為學費發愁從而自殺的事情也時有所聞。這是文明社會的悲哀,也是文明社會的恥辱。
曾經給朱總理上書說“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李昌平,對農村教育有痛切的體會。他在一次訪談中說,現在農村教育的情況有的比二十多年前還不如。他自己是70年代后期上的中學,當時貧下中農管學校,收費很低,一年只收兩塊錢,雖然農民很窮,還能供孩子念書。當時老師的責任心強,和學生的關系也比現在好。現在農村孩子上小學一年500元,上初中 1000元,上高中上大學好幾千,好幾萬。其實,又豈止農民的孩子讀不起書,如今連城里的父母也開始為孩子的學費操心發愁了。
1965年我上高中,班上有三個同學是領取助學金的。在他們看來,上學是“解困”的有效辦法。上學可以申請助學金,每個月他們都要從有限的助學金里擠出兩三元錢寄回家里,以補貼家用。他們從來沒有為考上大學交不起學費而發愁過。因為那時候大學基本不收費,而且,像他們那樣家庭貧困的同學,上大學也是可以申請助學金的。據說,在現任的各級領導干部中,就有些是當年依靠助學金讀完了大學,從而逐步走上領導崗位的。
說到貧困生上不起大學,很多人都歸因于“教育投入不足”。我們很難理解為什么會發生“教育投入不足”?我們的經濟已經相當的發展,我國經濟實力比起毛澤東時代,不知要增強多少倍。想當年,國家那么窮,國家經濟基礎那么薄弱,共和國成立之初,一窮二白,百業待興,卻從新中國建立起,就定下了讓所有考得上大學的學生讀得起大學的政策。這應該與經濟實力無關,只與政策和制度的設計有關。
我們現在也仍然是不富裕的。我國仍然是個發展中國家。在有限的資金,有限的財力,有限的物力情況下,優先發展什么?優先向哪部分人群傾斜?這很值得深思。有人表達了這樣的意思:我們需要資金投入的,差不多總是“投入不足”,比如教育、衛生、國防;而本應該控制和限制的,卻往往有超過需要的過剩投入,比如公款吃喝、公車消費、公費出國培訓,在這些領域里幾乎是應有盡有,像阿里巴巴的芝麻開門一樣,要多少有多少。其實,只要把公款吃喝、公車消費之類稍加控制,“教育投入不足”就可以極大的緩解。
至于向什么人傾斜的問題,就更為沉重。毛澤東時代要打造的就是讓貧窮者都讀得起書,都上得起大學的那樣一種“天堂”。所以,盡管當時國家很窮,卻沒有人因貧困而上不起大學。現在經濟繁榮了,國家實力增強了,卻年年都有上不起大學、上不起中學和小學的貧困生。所以,這應該與國家實力無關,與經濟發展水平無關。解決“教育投入不足”的問題,屬于“非不能也,實不為也。”只要想做,就應該做得到。
教育部在11月10日發布的《中國全民教育國家報告》中提出:爭取到2007年全國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家庭經濟困難學生都能享受到免費教科書和住宿生活補助,力爭到2010年在全國農村地區全部實行免費義務教育,2015年在全國普遍實行免費義務教育。我不知道目標為什么要定得那么遙遠。毛澤東時代也許有些不盡人意的地方,但至少,在教育投入方面,就比現在慷慨。所以,有不少人還是很懷念毛澤東時代。
「 支持烏有之鄉!」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