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7·5事件過去整整一年了,這是新中國六十年來民族關系最深的創傷。我從鳳凰衛視的一檔節目中感到了些許事件的根苗,寫下此文。)
鳳凰衛視去年曾經播放了一個系列節目,介紹上世紀60年代初期支援新疆的10萬上海人在80年后的命運。從內容看,節目本意是想“傷痕”一下當年的“支青”政策,時間上看應該是新疆7·5事件前做好的節目,節目中被采訪的“支青”們提到28年前的返回上海之路,不勝唏噓感慨,對返程前后的細節,恍如昨日,歷歷在目,心情激動,卻能娓娓道來。
從節目介紹中,上海支援新疆的青年是在文革前進疆的,1962、63、64年比較多,到了文革時已經基本結束了。這批人都分配在了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主要分布在南疆,隸屬于農一師和農二師,和文革中的下鄉知青是不一樣的。所以被官方稱為“支青”而不是“知青”。
鳳凰制作的節目省略了支青們來新疆的原因,在新疆奮斗的整個過程,只是從1980年支青們聚眾罷工要求返滬講起,就好像廚師在烹飪一條魚,去了魚頭和中段不要,只留下魚尾給客人吃,并且既不去鱗又不剔刺,一刀切下血淋淋地就端了上來,讓客人從魚尾中去想象整條魚的味道。
節目的引子,是從上海某公園一群60多歲身著維族服裝翩翩起舞的原漢族支青們開始的,他們中有的是“單頂”返滬的支青,有的是“雙頂”返滬的支青,有的是自謀生路返滬的支青,有的是退休后回滬安享晚年的支青,當他們跳起維族舞蹈的時候,每個人都是那樣的意氣風發,神采飛揚,臉上帶著真摯的笑容,歲月帶給他們的滄桑和苦難仿佛化作了喜悅,每個人都被激情感染,每個人都有變成了青年。(我不知道7·5事件后他們還會不會繼續他們的舞會,會不會戴上維族式的大胡子,穿上維族的花衣裳。上海方面的網友,可否留意一下?)
老知青們的維族舞確實跳得不錯,應該是受到了維族的真傳才能跳得如此好。當年的維族老百姓是比較窮的,沒有什么東西能拿出來招待遠來的支青們,只能通過他們的歌舞來表達他們的熱情,本民族的歌舞是他們所能拿出來不多的東西之一,代表著他們誠的心意。
節目中很多知青描述了他們離開新疆市的心理歷程,可以用“爭先恐后”“破釜沉舟”來形容一點也不為過。根本不去想回到上海有沒有工作,有沒有住房這些問題,子女上不上學……總之,只要呼吸著黃浦江畔潮濕的空氣,所有的困難就都不在話下——再大的生活困難難道還比得了在新疆遇到的困難大嗎?
整個節目,貫穿著上海支青們返城的艱難,返城后生活的坎坷,返城后精神的壓抑,子女的被邊緣……我看著節目,看著看著,卻總覺得少了些什么,被漏掉了什么,但是說不上來,直到介紹到一位返滬的支青教師。這是一位在臨走時已經在新疆的公辦學校里當了老師的支青,他在回憶他們他決定返滬的時候,動情地講起當地的學生把自家里最好的東西拿來送給他,學生們舍不得老師走,但是學生的家長告訴學生,不要攔著老師,因為老師是回到上海,回到生活條件更好的地方去過更好的生活,不能阻礙老師們去過好日子,不能耽誤了老師的美好前程……
那么當地人是誰呢?是南疆的各民族少數民族同胞,而南疆就是維吾爾族的主要聚居地。
到此,我明白節目漏掉了什么了,這就是在知青們回城過程中,當地群眾的感受。在我看到播出的這幾集節目中,我沒有看到一個當地的維族人談論這個事情,不知道是鳳凰的采編人員有意還是無意,反正當地人還是被忽視了。(當年中國知青們的返城大潮過去這么多年了,我極少看見以當地群眾的視角觀察這一現象的;以邊疆少數民族的視角觀察、感受知青運動的,我想應該也有,但我真是一個也沒看過聽說過,以后會有人來補這一課嗎?)
支青們走了,給我什么樣的感覺呢?從支青們的敘述中,感覺就是這些“支青”走了,把根都拔了走了,他們丟棄了自己的房子,賣了自己的家具,賣了自己的炊具,賣了自己的鋪蓋,能賣得都賣了,帶走了自己的孩子,不留絲毫掛念地走了,再也不想回來了!
那么換成當地的人,看法就是:這些“漢族人”走了,把根都拔了走了,他們丟棄了自己的房子,賣了自己的家具,賣了自己的炊具,賣了自己的鋪蓋,能賣得都賣了,帶走了自己的孩子,不留絲毫掛念地走了,再也不想著他們了,漢族人們在這里十幾年,當年誓死扎根邊疆的口號,消失在天山吹來的寒風中了——“漢族人”從“心”里拋棄了他們了。
從此,對漢族不再相信,不再貼心,有了隔閡,使三股勢力有了可乘之機。人的世界觀、意識形態,不會是空白的,你不去占領,人家就占領。就這么簡單。
我從片中明顯感到新疆兵團和自治區的領導們雖然不能預知后來的悲劇,但是清楚支青大規模回城對新疆的建設將產生嚴重的負面沖擊,因此千方百計想要留住他們。但是回城的潮流在當時全國有著深刻的政治背景,如同山洪暴發,泥石具下,根本不是新疆一個地區能夠阻攔得了,最后不得不被動地接受了事實。
那么當時全國是個什么形勢呢?就是全國知青已經基本上快返城完畢了,就剩新疆兵團這一口了。有人說新疆兵團的“支青”不同于其他地區插隊的“知青”,是具有邊防屯墾性質的,所以比其他地區慢了,這話有道理,但恰恰是同樣具有類似屯墾性質的云南生產建設兵團的知青們,掀起了返城回家的序幕。
云南農墾知青回城的過程這里不詳細說了,各種報道、分析文章太多了,大家可以自己找找看。其中有個細節想說一下,云南知青曾經組織了一個請愿團到了北京請愿,并要求國家要派出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以上領導接見面談,這個條件其實是按照總設計師的尺寸量身訂制的,但是,總設計師沒見,而是委托老屯墾將軍王震來接見,王震時任副總理,政治局委員,也符合代表們的條件。1979年1月10日上午和晚上雙方見了兩次面。據說老將軍第一次見面時嚴厲批評了“請愿團”丟掉了軍墾的光榮傳統,說現在全國都在抓綱治國,你們卻鬧事,對不起國家等等。晚上再次見面時,則溫和了許多,先請大家看電影《巴頓將軍》,再表示國家知道知青們的困難,理解他們的心情,將會盡力解決,要求知青們繼續扎根邊疆,并特別提到“鄧副主席說了,不久就要大規模投入資金,資金不夠,外匯也可以動用嘛!”。《巴頓將軍》是當時剛剛翻譯好的內參片,準備送到南疆前線去給即將投入戰斗的部隊看。小說《高山縣的花環》里面就曾描寫過戰前軍官們集體觀看這部電影。(題外話:讓部隊戰前看《巴頓將軍》最合適了,難道能看《英雄兒女》、《打擊侵略者》之類的電影嗎?)
老將軍為什么要給請愿團看這部電影呢?難道就是簡單地娛樂一下而已嗎?我是不這么認為的,將軍用意是很深的。《巴頓將軍》又是一個什么電影呢?影片主要描寫巴頓在二戰時的北非和歐洲戰場中帶兵作戰的事跡。影片中的美國將軍巴頓忠誠、驍勇、機智、堅強、果斷,并且不乏幽默。影片中有一個情節,是根據真實歷史拍攝的,某次戰役后,巴頓裝了一兜子的軍功章跑到野戰醫院,向那些戰斗中負傷的官兵大唱贊歌,大發獎章。不經意間,發現了一個身上沒有任何傷痕的士兵,瑟縮在角落里哭泣,一問才知道是個戰爭恐懼癥患者,當即大怒,認為這是一個逃兵,根本不配和其他受傷的將士們在一起。暴怒之下,給了兩皮帶,打飛了那人的鋼盔(美國報紙上說是給了一個耳光)。
那天晚上王將軍可能想通過面談和看電影傳遞給知青們至少3個信息:
第一:他是真誠對待這些知青們所面臨的問題的并愿意解決之;
第二:云南邊疆將發生戰爭;
第三:希望知青們繼續在邊疆扎根,建設邊疆臨陣脫逃或者嚇破膽,都是可恥的。影片中巴頓對待哪個美軍士兵的情節,大概是老將軍特別想傳達給知青們的,
但是知青們哪有心情看電影啊!除了返城,什么都不在心里了。一聽不讓返城,幾句話就和老將軍又談崩了,二者之間心理預期差距太大,會談不歡而散。知青們垂頭喪氣連夜回云南去了,失望和沮喪的氣氛籠罩著他們。令這些上訪的知青想不到的是,在他們還一籌莫展不知如何是好地在返回云南的列車上的時候,形勢突然逆轉——國家讓步了。
怒氣沖沖的老將軍應該是不想讓步的,但是對越作戰迫在眉睫,總不能前方作戰后方起火,況且這個仗誰也不知道打多久,國際形勢極其復雜,后方必須穩定,中國必須穩定。在多重因素疊加下,老將軍無可奈何了。
1979年1月15日,時任云南省委書記的安平生發表《15條講話》,其中一條就是“知青不愿留下的,都可以回去”。知情的回城之門終于打開,如決堤的洪水,西雙版納各農場知青無不爭先恐后回城。有知青回憶,“短短幾天,整個農場走空了,連隊靜得可怕!大家丟下武器,拋棄農具,有人還把農具架起來燒掉。很多人搭乘為對越自衛反擊戰運送物資的返程軍車回昆明,由于擁擠過度,發生了好幾起翻車事故……”與后來新疆支青回城的情景,如出一轍。
云南的知青回城了,其他地區的知青也自然而然地回城了,新疆地區是最后一個。還有一個詭異的相似,就是云南知青返城恰逢對越作戰,新疆支青返滬,恰逢蘇軍入侵阿富汗!太巧了吧?太耐人回味吧……
1980年代初,在國務院知青辦起草的知青工作回顧與總結中認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本來是為解決就業問題,但在“文革”10年中,當成政治運動去搞,指導思想偏了,工作上有嚴重失誤,造成勞民傷財,人民不滿……。記得當年有一句喊得最響的口號叫做“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那么我們就來看一看“實踐”是怎么檢驗的吧:
西雙版納,瀾滄江邊曾經的明珠,在知青離開后不久就逐漸變成了中國最大的毒品和武器走私通道,具體實施販運的人員,主要為當地老百姓;新疆,則分裂勢力惡性膨脹,破壞民族團結、傷害民族感情的事情屢屢出現,日甚一日,直至“7·5”事件發生!
“實踐”的結果,恰恰證明知青辦的結論錯了;“真理”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本來就是政治問題(就業問題是不是政治問題先不論),但是后來當作純粹就業問題去解決,指導思想南轅北轍,工作能不產生嚴重失誤嗎?政治上幼稚的代價,不知幾代人才能夠彌補。
無論新疆的解放與建設,還是東北與西南的農墾事業,眾所周知與王震將軍有著特殊而又密切的聯系。30年前,一只瀾滄江邊的蝴蝶,就在他的身邊翻動了幾下翅膀,隨后30年,竟然在西雙版納卷起了彌久不散的黑風毒風,更在天山腳下掀起了血雨腥風!將軍九泉之下,情何以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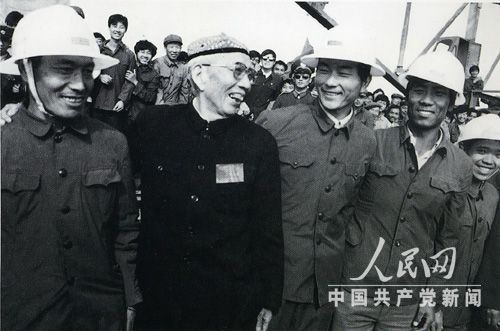
王震視察北疆鐵路,和鐵道部第15工程局鋪軌工人在一起。
我在這里沒有任何指責當年返城知青們的意思,他們不可能料想到后來的事情,特別是30年后的事情。哪怕是王震這樣久經戰陣飽經風霜的領導人,也不過臨終前發出“毛主席比我們早看五十年”的感嘆,何況他也不是決策人……往事不可追,但愿后人不會如此評價我們:后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后人復哀后人也!
相關文章
「 支持烏有之鄉!」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