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一代文豪的隕落
“1936年10月19日凌晨5時25分,一顆巨星隕落在東海之濱的上海:中國幾百年來最優秀也最痛苦的靈魂魯迅與世長辭。”
當時陪在魯迅身邊的只有夫人許廣平、二弟周建人和一個陪護婦。
馮雪峰在床上接到周建人的電話后,“立即打電話告訴了宋慶齡,隨之匆匆地趕到大陸新村,魯迅這位偉大的革命文學家已經溘然去世半個小時了。”
宋慶齡是繼馮雪峰之后趕到大陸新村向魯迅遺體致哀的第二人。據宋慶齡后來的回憶文章《追記魯迅先生》記述,馮雪峰當時對她說,他不知應當如何料理魯迅的喪事,如果由他公開出面治喪,肯定會遭到國民黨反動派的殺害。宋慶齡當即表示她愿意承擔起這件事情。
上午九點,宋慶齡打電話給上海各界救國會總干事胡子嬰,告訴她“魯迅的喪事由救國會來辦。”救國會的“靈魂人物”胡愈之當即將此消息告知了“救國會七君子”。
美共黨員、《中國呼聲》主編格蘭尼奇通知夏衍,要他“把消息告訴所有的中國革命作家。”
消息一傳十、十傳百,加上報紙電訊的傳播,一代文豪逝世的噩耗便已天下廣知。
當時的周曄只有十歲,她的堂弟周海嬰更年幼,僅七歲,尚懵懂不曉事,穿著孝服“在萬國殯儀館禮堂里的人群中快樂的穿來穿去”。周曄雖不知魯迅就是伯父、伯父就是魯迅,但當她想到以后“永遠見不到伯父的面了,聽不到他的聲音了,也得不到他的愛撫了”,以至心里難過感傷,“淚珠就一滴一滴地掉下來。”
魯迅逝世九周年之際,芳華正茂的周曄寫了紀念文章《我的伯父魯迅先生》,文中這樣寫道:“……伯父去世了,他的遺體躺在萬國殯儀館的大禮堂里,許多人都來追悼他,向他致敬,有的甚至失聲痛哭。數不清的挽聯掛滿了墻壁,大大小小的花圈堆滿了整間屋子。送挽聯、花圈的有工人,有學生,各色各樣的人都有。那時候我有點驚異了,為什么伯父得到這么多人的愛戴?”
魯迅喪儀葬禮的規格之高、規模之大,不僅令年幼的周曄驚異,也令世人驚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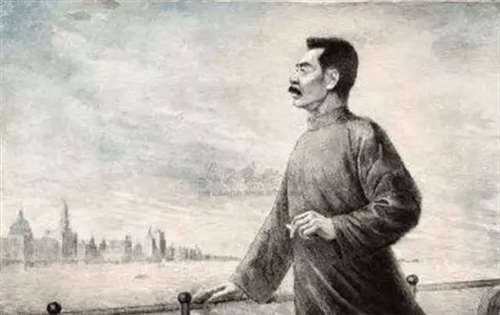
01
“豪華”的喪儀葬禮
魯迅逝世的噩耗傳到陜北,中共中央要求國民政府“為魯迅先生舉行國葬”,并“決定在全蘇區內:(一)下半旗志哀并在各地方和紅軍部隊中舉行追悼大會……”
中共中央又密電馮雪峰,同意“由馮雪峰負責主持魯迅葬儀,宋慶齡以公開的‘國母’身份料理喪事”的治喪方案。
由此,在總共有三個版本的治喪委員會名單中,其中一份就有毛澤東的名字,這份名單雖然只有上海日文報紙《上海日日新聞》敢于披露登載,但這個新聞“還是在上海革命人民中間迅速傳播開來,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
“通過他的喪事來發動群眾,搞成一個群眾性的運動”,這個目標的最終達成,除毛澤東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外,“國母”宋慶齡的巨大能量絕對至關重要。
在她的影響下,復旦大學創始人馬相伯、民國元老蔡元培師生二人聯袂登場,上海各界救國會的沈鈞儒、鄒韜奮、章乃器、李公樸、王造時,外國友人內山完造、史沫特萊都成了治喪委員會成員。
她還動員了財政部部長孔祥熙及其夫人宋靄齡來全程參加魯迅的葬禮活動,又以治喪委員會的名義要求租界工部局維持秩序。
上海市市長吳鐵城受蔣介石的委托,也來萬國殯儀館禮堂致哀。
這些都為參加“隆重莊嚴而又富有濃重政治色彩”的魯迅喪儀葬禮的人提供了安全保障,整個喪儀葬禮活動從開始到結束,沒有一人被捕。
中共上海地下黨組織又精細籌劃,周密安排,“通過工會、共青團、救國會這些群眾性團體去發動廣大群眾參加追悼會”,為防“出殯路上有一些反動分子出來搗亂,”又“通過‘文委’所屬各聯和有關人民團體,連夜組織了一支以‘文委’所屬各聯為主的送殯隊伍,包括了學生、店員、女工、家庭婦女,這支隊伍粗粗估計大約有五六千人。”
絡繹不絕的人群“從早到晚,不斷地來悼念,與遺體告別。”吊唁簽名簿冊上簽名的“有個人9470人、團體56個,未簽名的不計其數。”“群眾自動來的不少,由組織發動的也不少。”川流不息的吊唁人群使“黑紗需用量太大,幾個女子趕制黑紗圈,仍然供不應求。”
吊唁人群中失聲痛哭的有本應駐守機關卻“擅離崗位”的鄭育之,整日長跪不起的有“魯迅家中留飯最多”的蕭軍,守夜守靈的有胡風、蕭軍、周文等……唁客敬送的挽聯、花圈、鮮花多得數不清,其中最彌足珍貴的是那些“數不清的挽聯”。茲摘錄部分,一是可以幫助我們初步熟悉魯迅的朋友圈,二是可加深對“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魯迅的認知。
著述最謹嚴,非徒中國小說史;
遺言太沉痛,莫做空頭文學家!(蔡元培)
方懸四月,疊墜雙星,東亞西歐同隕淚;
欽誦二心,憾無一面,南天北地遍招魂。(郭沫若)
痛不哭,苦不哭,屈辱不哭,今年成何年,四個月前流過兩行淚痕,又誰料這番重為先生濕;
言可傳,行可傳,牙眼可傳,斯老真大老,三十年來打出一條血路,待吩咐此責端賴后世肩。(唐弢)
郭沫若、唐弢的挽聯都把魯迅的逝世與四個月前的高爾基逝世聯系了起來。
死者趕快收斂埋掉拉倒,生的主張寬容那才糊涂。(王造時)
踏《莽原》,刈《野草》,《熱風》《奔流》,一生《吶喊》;
痛《毀滅》,嘆《而已》,《十月》《噩耗》,萬眾《彷徨》。(孫伏園)
王造時把魯迅的遺言和文章內容合為一聯,孫伏園則用魯迅所著書名及所主編之刊名綴為一聯。
一代高文樹新幟,千秋孤痛托遺言。(孔祥熙)
譯著尚未成書,驚聞隕星,中國何人領吶喊?
先生已經作古, 痛憶舊雨,文壇從此感彷徨。(姚克、埃德加·斯諾)
魯迅在中山大學教學期間,孔祥熙慕魯迅之名,曾邀魯迅去其家中做過一次客。姚克是受教于魯迅的學生,也是斯諾與魯迅的聯系人和翻譯。
平生荊棘向前進,未死精神待后人。(暨南大學校長鄭洪年)
杜少陵愴懷饑溺,李長吉嘔出心肝。(上海商會會長、嵊縣人王曉籟)
在事實上闡揚真理,的確是諷世砭俗的大文豪;
從文學上領導革命,不愧為臥薪嘗膽的老同鄉。
(紹興七縣旅滬同鄉會委員長)
敵乎友乎?余惟自問;知我罪我,公已無言。(徐懋庸)
一生不曾屈服,臨死還要斗爭。(章乃器)
文苑苦蕭條,一卒彷徨獨荷戟;
高丘今寂寞,芳荃零落痛余香。(曹聚仁)
這世界如何得了,請大家要遵從你說的話語,徹底去干!
縱軀體有時安息,愿先生永留在我們的心頭,片瞬勿離。(沈鈞儒)
沈鈞儒書敬挽聯后,又大書“民族魂”三字做成大旗,為魯迅覆棺蓋槨。

出殯時,浩浩蕩蕩的隊伍行進在租界華界的大街上,途中不斷有人群加入到隊伍中,“將近虹橋路時……隊伍足足有二里多長”,“整整兩個多小時,一萬多人組成的送葬隊伍,就這樣唱著挽歌,呼著口號,行進在白色恐怖下的大上海。一次悼念,儼然成為一個自發的、悲壯的群眾愛國示威。”
“由于事前考慮得比較周到,所以魯迅出殯在幾百萬上海人中成了一次政治性的大示威,對革命人民來說,這也成了一次最有力的革命大檢閱。”
各地的悼念活動紛紛舉行,郭沫若、蕭紅在日本,臺靜農在山東大學,錢玄同、沈尹默、劉半農在北大,天津、廈門、廣州等地青年也紛紛集會悼念魯迅……
“茅盾在桐鄉因痔瘡發作,疼痛難忍,無法行走,只得請夫人孔德沚代表他前往。”
朱安在北平照料著魯迅的八旬老母,不能南下參加喪禮,她“將一間書房布置成靈堂,擺上魯迅生前愛吃的幾樣小菜,為魯迅守靈。”
聶紺弩受馮雪峰指派,將從南京出逃到上海的丁玲護送到西安。丁玲在德共黨員馮海伯的診所里聞知噩耗后,即以“耀高丘”的署名給許廣平發出了一封唁函:
“我是今天下午才得到這個最壞的消息的!無限的難過洶涌在我心頭。尤其是一想到幾十萬的青年驟然失去了最受崇敬的導師,覺得非常傷心。我兩次到上海,均萬分想同他見一次,但為了環境的不許可,只能讓我懸想他的病軀,和他扶病力作的不屈精神!現在卻傳來如此的噩耗,我簡單不能述說我的無救的缺憾了!……這哀慟真是屬于我們大眾的,我們只有拼命努力來紀念著這世界上一顆隕落了的巨星,是中國最光榮的一顆巨星!”
丁玲的唁函是總共收到的54件唁電、78件唁函中的一份。
丁玲之所以署名“耀高丘”,源自于魯迅的舊詩《悼丁君》,當時魯迅聞聽丁玲被殺害的謠傳后,寫下了這首詩:
如磐夜氣壓重樓 ,
翦柳春風導九秋。
瑤瑟凝塵清怨絕,
可憐無女耀高丘。
樓適夷在獄中從一個年輕看守遞進來的一張剪報上看到了魯迅逝世的消息,他第一個想法就是要告訴難友們。他在牢房里的黑石板上寫了“魯迅先生逝世”六個大字,從鐵窗中舉了出去,這是難友們平時交流信息的方法。很快,大家用相同的方法,把這個消息傳遍了整個監牢。
第二天放風的時候,各人臂上都已佩好一塊從破衣服上撕下的黑布,當作哀悼的黑紗,這是他們唯一能做到的對先生表示哀思的儀式。
……

02
關鍵人物之一:許壽裳
魯迅為何能在整個文化知識界、在數十萬文化青年中、在紅色蘇維埃政權里擁有如此強大的感召力?
這是魯迅奮斗一生、積累一生的結果。
魯迅的偉大是那個特殊的大時代造就的,他所處的時代貫穿著推翻腐朽帝制、新文化運動興起、反帝反封建救亡圖存、反壓迫反奴役追求光明等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大事件,魯迅生逢其時又參與其中。
他從怯弱走向不屈,從“幾近死灰的心”而成為“急先鋒”和“主將”。
而成就魯迅走向偉大的,是他朋友圈中三個關鍵的人物,這三個關鍵人物分別是結識于東京的許壽裳、約稿于北京的錢玄同和暗中相助于上海的史沫特萊。
1902年,21歲的魯迅作為官費留學生與陳衡恪、陳寅恪兄弟同船前往日本。進入弘文學院學日語時,八人同住一間宿舍,魯迅與年僅12歲的陳寅恪床鋪相連,“腳抵著腳度過了兩年。”
他們成為魯迅的朋友,但絕不是最鐵的朋友。魯迅在東京結識并成為“相知35年”的鐵桿是許壽裳。
許壽裳對魯迅生前身后的真摯友情和鼎力相助,無人能出其右,無人堪與比肩。
許壽裳是紹興柯橋人,在杭州求是學院上學時,與陳儀是同班同學,并在此結識了以后半生追隨的蔡元培。
許壽裳來到反清大本營的東京后,同魯迅、周作人、錢玄同等人拜章太炎為師,又帶魯迅加入了東京的浙學會(后來發展為以暗殺清廷官員而著稱的光復會),認識了陶成章、徐錫麟、陳天華、秋瑾等革命黨人。
由于沙俄違約,拒不從中國東北撤軍,更提出七項無理要求,激起了東京愛國青年學生的憤怒,500多名留學生組成了“拒俄義勇隊”,日夜操練,又馳書國內,要求清政府采取強硬手段拒絕沙俄無理要求,并表示如若開戰,“拒俄義勇隊”愿全體回國,開赴東北,為國死戰。
清政府卻嗤之以鼻,并修國書要求日本政府解散“拒俄義勇隊”,陳天華憤而投海。
500多留學生被徹底激怒,馬上把“拒俄義勇隊”改組為“軍國民教育會”,決以革命暴動和暗殺為手段,誓死推翻腐敗無能的清廷政權,200多人組成了暗殺團,分批回國,陶成章回到上海,與蔡元培、章士釗、陳獨秀等人組織上海暗殺團,伺機而動。
原本可以成為勤王抗敵的熱血戰士瞬間轉變為大清國的掘墓人。

魯迅當時也是暗殺團成員之一,但當他要被派回國時,他猶豫了,他提出了一個疑問,“倘若我被抓,被砍了腦袋,我家中的老母由誰贍養?”暗殺團便放棄了魯迅,他與許壽裳繼續留在日本學習。為此秋瑾還特別看不起“怕死”的魯迅。
關于這段往事,魯迅后來曾對許廣平說道:“革命者叫你去做,你只得遵命,不許問的,我卻要問,要估量這事的價值,所以我不能做革命。我看事情太仔細,一仔細,即多慮,不易勇往直前!”
所以魯迅只能成為一個拿筆戰斗的斗士、戰士,而沒有成為一個拿刀槍炸彈去搏殺的猛士、死士。但他筆下紀念的猛士、死士卻又激勵鼓舞著他成為不屈的斗士和戰士,也激勵鼓舞著無數如夏伯陽般戰斗的年輕人。
留日七年多的魯迅回到國內,許壽裳將其安置在杭州“官立兩級師范學堂”教書,一年后魯迅回到故鄉,在“紹興府中學堂”任教。
辛亥革命成功,原光復會上海暗殺團的核心骨干蔡元培,由革命者成為了執政者,就任民國教育總長一職后,他隨即將許壽裳、陳衡恪召至身邊協助工作。
魯迅寫信給許壽裳,要其幫忙尋找新職,以離開令人窒息的故園。經許壽裳向蔡元培舉薦,教育部錄用魯迅為社會教育司第一科科長,月薪高達300元大洋。
袁世凱竊國后,教育部北遷北京,魯迅也隨之到了北京,每日朝九晚五上班,住在紹興會館抄寫古碑。
1917年,蔡元培任職北大校長后,又經許壽裳的推薦,北大聘用教育部公務員魯迅為中文系兼職講師。講課之余,魯迅領受校長的指令,為北大設計了校徽。
工作穩定、收入頗豐的魯迅耗巨資在八道灣購得“足可以開運動會”的巨宅一所,兄弟三人及家眷老母全部搬到這里。
除了沒有愛情,這是魯迅一生中家庭生活最為和諧的時期,也是他光輝生涯剛剛開始的時期。

03
關鍵人物之二:錢玄同
那個時候的北大,集聚了太多聲震寰宇、蜚聲國際的巨匠和大師,新文化運動、五四愛國運動、傳播馬列主義、建立中共早期黨組織,無一不是肇始于北大。
魯迅人生中的第二個關鍵人物出場,使魯迅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主將。
這個人就是《新青年》的輪值編輯錢玄同,在補樹書屋的老槐樹下,留日同學錢玄同的一番話打動了魯迅幾近死灰的心,喚起了魯迅沉睡已久的創作欲望,寫出了不朽名著《狂人日記》刊登在《新青年》上。
從此開始,他與李大釗、陳獨秀惺惺相惜,與胡適關系親密,與大弟周作人和睦相處,與郁達夫同病相憐,與沈尹默、劉半農志趣相投,與《晨報副刊》的主編孫伏園亦師亦友……
《阿Q正傳》在《晨報副刊》的連載,更使魯迅聲名大震。以致北漂的文學青年紛紛慕名前來,最著名的故事就是沈從文、丁玲的寫信求助,魯迅因各種各樣的原因與他們失之交臂,反倒使郁達夫與沈從文留下了一段扶危濟困、一生感恩的文壇佳話。
到女師大任教后,魯迅與教務長林語堂又成為知己好友。也是在女師大,魯迅遇見了廣東女學生、許崇智的堂妹許廣平,并因許廣平而卷入了女師大學潮中。
“三一八慘案”后,林語堂等人成為第一批遭通緝的教員,林語堂逃離北京、南下廈門大學后,聽說魯迅也被列入黑名單之內,遂向學校舉薦后,即函邀魯迅到廈大任教。
魯迅與許廣平相攜南下,抵上海后,魯迅赴廈大,許廣平回廣東,兩人自此鴻雁頻傳,給我們留下了事無巨細的《兩地書》。
林語堂對魯迅到廈大后的處境有如下描述:“我請魯迅至廈門大學,(魯迅)遭同事擺布追逐,至三易其廚,吾嘗見魯迅開罐頭在火酒爐上以火腿煮水度日,是吾失地主之誼,而魯迅對我絕無怨言是魯迅之知我。”
魯迅對于校方的排擠,想走又不能走,彷徨徘徊,他說:“只怕我一走,玉堂(林語堂本名)要立即被攻擊。所以有些彷徨。”
魯迅最終還是離開了廈大,來到了廣州中山大學,因為他人生的第一個貴人許壽裳在中山大學擔任教務長,而且許廣平也在廣州。魯迅又函邀林語堂赴粵任教,林語堂因福建是家鄉,不愿再遷而留在廈大。
兩人的摯友情誼由此可見一斑。
在中山大學,年輕的共產黨員畢磊成為廣州黨組織與魯迅的聯系人,在畢磊的牽線下,魯迅曾與陳延年會面。
郁達夫與郭沫若同是創造社的創始人,據郁達夫的回憶文章,此時的魯迅已決定與左翼的創造社聯合,此事當時只有郁達夫、魯迅和許廣平三人知曉,但計劃永遠沒有變化快。
1927年4月中旬,南昌、九江、上海的清黨運動蔓延到廣州,中山大學大批學生被捕,營救無效后,許壽裳與魯迅同進退,一起離開了廣州。許廣平隨魯迅來到了上海,兩人住進了共和旅社,正式開始同居生活。
抵達的第二天,郁達夫、王映霞夫婦前來旅社探望,接著林語堂、孫伏園、二弟周建人等人也前來探望,五天后,魯迅決定定居上海。
時許壽裳又回到了蔡元培身邊,擔任大學院院長蔡元培的秘書長,經他的再次堅請,蔡元培又聘用魯迅為大學院的“特約撰述員”,不用打卡上班就可支領月薪300大洋,使漂泊無著的魯迅頓時生活無憂。有了這份薪資,“全身衣著不值2元錢”的魯迅一次性在內山書店買了10多元的書籍,令第一次見到魯迅的內山完造驚詫不已,自此兩人逐漸熟識,成為至交。

04
第三個關鍵人物:史沫特萊
魯迅在上海整整生活了9年多,在他生命的最后幾年,共結識了60余位紅色朋友,最終成就了他“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的崇高地位。
整個過程經歷也充滿著曲折坎坷、柳暗花明的傳奇色彩。
魯迅定居上海后,他與創造社、太陽社的論戰便開始了。論戰起始于成仿吾,繼之馮乃超、李初梨、蔣光慈、錢杏邨等人加入,最后郭沫若也出馬壓陣,雙方你來我往大戰三年。
郁達夫對魯迅真是朋友情誼高于一切,在論戰開始時就退出了創造社,并與魯迅同氣相求、同聲相應。他后來回憶道:“當時創造社、太陽社的左翼青年們,集中火力攻擊魯迅長達三年之久。”
眾所周知,魯迅絲毫沒有退卻讓步,應戰回懟,同時又與梁實秋、林語堂、梁漱溟、胡適、章士釗、顧頡剛等眾多“論敵”先后展開論戰。
1929年5月初,共產國際派往中國的史沫特萊來到上海,她以記者的身份交友甚廣,獲取的信息量巨大,特別是她與董秋斯結識后,對“中國的高爾基”——魯迅有了相當深刻的了解,史沫特萊后來在《中國的戰歌》一書中寫道:“魯迅是一位偉大的作家,被一些中國人稱作中國的高爾基。”
高爾基是蘇聯社會主義文學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史沫特萊認為魯迅既然是中國的高爾基,中國黨應該指示年輕的革命者停止對魯迅的攻擊,轉而團結魯迅,讓他成為革命的旗手來影響年輕人,從而促進革命。
徐恩曾在其回憶錄中談到這事時,這樣寫道:“這情形被史沫特萊看到,認為這是共產黨的失策,因為魯迅在中國文壇和青年群中極有影響力量,大可加以利用,因而向共產黨建議應設法把他爭取過來。這建議立即被接受……”
由于史沫特萊與中共并無直接的聯系,這個建議應該是直接向共產國際提的,再由共產國際向中共中央下達了結束論爭、團結魯迅的相關指示。
中共中央對此項工作的重視程度堪比四年以后的遠東反戰會議。
長達三年的論爭終于平息,其源頭就在史沫特萊的暗中相助。
1929年10月,中共中央正式發出了“黨中央關于停止同魯迅論爭的指示”,并派中宣部文委書記潘漢年、秘書吳黎平下到基層貫徹執行中央決定。
于是左聯開始籌建,自由大同盟開始發起,魯迅都是發起人之一,繼而在共產國際代表埃韋特、伊羅生實際控制的民權保障同盟中,魯迅又擔任了執行委員。
在此過程中,馮雪峰成為黨組織與魯迅的聯系人,在他的牽線聯絡下,魯迅與李立三、瞿秋白、陳賡等中共領導人先后會面。
魯迅轉向左翼,靠攏紅色,立即被國民黨特務監視監控。在魯迅加入自由大同盟后,即被國民黨浙江省黨部宣傳部長許紹棣定性為“墮落文人”,并呈請上級對其進行明文通緝,內山完造將魯迅從景云里寓所轉移至拉摩斯公寓避難。
東方旅社事件后,因受密友柔石的牽連,魯迅再度面臨危難,內山完造又將魯迅安置在花園莊旅店避難39天。
周根康、張榮甫被捕后,內山完造再次將魯迅安排在千愛里三號寓所避居25天。
自此,魯迅大陸新村的住址對外嚴格保密,他與人會面的地點幾乎全部定在內山書店,而會面的聯系人便是內山完造。
即便在如此險惡的環境中,魯迅對紅色朋友仍然關愛有加,并向紅色朋友伸出援助之手。
他寫文章紀念左聯五烈士,讓世人知曉、記住了左聯五烈士;上海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黃平在天津被捕后,他親筆寫信給宋慶齡、蔡元培,請他們以民權保障同盟的名義進行營救;陳賡在鄂豫皖蘇區負傷抵滬療傷時,曾到他家中講述紅軍英勇作戰的情況;昔日“論敵”成仿吾從鄂豫皖抵滬找黨,通過內山書店找到他,再由他幫其接上了組織關系;瞿秋白被捕后他盡全力營救,瞿遇難后,他整理瞿秋白的遺稿,出版了《海上述林》;他幫助丁玲脫離囹圄,奔赴延安;他幫助吳奚如探悉了“怪西人案”的來龍去脈,使中共地工人員的損失降至最低;遠東反戰會議之前,他在華懋飯店及伊羅生的住所分別會見了國際代表馬萊和古久里;他在銀行保險箱中保存了方志敏托人輾轉送來的《給黨中央的信》等獄中遺稿……
這些紅色故事只是魯迅與60余個紅色朋友交往中的雪泥鴻爪和驚鴻一瞥。

05
魯迅的“神交”:偉人毛澤東
以上的所有記述仍不是魯迅“為什么得到這么多人的愛戴”的全部和真正原因,直到偉人毛澤東成為中共的實際最高領導人。
魯迅與毛澤東,二人從未謀面,卻相互讀過對方的文章詩詞,當魯迅讀到毛澤東在第一、二次反圍剿勝利后所作的詩詞時,對馮雪峰說毛澤東的詩詞“有一股山大王的氣概”。
馮雪峰因身份暴露受到追捕,“于1933年12月中旬,悄沒生息地離開了上海,踏上了去江西瑞金的征程。”
馮雪峰到中央蘇區后,博古在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總書記,周恩來就任紅軍總政委,毛澤東則在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后被完全架空。
“比較空閑”的毛澤東便常找馮雪峰聊天,“他們談得最多的是魯迅。”
毛澤東熟讀并異常喜歡魯迅的作品,他對馮雪峰說:“我與魯迅的心是相通的”。
兩位偉人心靈相通的交集點或許就是他們都不忍看著窮人受凌辱、受壓迫!魯迅拿筆桿子啟迪民智,鼓舞人們追求光明,毛澤東則用槍桿子領導人民鬧革命,兩人的終極目標都是希望窮人翻身得解放、做世界的主人、過上好日子。
長征、東征后的馮雪峰領受中央的命令,于1936年4月重回上海開展地下工作,他首先找到了魯迅,并住在了魯迅家中。
在路易艾黎的翻譯下,馮雪峰向魯迅、史沫特萊詳細講述了紅軍長征與東征的經過,并與魯迅單獨交流了紅軍實際當家人毛澤東對他的評價,這令魯迅感動不已。聽到陜北缺醫少藥,物資短缺,魯迅拿出100元交給馮雪峰,讓他給毛澤東買些東西捎去。而宋慶齡、史沫特萊則安排德共黨員馮海伯前往西安開設診所,作為接收醫藥和醫療器械的中轉站。
馮雪峰的政治交通員周文買了火腿、罐頭香煙、圍巾等物送到西安,再經西安的交通員送達陜北。
但魯迅怎么也沒想到,在他生命的最后半年中,會再次卷入一場紅色論爭——關于“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兩個口號的論爭。
發生于上海的兩個革命口號之爭,映射著延安的毛澤東與莫斯科的王明之間的政治斗爭。
時任左聯黨團書記的周揚提出“國防文學”的口號,“是因為當時在共產國際的中共代表王明的指示或影響……為了討好斯大林,王明不惜代價,實際上走向‘求蔣抗日’,他的第一個實際行動就是解散左聯,以‘國防文學’的口號來結束‘左翼’的長達十年的努力和抗爭。”
而“與此同時,中央紅軍從蔣介石的圍追堵截中死里逃生,召開了瓦窯堡會議,提出的卻是與斯大林和王明并不一致的‘逼蔣抗日’的方針。馮雪峰參加了這次會議,并被特派到上海來向左翼文化界傳達和貫徹這一精神。”
內涵不同的指示精神分別來自莫斯科和延安,上海黨內的斗爭就無可避免,顯露于外的就是兩個口號之爭。
魯迅的不幸逝世,令偉人毛澤東大為痛惜,既然國民政府不肯為他舉行國葬,那么共產黨人就為他舉行風光大葬,并讓葬禮變成一場“群眾性的運動”。
偉人毛澤東對魯迅的褒揚和推崇,不因魯迅的逝世而消減,反而有增無減。
魯迅逝世一周年,毛澤東在延安發表講話,稱魯迅為“民族解放的急先鋒”、“黨外的布爾什維克”。
魯迅逝世二周年,周恩來在危城武漢發表講話,他秉承偉人的意旨,稱“魯迅先生之偉大,在于一貫的為真理正義而倔強奮斗,至死不屈,并在于從極其艱險困難的處境中,預見與確信有光明的將來。”
1940年1月9日,在陜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毛澤東在講演中說:“在我黨領導的文化新軍中,魯迅,就是這個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魯迅是……空前的民族英雄。”
魯迅“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實際在暗諷王明的奴顏媚骨,偉人毛澤東通過褒揚、推崇魯迅,向黨內傳遞出一個鮮明而確定的政治信號。
“不久,王明失去了共產國際的支持和保護,毛澤東以反對教條主義(洋教條)對王明實行有力的批判,中央對抗戰初期的右傾機會主義展開清算,‘國防文學’口號實際上被中共否定。”
兩個口號的論爭無疑是以魯迅、馮雪峰為代表的一方取得完勝。
喜歡魯迅、敬重魯迅,毛澤東是發自肺腑的,他與魯迅心靈相通,神交已久,在毛澤東延安窯洞辦公桌的右手邊,端放著的是《魯迅全集》。
褒揚魯迅、推崇魯迅,毛澤東在特定的歷史階段,借用魯迅與王明開展斗爭,策略是高超的。他說魯迅一直戰斗到死,魯迅生前最后時刻在跟誰戰斗?毫無疑問是跟王明。
毛澤東對魯迅的評價之高,世上絕無第二人能夠企及。
1949年7月,新中國建立在即時召開的全國文聯代表大會,給參會代表發了一枚紀念章,紀念章上有兩個頭像,前為毛澤東,后為魯迅。
新中國建立之后,毛澤東在講話中常常稱“馬、恩、列、斯、魯”,把魯迅和以往的馬列主義大家并列在一起。
1971年,毛澤東在武漢說:“魯迅是中國的第一個圣人,中國第一個圣人不是孔子,也不是我,我是圣人的學生。”
1976年,在毛澤東生命的最后一年,他對身邊人還說“多讀點魯迅”。
行文至此,魯迅侄女周曄心中“為什么伯父得到這么多人的愛戴?”的驚異應迎刃而解了,而魯迅先生為什么在中國家喻戶曉、婦幼皆知,也應豁然開朗了。

「 支持烏有之鄉!」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