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
《現代主義》原書初版于1976年,1992年國內翻譯出版,是一本頗有教益的系統的論文集,研究文學藝術(以至各思想領域)向現代主義轉變的背景、具體內容和各種方向。
馬雅可夫斯基的詩,國內翻譯了多卷,很早就想挑選錄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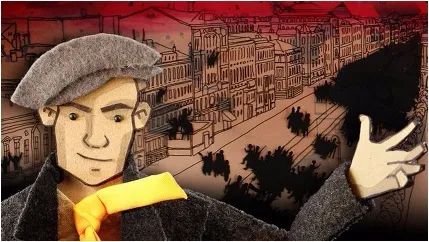
德國作家凱特琳·羅特(Katrin Rothe)《1917年:真實的十月》中的馬雅可夫斯基影像
俄國未來主義
作者│G·M·海德
來源│《現代主義》
(外國文學研究資料叢書),1992
1
弗拉季米爾·馬雅可夫斯基,這位俄國文學中未來主義運動中最有才華、即使不是最善于革新的詩人,在他一九一五年的重要詩作《穿褲子的云》里,把自己稱為“我們今天口若懸河的查拉圖斯特拉”。這并不是他授給自己的唯一堂皇稱號(他還把自己看作《啟示錄》里的基督),但它卻是最貼切的一個:這位分裂主義先知正式宣布——的確,是編造——新時代到來,并給舊世界和舊我宣讀悼詞的預言家姿態,對他是最合適不過了。馬雅可夫斯基和尼采都具有高亢聒耳的聲調,希望在更新事業中廢棄一切,并神經過敏地主張不惜巨大代價以征服和支配他的性格中被動的、直觀的方面。馬雅可夫斯基特別蔑視前面一代象征主義詩人和他們辨析入微、意在言外的文學,這種文學乃是它被自覺地定位其中的那個文明發展晚近階段的頹敗的花朵。未來主義得之于尼采的一般影響的確是實質性的,就運動以尼采式的激情,獻身于擺脫頹廢的過去,肯定人反抗決定論和習慣的意志而論,尼采的影響大概是最極端和最強烈的。
許多同時代批評家把馬雅可夫斯基及其朋友們的所作所為僅僅看作粗俗的夸張和自我宣傳,這并不足為奇。他們不求取悅于人:一九一二年馬雅可夫斯基在克列布尼科夫、克魯喬尼克和戴維·布爾柳克協助下炮制的那篇聲名狼藉但名符其實的宣言——《給公眾趣味一記耳光》,似乎只是這個集團在公開場合喧囂尋釁的典型作風轉化為書面形式而已,他們的這個作風幾乎一直保持到一九一七年革命前夕。克列布尼科夫聒耳欲聾地標榜自己是“世界總統”;拉里奧諾夫和岡察洛娃,兩位最有才華的未來主義畫家,身穿奇裝異服、頭戴面具招搖過市;在咖啡館和餐廳舉行的“即興表演”很象達達主義放浪形骸的宴會。馬雅可夫斯基本人在盛大集會上登臺作咄咄逼人的粗魯表演——朗誦詩歌,大聲講粗話,例如一九一七年在彼得堡的芬蘭畫展開幕式那次聲名狼藉的露面。然而鮑里斯·帕斯捷爾納克——他的詩作令人很難指責他對馬雅可夫斯基有什么偏見——描寫他在一九一四年初見這位詩人的情景,卻烘托出一個極富創作能力、遠非單憑驚世駭俗取勝于人的品格,而他的描寫風格又是非常敏感和顯然公正的:
他坐在椅子上象騎在摩托車的鞍座上,身體前傾,把香腸切成片并迅速吞食;玩紙牌,眼睛轉來轉去,頭卻不動;沿庫茲涅斯基大街莊重地漫步;用鼻音大聲吟誦自己和別人一些經過深思熟慮的作品片斷,好象吟誦禮拜禱詞的片斷似的,皺眉,思有所得,驅車兜風,當眾誦讀。在這一切的背景里,就象某個向前猛沖的溜冰者身后留下的軌跡,那里總會隱隱現出某個特殊的專屬于他自己的日子,在這個先于所有已往時日的日子里,他完成了使他顯得如此軒昂自得的驚人起飛。他的行為舉止令人覺得好象某種決定已經付諸實施,而它的后果是不可改變的。這個決定就是他的天才;他在某個時候跟它的遭遇曾使他這樣吃驚,以至它從此便成為他在一切時候的既定主題,而他為體現這主題也已獻出他的整個身心,決無任何顧惜和保留。[1]
摩托車的意象是恰當的,它喚起未來主義者愛好快速運動,愛好向遠方沖刺的聯想,這種沖刺在空間上與他們沖向未來相平行,正如馬里內蒂的一九〇五年早期詩作《致賽車》“為距離而陶醉的賽車”一語所示。馬雅可夫斯基迅速、笨拙的動作,表現城市生活的緊張節奏和同時而不相關聯的繁多刺激,這些被俄國未來主義者——如同他們的意大利先驅那樣——體現在他們的美學理論里,其原則是藝術必須和生活一樣不連續,必須釋放類似機器和城市所具有的能量,以推動人類去征服時空。馬雅可夫斯基在《詩是怎樣寫成的?》里面寫道:
為了描寫愛的溫柔,請搭上從盧比昂斯基廣場到諾金廣場的七路公共汽車吧。那可怕的顛簸會使改變了的生活的魅力一下突現出來,比任何別的東西都管用。[2]
巨大的人的感情,從馬雅可夫斯基叫作頹廢派和象征主義詩歌的“顫抖和悸動”里解脫出來,被戲劇化地同城市動力學相聯系。技巧與未來主義的繪畫相似,如安伯托·博齊奧尼的《街上的喧聲穿堂入室》(1911)或卡羅·卡拉的《馬車的顛簸》(1911),那里強烈的不連續性沖擊著和歪曲著感受力:在俄國繪畫里,如果沒有嚴格對應的作品的話,娜塔麗婭·岡察洛娃的《騎車人》(1912)或馬列維奇的《磨刀人》(1912)是可以比擬的。上面這段馬雅可夫斯基的話也揭示了導致他服膺布爾什維克領袖的那種古怪的唯物論,因此也和他們一樣,他致力于意識的革命化。機械化不但塑造知覺(如印象派所認為的那樣),而且塑造意識;盡管俄國未來主義和意大利未來主義截然相反,不是尋求人的機械化,而是歌頌戰勝自然的人。對于這時的俄國人來說,機器跟西方的相比雖然還很原始,它們在社會中卻起革命的作用,并反映到藝術里去;這種作用把它們跟馬里內蒂所歌頌的流線型汽車區別開來,也把俄國未來主義與意大利未來主義從政治上區別開來。
正如未來主義者多少熱心地指出的那樣,布爾什維克主義很象他們自己的運動,是一種抓住將來,把它的尾巴拴在現在這部笨重牛車上的努力。帕斯捷爾納克筆下滑冰者的鮮明意象,刻畫了—個對俄國的落后、對精疲力竭的文學傳統的愚蠢無聊不勝煩躁的人;它也暗示某種不穩定性。托洛茨基在他的《文學與革命》(1924)里明確指出一個事實,“在未來主義對過去的夸張的拒絕里,包含的是波西米亞式豪放不羈的藝術家的虛無主義,而不是無產階級的革命主義”。可是也無可否認,未來主義的作品是革命塑造出來的。馬雅可夫斯基在一九一七年以前很久,甚至當他還是一個學童時,就已卷入革命的鼓動。他有時顯得天真的對水電站的傾心(在《穿褲子的云》里他稱自己為“機器和英國的贊揚者”),助長他要消除經濟落后的革命主張,這種落后是俄國專制制度的產物和支柱。他撰寫于一九二八年的機智的自傳《我自己》告訴我們,他幼年時代看見納卡采杰王子鉚釘廠燈火通明的夜景,使他相信電力勝過自然:自然“不夠時新”。他在早期未來主義即興表演的愉快日子里發展起來的自我宣傳技巧,后來讓位于一種精心設計的,可向大量聽眾傳播社會主義和詩歌真理而無需加以通俗簡化的講臺方式;從這種綜合所提出的特定問題來看,他的成功是令人矚目的。他的詩歌風格和措詞,別出心裁地吸收了大眾(特別是城市)語言和民謠形式,勇敢地試圖反馬拉美之道而行之,不是去提純它的用語,而是把它激活起來。《詩是怎樣寫成的?》這樣界定問題:
革命……已經把粗陋的群眾語言推上街頭,繁華區的大道上涌流著郊區俚語,知識界軟弱無力的次級語言,連同它閹割過的名詞“理想”,“正義的原則”,“基督和反基督的先驗觀照”——所有這些在餐館里輕聲細語的詞藻都被踩到了腳底。新的語言成分已經出現。我們怎樣用它寫詩呢?……我們怎樣才能把口頭語言錘煉成為詩歌,從口頭語言把詩歌萃取出未呢?[3]
但現在馬雅可夫斯基已經遠離未來主義早期階段了;這些評述在某種程度上表明他對社會主義國家承擔了義務,那是其他未來主義者有所不能的。他的作品跨越未來主義,從原始表現直到發展成為一種更唯理論的抽象構成主義,連同它令人矚目的建筑方案和戲劇設計。但許多所謂立體-未來主義[4]的其他信徒的無政府主義,不容他們按社會主義繪圖板調整自己的藝術。正如托洛茨基正確地說過的那樣,未來主義實質上是前革命思潮,而馬雅可夫斯基深思熟慮過的頑強的獻身精神決不是運動的主流。未來主義與傳統的完全決裂留下許多可能的政治選擇:的確,意大利未來主義就是倒向法西斯主義的。
2
未來主義美學的主要問題是努力把詞本身從文學傳統的覆蓋物下解放出來。這樣做的途徑之一是前引馬雅可夫斯基那段話所提示的方法;另一條途徑是堅持詞的自主性和文學文本的自主性。如果說第一種主張與象征主義對語言暗指和聯想力量的探索相抵觸的話,那么第二種主張顯然和馬拉美對德加的著名評論相聯系,他說,“親愛的德加,詩不是用觀念,而是用詞寫成的”。詞被詩人所指定,選用到他的文本的自由結構里,它們也就從日常談話的壓抑下解脫出來;象征主義者的藝術致力于救贖墮落的世界,未來主義者則認為世界及附著于它的語言并沒有墮落,只是僵化而已。未來主義詩歌是功能性的——是為發掘金礦而穿鑿巖石的鉆頭。馬里內蒂曾鼓吹詩人只用動飼的不定式,“以便使動怍不局限于單一的動因:我們對動作的感知更多于對動作者的感知。”這樣,他就有力地支持了奧爾特加·y·加塞特所謂我們時代“藝術非人性化”的東西——群體的人只是一系列功能罷了。人的個性概念已經改變,正如一九一四年六月D·H·勞倫斯致愛德華·加尼特那封對馬里內蒂的物質“人體學”表示興趣的著名信件所論證的那樣。馬里內蒂的許多作品不是按人性化的句法安排版面,而是按一定的排印設計,形成一種原初的視覺整體;同樣,馬雅可夫斯基成卷的詩作也是以新奇的排版和布局出現,或者出自他本人(馬雅可夫斯基對繪畫藝術頗有造詣)的設計,或者是他的某位同事的構思。所以,和馬里內蒂的情形一樣,當詞在印頁上忽上忽下,忽而變大忽而變小以至于無,或形成各種可體現或違背它們的語義內容的形狀和圖案時,詞就獲得了新的功能。未來主義藝術在許多方面可以說是對瓦格納式“總體藝術”夢想的擅自修改。對語法和句法的攻擊,對詞的音響和圖形素質的強調,都打擊了書籍本身,打擊了排列成行的字詞按部就班地橫過頁面這種歐洲社會交流思想的主導方式。未來主義戲劇在俄國和在意大利一樣——未來主義都是這樣那樣地富于戲劇性的——要求在不受文本約束的場面讓全體聽眾參加進來;同樣,他們的詩歌要求讀者在構成文本方面給予積極的合作(也許不象達達主義者的作品那樣自由,達達主義者的部分作法已被未來主義者所預先實行了〉。瓦西里、卡緬斯基(1864-1961)的“鋼筋混凝土詩”,在建構上和最新式的具體詩或碎切詩是一樣的漫無規律;也象這種詩一樣,可按不同的方式解讀或“表演”,每次都揭示不同的意義。維列米爾·克列布尼科夫的詩作《笑聲祓魔》(1910)選取俄語的“笑”字,用不同的屈折和結尾與這個詞根結合成詞(大多數“不存在”),使它玩出不尋常的把戲,便是解放詞從而也解放讀者的一種方式。它與其說是語義學的實驗,不如說是利用俄語特有的構詞程序的形態學實驗;它的咒語式樣則依靠巫醫的感通魔法來表現笑聲的解放效果,這種巫醫奇怪地變成俄國未來主義所喜愛的詩人的借喻,變成這個運動重要的原始主義成分的一部分了。當然,這首詩也是一招絕技,象駕駛飛機從塔橋底下穿過似的——一種為未來主義者所愛好的業績,出奇地大膽,好表現而且是最新奇的。克列布尼科夫是重要宣言《給公眾趣味一記耳光》的署名者之一:這個立體-未來主義者集團是有共同目標的,盡管看來文件中攻擊語言的部分是克列布尼科夫和克魯喬尼克的大作,而攻擊傳統的部分則出自馬雅可夫斯基和布爾柳克之手。這篇宣言要求授權詩人
用做作的和編造的詞來擴充人民的詞匯。詞在更新著……對祖上傳下來的語言宣告無限的憎惡。
克列布尼科夫和克魯喬尼克還寫了《詞本身》(1913)宣言,接著克魯喬尼克又進一步寫了《詞本身的聲明》(1913)——一篇出自未來主義者對永恒性的輕蔑而寫的粗糙的書目提要。前一篇宣言類似馬里內蒂的“自由語”,用意也相近。意大利人有更加發達的塑性感覺,他們的未來主義運動與意大利的博物館文化相論爭。俄國人則強調口頭和聽覺效果;他們利用民間詩歌和賽西亞神話——這是一種復合現象,為了當前目的,不妨把它界定為一種極端的和神秘的民族主義,它祈求以賽西亞人為象征的原始非理性主義迅即戰勝歐洲的理性主義和唯物主義——由此而有已經提到的巫術,不熟悉這一現象的讀者可參看斯特拉文斯基的《春祭》(1913)。兩篇宣言中這較早的一篇開頭舉出了詩歌里有表現力的音響的例子,其中最抽象的是克魯喬尼克聲名不佳的
Dyr bul shchyl
ubeshchur
skum
vy so bu
r 1 ez [5]
這就是整個文本,在英語里(或不如說在用英語字母拼寫出來的字樣里,如上文那樣)和在俄語里一樣,是沒有意義的,盡管在俄語里這些音響暗示某些可能由它們拼讀出來的詞或詞素。作者聲稱它們是非常俄羅斯的音響(有些在斯拉夫語以外是沒有真正對應物的);而且,在拒絕歐洲影響的賽西亞沖動支配下,克列布尼科夫和克魯喬尼克斷言此詩比普希金全部作品還更加是俄羅斯的。國際性的普希金,最偉大的俄國詩人,被《一記耳光》說成是應“從現代汽船上扔下海去的”首批作家之一,這個說法很象龐德斷言人們不需要閱讀莎士比亞,你可以從“惱人的周圍談話”里找到你需要知道的關于他的一切。所談的語言應當是“超理性的”,擺脫一切僵硬的邏輯形式,這些形式至少從陀思妥耶夫斯基時代以來就被看作是西方思想的產物:它那有表現力的音響力量應當發揮沖擊作用,而不被概念化過程所阻隔,以免分散能量。其效果可與博齊奧尼所召喚的“物理先驗主義”相比,而且可能也受馬里內蒂一九一二年“自由語”宣言的影響,他聲稱把詞從傳統意義的約束下解放出來,會便利人們彼此之間“無線電”想象的直接溝通。這樣造成的音響傾向于成為不協和音:這部分地是為了引起讀者的注意,但照克魯喬尼克的說法,更是因為不協和音在我們心靈中知道如何把音響轉化為協和音。和諧無非是兩個不協和音在一個力點上的平衡:一種在意象主義和旋渦派理論里也找得到的動力學。這篇宣言以及別的同類宣言,到處都是演出的強調和強調的演出。一九一三年兩次演出(或兩出戲,因為缺少更確切的詞)在圣彼得堡出臺,它們顯示了這個集團各種結合起來的才能:一次是馬雅可夫斯基的《弗拉季米爾·馬雅可夫斯基:一出悲劇》,一次是克魯喬尼克不尋常的歌劇——由克列布尼科夫寫序、馬列維奇設計布景的《戰勝太陽》。
這出歌劇的主題,后來在馬雅可夫斯基的詩作《弗拉季米爾·馬雅可夫斯基在避暑莊園的奇遇》(1920)里再一次出現。未來主義一切表現形式的中心是戰勝時間,不象普魯斯特或艾略特那樣把它想象為回到過去的運動,而是想象為躍入將來。在馬雅可夫斯基的詩里,詩人邀請太陽一道用茶,以便打斷永恒的,使他日久生厭的日出日落;憑借奇妙的想象,太陽承認為繪制宣傳畫忙個通宵的馬雅可夫斯基,是在制造行將象太陽的熱力那樣向四外散播的光明和溫暖,一個顯示人類意志力量勝過自然的過程。克魯喬尼克的歌劇(1913)——為此馬列維奇制作了被他說成是他的首批至上主義(幾何上抽象)圖案的東西——描寫來自“將來國度”的“強壯者”,和一隊運動員、一個英勇的飛行員一起,制服了“愛爭吵者”、“懷惡意者”和各種各樣的歷史人物,共同慶祝未來世界從時間里解放出來。照這樣說法,它似乎是表現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的輕率混合;事實上,因為整個劇本寫得晦澀難懂,到處充斥dyr bul shchyl之類的咕噥和口哨,情節混亂到幾乎無法領會,這出歌劇與其說是可怕,不如說是可笑。鮑里斯·托馬舍夫斯基回憶首演之夜的文章(《戲劇》No,4,1938)表明,正如一九一七年科克托—畢加索—薩蒂埃的《展出》那樣,整個節目不妨當作一種雜技表演來欣賞。高級藝術和輕歌舞之間的界限,在熱情高漲的混雜人群腳下被踐踏得不復可辨。聽眾似乎被事態吸引住了,情緒極好,僅當一次挨到直接辱罵時,才變得有點按捺不住。《戰勝太陽》是未來主義者宣傳他們自己的經營最力的作品。
3
革命后,未來主義者在蘇維埃文化生活中支配了不長一段時間。這并非因為沒有其他先鋒派運動向他們的最高地位提出挑戰;二十年代在俄國和在別處一樣,是一個極富藝術實驗的時期。他們的統治地位其實應歸功于能干的、在政治上承擔義務的馬雅可夫斯基的努力,他以詩人和新制度宣傳家的資格,把他不知疲倦的精力(和老練的、可與布萊希特媲美的辨證美學)交給布爾什維克去支配。在戰時共產主義艱苦條件下出版的,馬雅可夫斯基和才華橫溢的教條主義者奧西普·布里克在其中起主導作用的短命刊物《公社藝術》,一九一八年首期發表了馬雅可夫斯基的詩作《給藝術大軍的命令》,號召未來主義者和布爾什維克通力合作,為打敗政治和美學上的過去勢力而奮勇前進。這個號召是那些在精神上較接近象征主義那一代的未來主義者,如謝爾舍涅維奇(馬里內蒂在俄國的翻版)和伊戈爾·塞維里亞寧(他創立所謂自我-未來主義,區別于馬雅可夫斯基的立體-未來主義)之流,所不能接受的。布里克要求具體的、反唯心主義的藝術,把藝術創作歸結為生產過程的一個方面(如同馬雅可夫斯基《詩是怎樣寫成的?》所主張的那樣),把藝術家看作工人而不是英雄(浪漫主義者和象征主義者把他們看作英雄),這種觀點為從二十年代撐持過來的那些先鋒派的偽唯物主義理論定下了調子——他們堅持“未來主義者”稱號甚至到該詞在政治上已變得可疑之后,這不過是因為唯有在這一革命旗幟下,才能為抽象藝術提出連貫的唯物論辨解。在這期間,一個重要的“功能主義”批評和理論派別(今天以“形式主義”的通稱知名)已經產生,索緒爾新語言學所鼓舞的這一學派,把未來主義者(它們的親密盟友)的語言實驗當作對陳腐的文學治學方法的必要挑戰,當作新的批評方法和整個文學理論的依據。[6]在這個背景下,最令人矚目的論文無疑是羅曼·雅各布森的《最新俄國詩歌》(1919;1921修訂),[7]一篇寫于他還是“莫斯科語言學小組”成員時的著作(他后來移居布拉格,在那里發表第二版,隨后又去美國);扼要闡明一下未來主義詩歌和形式主義批評之間的聯系是值得的。
雅各布森不懷疑“最新”俄國詩歌是所謂未來主義詩歌,盡管他拒絕從整體上給這個運動所代表的東西下一類型學定義。他贊同地援引克列布尼科夫的話,“將來是藝術的祖國”,以此為出發點,首先分析了時間和陳腐傳統使革新(如普希金的革新,他常常引證這位詩人并引起爭議)轉變為正統的過程,然后又分析了現在的詩歌(以克列布尼科夫為代表,他詳細分析此人的詩作)和過去的詩歌獲得更新的相反過程。他堅稱,詩歌是憑借特別的語言手段從內部更新的;他的論文自始至終把詩歌語言當作一種超越語言來處理。新的題材“內容”(他和I·A·理查茲一樣,不認為“內容”和題材有什么兩樣)所能做的只不過是為新的語言形式——聲音、句法、節奏等——提供他所謂的“動因”而已。所以把革新的分析建立在外部或社會原因的基礎上是錯誤的。雅各布森于是就把馬里內蒂關于文學形式是在內外新的經驗形式壓力下獲得更新的錯誤的印象主義“報導”理論(雅各布森自己的術語),拿來與克魯喬尼克關于從詩歌語言內部出現的新形式產生新內容并最終產生新境界的主張作了對比。在這個比較的基礎上,雅各布森把他所謂的詩歌語言系統(俄國詩人,特別是克列布尼科夫的語言系統)和情感或表達情感的語言系統(馬里內蒂的語言系統)作了區別;這樣,詩歌就被描寫成具有服從內在法則的特性,它的交際功能被削減到最低限度。正如一切其他藝術都是由自我生效的“材料”塑造所構成,詩歌也是這樣:它的“材料”就是詞。結果文學研究被適當地界定為對文學性的研究。傳記、心理、政治等等都被這個理論貶為不重要的角色;的確,早期形式主義理論滿足于在論戰中撇開超文學材料而不予理睬,只是后來(在諸如沃洛希諾夫《馬克思主義和語言哲學》之類的書里)[8]它才變成一種更加精細的符號系統方案。在他的理論里,被雅各布森稱為“情感和精神經驗世界”(即傳統詩歌資料)的東西,是當作對文學語言的“辯護”來予以說明的:他論證說,甚至浪漫主義作家,當他們的作品初問世時,也是被人當作形式的而不是經驗內容的革新家來接受,后者被理解為只是前者的“辯護”(雅各布森援引同時代批評家證明這點)。在此背景下,有關克列布尼科夫作品最重要的事實是,他離開早期作品求助于情節結構為“非理性”詩歌手法辯護的作法,移向對民間故事和民謠一類作品中這種手法的有特色的“剝露”而撇開任何辯護。音響(或其他語言要素)控制意義,產生歧義、對應和(克列布尼科夫最喜歡的)雅各布森所謂“變形”(性質各異,但基本上是逆轉或否定的隱喻,用什克洛夫斯基的關鍵性術語來說,它把言語的指涉對象生疏化了)。[9]對民間材料、趣聞和笑話結構和形形色色俏皮話的興趣,在學術研究中對這類“低級”材料有爭議的利用,是這個時期文學先鋒派大都具有的特征(達達主義者,喬伊斯,當然,在類比的意義上還有弗洛伊德)。
雅各布森指明,未來主義文本的艱難和陌生感迫使讀者參與把它們實感化的過程。這個公式和它的基礎概念“復雜化”或“艱難化”(也是什克洛夫斯基的關鍵性術語)的提出,在時間上先于羅蘭·巴特對“可讀性”和“可寫性”的理論區分:后面這個公式對形式主義者的發現并沒有增加什么重要的東西。很清楚,未來主義者和布爾什維克的結盟正屬于這個(后來被構成主義美學界定得更加嚴峻的)“實感化”領域;但雅各布森沒有觸及這一點,而對它的充分調査會是極其復雜的。從純粹風格的層面來看,克列布尼科夫文本的特色在于,它們的各種成分是通過并置聯結在一起,或者說是并時地而不是順序地聯結著,這種手法和未來主義者把常見的文學引喻(矛盾法,夸張法,語法形式借代)加以具體的實感化的典型作法相結合,就造成一種自主的關系系統。由此而有詩的“空間”,和圖畫的空間類似,從而語言就成為多維的,而不是(象它在理性的、非詩意的說話里面所力求做到的那樣)單純連續的,而文學也就可以同電影的時間復合性媲美了。在現代詩人,尤其是未來主義詩人使用的造句手法中,造成非線性時間連續最有效的辦法之一是“無動詞”,雅各布森既從未來主義詩人也從其他詩人(如馬利安霍夫)那里舉出這樣的例子。“無動詞”隱含整首詩變成一個動詞的意思。克列布尼科夫本人區別了兩種詞,一種是能用它來看的詞(“詞-眼”),一種是能用它來做的詞(“詞-手”):這可能不是很精巧的一種對應,但從這里至少能抓住象征主義的語義主義和未來主義的功能主義之間的根本差別。由于這種差別,克列布尼科夫的詩歌(推而廣之,一般未來主義的詩歌,既然有關的人都向他學習)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種分離性的,而不是聯合性的詩歌。這個帶有典型傾向的公式(雅各布森和其他形式主義批評家一樣,幾乎就是以這樣的措詞來表述公式的),當然與T·S·艾略特在論玄學派詩人時所闡述的再聯合學說正相反對——那篇論文不論如何不同凡響,顯然是具有傳統主義的含義和象征主義的效用的。雅各布森從兒歌、民間咒語和儀式以及(馬雅可夫斯基所欣賞和模仿的)城市歌謠收集分離的和陌生化的例子,樂此不疲,把它們與克列布尼科夫的文字游戲、雙關語等中肯地聯系起來,以“詩歌詞源”的名目歸為一類(他把詩歌詞源界定為與他種詞源有關、但在這種“形式”下專屬于詩歌的一種特殊的詞源類別)。這類詞源引起的語音和語義的變形和新意,是詩歌詞源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參與構成了雅各布森所謂詞的新義的“意義潛力”:那就是說,詞的抽象作用的潛力(雅各布森就這樣把他的論文帶回到開始時反對馬里內蒂“印象主義”的論點:事實上,俄語МеτнЫй一詞也許譯作“非實體的”會比“抽象的”更確切些)。因此他的結論是,如果押韻最早的歷史表現是語義動機促成的話,那么在克列布尼科夫的押韻(也隱含馬雅可夫斯基的押韻)里,我們知道了一種被雅各布森巧妙地說成“在尋找意義的詞”的東西。[10]雅各布森的論文本身就是一篇引人矚目的創作,它的別開生面和左右逢源的準確性可以看作形式主義批評反對偶象崇拜和引起爭議的最典型的代表作。
這個批評運動的歷史文獻當然是很豐富的,更不用說雅各布森和他同事們的作品——不論他們是否留在俄國——是從俄國未來主義的背景大大向前邁進了:二十和三十年代“通俗派”和“莫斯科語言學小組”的最好著作決非僅限于對先鋒派的研究而已,他們造成了批評的一次革命,和對俄國及外國先前文學的一次根本性的重新評價,就象英美的“新批評派”所造成的那樣,后者盡管有更大保守性,是在現代主義環境中以類似的方式崛起的。不過,這些俄國人的影響,無論在范圍上還是方向上都比“新批評派”更廣更多。除了雅各布森自己在語言學方面的主要貢獻以外,俄國形式主義者也對現代符號學理論作出很大的貢獻,而茨維坦·托多羅夫譯成法語的形式主義論文集《文學理論》(1965),一直有著巨大影響。有趣的是,由列維-斯特勞斯的《結構人類學》所肇始的語言學和其他符號學分支之間的相互指責,已導致結構主義在蘇聯的復興。[11]
維列米爾·克列布尼科夫——雅各布森論文的主要話題——死于一九二二年。他即使不算俄國未來主義毫無疑義的創始人,也無疑是一位偉大的革新家,他的作品變成其他詩人,包括馬雅可夫斯基在內,從中吸取教益的無限深邃的實驗寶藏。他是非常多產的,這些作品在俄國文學中只是到現在才被放到適當的位置。翻譯成外文的極少,至少在英語是如此。他去世之后,前革命時期無政府的實驗主義也隨之結束。馬雅可夫斯基在一九二三年創辦的刊物《列夫》(“左翼藝術陣線”的縮寫),有力地堅持了未來主義和非客觀(或至少是非再現)的藝術。它停刊于一九二五年,而它的替代物,一九二七年創辦的《新列夫》(《新左翼藝術陣線》),調子是奇怪地反復無常。在日趨保守的政治氣候下,馬雅可夫斯基堅韌不拔的激進態度(他高興地看到妥協性新經濟政策的結束)變緩和了,他保證未來主義并不摒棄過去本身,而僅僅拒絕在現在試圖確認過時的風格。馬雅可夫斯基繼續寫出重要作品,直到一九三〇年自殺為止,但俄國現代主義欣喜若狂的創作激情已經不見了。到克魯喬尼克發表他的《俄國未來主義十五年》(1928)時,這個運動已告終止,盡管他以稍遜的才具,繼續創作到一九三四年,發現此后自己就象龐德筆下的M·維洛格。
和同時代人脫節
被年輕人冷落
為這些幻想的緣故
——縱然他逃脫了許多同輩作家的殘酷命運。俄國現代主義中反對偶象崇拜最力的運動就這樣過去了,身后留下至今享譽不衰的人物馬雅可夫斯基——世界上被人引用最多、理解最少的作家之一。它還留下一個心情矛盾的功能主義,以構成主義的形式繼續生存到三十年代,以催育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并鼓舞蘇聯以外的藝術家。俄國未來主義在豐富的蘇維埃現代派運動中的適當位置——的確,還有這整個運動的意義——只是到了現在才被人們所理解。
[1] 鮑里斯·帕斯捷爾納克:《安全的行為》(1931),喬治·利維譯。
[2] 弗拉季米爾·馬雅可夫斯基:《詩是怎樣寫成的?》,G·M·海德譯(倫敦,1970)。
[3] 弗拉季米爾·馬雅可夫斯基:《詩是怎樣寫成的?》,G·M·海德譯(倫敦,1970)。
[4] 未來主義各個不同的(往往相互矛盾的)組成部分,在弗拉季米爾·馬科夫的標準著作《俄國夫來主義》(倫敦,1969)里有充分的文獻引證。
[5] 弗拉季米爾·馬科夫改用英語字母拼寫,《俄國未來主義》(倫敦,1969)。
[6] 最好的概述仍然是維克托·厄里奇的《俄國形式主義的歷史和學說》(海牙,1969)。
[7] 沃爾夫-迪特爾·斯滕伯爾編《俄國形式主義文集》,第2卷(慕尼黑,1972)收有俄語文本和德語對照譯文。
[8] V·N·沃洛希諾夫:《馬克思主義和語言哲學》:L·馬泰卡和I·R·季圖尼克譯(倫敦和紐約,1973),列寧格勒1930年初版。
[9] 維克多·什克洛夫斯基的兩篇重要論文,《藝術作為技巧》和《斯泰思的〈特里斯川·項狄〉:風格評論》,收入L·T·萊蒙和M·J·里斯編譯的《俄國形式主義批評:四篇論文》(林肯,內不拉斯加,1965)。
[10] 為了一般的研究現代主義,了解這些理論里更多的有關論述,可參閱戴維·洛奇的《現代主義小說的語言:隱喻和轉喻》,第450—464頁及以后。
[11] 德米特里·塞加爾的論著《蘇聯語文學中的結構主義面面觀》為此提供了給人深刻印象的證據,論文收進T·A·塞比奧克即將發表的《結構主義遍布世界》一書。
「 支持烏有之鄉!」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