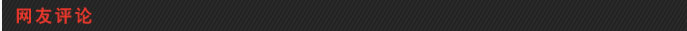朝鮮停戰:原子彈是什么老虎?

今年7月27日是朝鮮停戰協議簽字60周年紀念日。據報道,美國將舉行隆重大會,奧巴馬可能出席。筆者預測,如果奧巴馬出席發言,一定又會豪情萬丈地贊揚美國在那場戰爭中的勝利。的確,奧巴馬演講功夫是第一流的,他的擬稿班子也是第一流的。盡管當年“聯合國軍”總司令美國上將克拉克在停戰協議簽字時說:“我是美國歷史上第一個在沒有取得勝利的停戰協議上簽字的將軍”。但到了2010年,正在韓國訪問的美國總統奧巴馬前往龍山美軍基地慰勞駐韓美軍,發表演講稱,不少人說朝鮮戰爭是“為打成平手的死亡(Dieforatie)”,但現在大家可以重新認識到“朝鮮戰爭絕對不是沒有勝負的戰爭,我們當時取得了勝利,現在仍然還是勝利者”。
關于誰是勝利者的問題,被世界學界公認的,也是中國學界(包括公知)公認的中國近代史權威、美籍華人徐中約先生的評價早已眾所周知:“與聯合國軍隊在朝鮮打成了平局(這本身就是一種勝利)。”
奧巴馬是政治人物。對他的言行,讀者原不必用史實來衡量,問題在于,我們中國卻有一些自由派人士喜歡配合美國總統作義務宣傳。因此,在“抗美援朝是中國最大的錯誤”思想指導下,某些人又發明了中國在美國原子彈威脅下不得已簽“城下之盟”說(見《朝鮮停戰簽字,還緣于美國的核威脅》一文)。可以預期,今后還有很多類似的說法來奇葩爭艷,比如中國跪求和談說之類。筆者以為上述觀點新奇,努力爬梳材料,不料發現其論點實在太不靠譜。就拿朝鮮停戰來說,真的是在原子彈威脅下的“城下之盟”嗎?當年美國國務卿迪安•艾奇遜曾用一句話就回答了這個問題,他說,杜魯門關于使用核武器的表態“把盟友嚇得半死,對敵人卻未起作用”。美國著名的軍事歷史學家約翰•托蘭說得也頗為深刻:“杜魯門的原子彈威脅非但沒有引起毛澤東的擔憂,反被他當成了有用的工具。”今年恰逢停戰60周年,現在來回顧這段關于原子彈的歷史,以此紀念還是很有意義的。
1950年9月5日,毛澤東在中央人民政府第九次會議上說:“對于朝鮮人民,我們需要給予幫助和鼓勵。朝鮮人民對于中國革命是有很大幫助的。中國革命的幾個階段,都有他們的幫助。美國在朝鮮干了起來,也可以在別的地方干起來,它什么都可以干起來。我們不準備就不好。我們準備好了就好對付它。所謂那樣干,無非是打第三次世界大戰,而且打原子彈,長期地打,要比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打得長。我們中國人是打慣了仗的,我們的愿望是不要打仗,但你一定要打,就只好讓你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彈,我打手榴彈,抓住你的弱點,跟著你打,最后打敗你。我們要準備大打、長打、打原子彈。”這是毛澤東首次提到準備打原子彈。毛澤東不是不知道原子彈威力,但他更相信人民戰爭的力量,相信世界人民反核的力量,也洞悉世界政治格局,特別是二戰后形成的美蘇各自戰略重點對使用原子彈的制衡作用。由于做到了“準備好了就好對付它”,終于使美國原子彈成為一個紙老虎。
1950年10月19日,中國人民志愿軍跨過鴨綠江奔赴朝鮮戰場,麥克阿瑟“回家過圣誕節”的叫囂被徹底擊碎。10月29日,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在給麥克阿瑟的指示中同意他由進攻轉入防御。同時,美國決策者認為又不能向中國示弱。11月30日,杜魯門在記者招待會上稱,“聯合國的部隊不打算放棄他們在朝鮮的使命”,美國“將采取任何必要的步驟,以應付軍事局勢”。當他被追問是否包括使用原子彈時,他說:“我們一直在積極地考慮使用它。”順便說一句,美國此后就一直處在“考慮”的層次上,不敢越雷池一步。不過,當時杜魯門還拋出了一句極為令人震驚的話,說他的戰場指揮官將負責對核武器的使用。
盡管幾個小時后白宮新聞辦公室就發布了一份“澄清聲明”,解釋杜魯門“并不是說已經決定要使用原子彈”。但是,杜魯門的這番話還是飛快地傳遍世界的各個角落,瞬間掀起軒然大波——人們普遍認為,杜魯門的話意味著,朝鮮戰場的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已經領受了總統授權,可以隨心所欲使用原子彈了。
美國的盟國一直密切關注戰爭的發展。早在麥克阿瑟下令轟炸鴨綠江上橋梁時,英國、加拿大等就認為這違背了盟國協商的原則,可能導致戰爭擴大。杜魯門在11月30日記者招待會上關于使用原子彈的威脅,更使各盟國震驚不已。反應最激烈的是英國。在倫敦,大約100名工黨議員聯名向首相艾德禮致信,反對在任何情況下美國使用核武器。英國參謀長會議還致電“聯合國軍”總司令麥克阿瑟:“在我們看來,如果在朝鮮使用原子彈,不僅不能有效地阻止中國軍隊前進,而且將會使局勢變得更加糟糕,蘇聯空軍將不可避免地參加戰斗。”英國等國除了擔心使用原子彈會導致蘇聯空軍公開參戰外,他們更擔心的是蘇聯原子彈的報復。這雙方一動原子彈,二戰舊傷尚未愈,豈不又添新傷嗎?情況十萬火急,杜魯門講話后數小時,英國首相艾德禮便要求赴華盛頓與杜魯門會晤,法國總理和外長趕赴倫敦去與英國戰略協調,荷蘭官員也與英國密切接觸,并達成高度共識——必須迫使美國人保持克制。這樣一來,美國的盟國簡直要起來造美國領導地位的反了。在各方壓力下,最后,杜魯門被迫正式聲明“不使用原子彈”。這樣“造反”才大體上平息下來。
不過,美國內部對是否使用原子彈還在爭論。麥克阿瑟是堅定的使用派,他甚至狂妄建議,投擲20至30顆原子彈轟炸中國,再加上其它措施,把戰爭擴大到中國東北,“中共即將面臨軍事崩潰的危機。”麥克阿瑟的我行我素再次引起英國等盟國對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擔心,當時同樣手握原子彈的蘇聯也提出強烈抗議,“炸彈也可用炸彈回敬”。杜魯門不得不親自出面阻止麥克阿瑟的冒險行徑。最后,杜魯門忍無可忍,為了徹底封住這位原子彈“大嘴”,在沒有任何前兆的情況下,突然于1951年4月11日宣布解除麥克阿瑟軍職,即時生效。杜魯門同時向全國發表講話,警告中蘇不要對聯合國軍進行空中攻擊,否則就要對由此引起的后果承擔責任。然而,朝鮮戰場上的地面戰斗依然照常進行。詭譎的是,為麥克阿瑟“滅火”的杜魯門同時下令向關島地區緊急運送核部件,9架B-29轟炸機受命飛越太平洋,接著美軍舉行了公開的核戰演習。后來的事實說明,杜魯門的行動和麥克阿瑟的不一樣,一個是威嚇,一個還真的是想一展宏圖。
這次部署是杜魯門政府在朝鮮戰爭中最重要的一次訴諸原子彈的威嚇行動。因為派往關島、繼而飛至沖繩島的9架B-29轟炸機真的攜載了核彈頭。杜魯門當局的這次核威脅,對中朝軍隊并沒有產生什么影響。盡管那些恫嚇之詞傳到了北京,但在朝鮮戰場上中國志愿軍仍然是按照老傳統——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繼續戰斗。
面對一個有備無患、不怕原子彈威脅的國家,威脅是不起什么作用的。和中國這樣的對手打交道,杜魯門機關算盡,依然一籌莫展。實際上,美國內部對真正使用原子彈一直沒有信心。據后來解密的美國中情局1950年11月9日的備忘錄,即《關于美國可能動用原子彈打擊中共在朝鮮的侵略行動應考慮的問題》,其要顧忌的問題很多,比如,會減小蘇聯介入的可能性嗎?中國會加大兵力還是終止介入?對美國有利嗎?一定有效嗎?對盟國會造成什么影響等等。評估不可謂不周到全面,不過似乎還是“有心無膽”。1951年6月末,B-29轟炸機和所載運的核武器,又悄無聲息地撤回。隨著戰場局勢的進展,美國人隨后不得不坐到談判桌前,開始與中朝方面進行停戰談判。
1952年是美國總統大選年,此時朝鮮戰爭已經打了兩年。美國發現,勝利十分渺茫,和談亦不見希望。這引起美國人民強烈不滿,反戰、厭戰情緒日益高漲。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艾森豪威爾,乘機抓住朝鮮問題攻擊民主黨的杜魯門政府,并最終贏得了總統大選。
當時,大多數的美國人同意采取“強硬步驟”結束這場戰爭。美國政府就使用原子彈的可能性進行了反復討論。新“聯合國軍”司令克拉克又主張使用原子彈,但參謀長聯席會議對使用原子彈的效果表示懷疑,因為敵方只要有很好的地下工事,即使在原子爆炸中也可以不受傷害。而中朝一直在做這方面的工作,大量防止核攻擊的工事已經初具規模。艾森豪威爾為此十分糾結。他認為如果使用原子彈能使美國取得“重大勝利”,那就值得,但他除了對原子彈的效果沒有把握外,還非常擔心盟國的反應,認為那將觸犯全世界人民。
據歷史記載,艾森豪威爾一度也通過印度對中國進行嚴重的核威脅警告,在停戰談判中中國也作出過讓步。據說艾森豪威爾在回憶錄中得意地寫道:中國在朝鮮之所以作出最后的讓步,乃是美國核威脅起到了“抑制的作用”。現在回過頭來看,艾森豪威爾的此番言論與奧巴馬的“勝利”之說都有自吹之嫌。還是來看看美國中情局1953年4月8日,即停戰協議簽訂前三個多月的“特別評估報告”所言:“我們不能夠判斷是否這種認識(指使用原子彈——筆者注)會自動地使共產黨作出必要的讓步,從而締結停戰協定。”總之,“一廂情愿”用在艾森豪威爾和奧巴馬身上,都是比較合適的。
同樣不能忽視的是當時的國際政治格局對原子彈使用的制衡因素。朝鮮戰爭剛開始時,美國的核武器數量還不足以應付在歐洲遏制蘇聯和在朝鮮戰爭中對付朝鮮和中國。也就是說,其核力量還不能兩頭兼顧。到了朝鮮戰爭后期,美國的核力量有大幅度增加,但蘇聯打擊美國的核能力也不斷增長。
歷史的事件總是多種力量合力的結果。不管毛澤東和那代中國領導人是否把每個細節都掐算得那么準,但采取的對策是完全正確的。那時中國認為,“中國方面不能作出任何讓步,因為任何讓步都會被對方理解成懦弱的表現”。中國方面斷言,“要使美方返回談判桌,唯一的做法就是為即將到來的戰爭做準備”。毛澤東的“打原子彈”準備工作算是擊中了美國命門,使美國的原子彈始終沒有超出“紙”的水平,一直到1953年7月27日《朝鮮停戰協定》正式簽署。歷史表明,站起來的中國人民就是不吃美國核訛詐這一套。英國元帥蒙哥馬利于1960年代初訪問中國后,頗有感慨地指出:“戰爭的禁律之一就是不能進攻中國,誰要是進攻就一定要大倒其霉,因為中國就像一塊吸水石一樣,任憑你有原子彈,有大量新式的技術裝備也無濟于事,必將被7億中國人所擊敗。”此前,美國的首任“聯合國軍”總司令麥克阿瑟,那位堅定地要對中國使用原子彈的強人,在臨死前,道出了他一生的從戰教訓,數次勸阻美國的肯尼迪總統和約翰遜總統:千萬不要再在亞洲打仗!
應該說,朝鮮戰爭中的核威脅對中國也產生了影響。自從世界上出現了原子彈,中國就多次受到原子彈的威脅。中國人民也切切實實地感受到沒有核武器受人欺侮的滋味,這是毛澤東那一代中共領導人特別不能忍受的。盡快發展自己的核武器,就成為中國上下共識。
其實,早在朝鮮戰爭前夕,毛澤東訪問莫斯科回來之后,曾對身邊的警衛員說:“這次到蘇聯,開眼界哩!看來原子彈能嚇唬不少人。美國有了,蘇聯也有了,我們也可以搞一點嘛。”蘇聯成功爆炸了原子彈,這無疑對毛澤東是一種巨大的鼓舞。更早的時候,1949年初,中共曾撥美元請錢三強設法到法國購買有關核試驗的儀器和書籍,錢三強因故未能成行,只好托人找到他的導師約里奧•居里代辦。居里托來人帶給毛澤東一番話。他說:“你回去告訴毛澤東,要保衛世界和平,要反對原子彈,就必須有自己的原子彈。原子彈的原理又不是美國人發明的,你們自己有自己的科學家嘛。”這番話,與毛澤東所說,原子彈有了不一定要用,但它是一種威懾,可以保衛和平,真可謂智者所見略同。
新中國在制造原子彈過程中經受的最嚴峻的考驗無異是蘇聯撕毀合同的行為,這更激起了毛澤東的雄心,他說:“敵人有的,我們要有;敵人沒有的,我們也要有,原子彈要有,氫彈也要快。管他什么國,管他什么彈,原子彈、氫彈我們都要超過。”1964年10月16日,中國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這顆原子彈不但彰顯了中國獨立于蘇聯的能力,也使美國不得不面對一個新的核大國已經崛起的事實。要知道,在冷戰時期,擁核才有大國地位,大國才能不被別國威脅和欺負。美國政府的第一反應是在盡可能地貶低其影響的同時,拒絕接受中國成為核俱樂部成員。約翰遜在當天發表的聲明中聲稱,中國的核試驗并不“出乎意料”,美國和西方國家會“認識到這種爆炸的有限意義”。但是,在美國政府內部不少人心里都明白,不管美國愿意不愿意,中國因為握有核武器而恢復在聯合國的席位和參與核裁軍等國際重要事務的談判,只是個時間問題了。手中握有原子彈,才能為昂首進入聯合國“五強”開道,這可是玩真的!順便提一句,中國原子彈爆炸成功,也使得蔣介石“反攻大陸”的美夢徹底破滅。因為沒有美國支持,“反攻大陸”想都不敢想。以前美國對蔣介石的忽悠還有點將信將疑。但大陸有了原子彈后,蔣介石的話就只能自說自聽了。原子彈在新中國手里變成了“真老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