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20世紀前蘇聯作家高爾基的評價,歷來存在著不同觀點的交叉,無論是在俄羅斯國內還是國外,也無論是在他生前還是死后。一個具有象征意義的現象是:高爾基的頭像,從他誕辰100周年紀念日起,就曾和普希金頭像一起,每周出現在影響頗大的俄羅斯《文學報》報頭上;但到蘇聯解體前夕,從該報1990年第18期(5月2日)起,高爾基頭像卻悄然消逝。類似的情形也發生在原俄羅斯聯邦作家協會機關刊物《我們同時代人》的封面上。
莫斯科的高爾基大街和伏爾加河畔的高爾基市也恢復了它們的原名:特維爾大街和下諾夫戈羅德市。一時間,高爾基在他的祖國,似乎真的像我國“十年內亂”期間一位大人物所說的那樣,要被“倒過來看”了。
可是,到了2004年4月22日,在《文學報》編輯部為創刊75周年而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主編尤里·波里亞科夫卻向與會者鄭重宣布:本報在廣泛征求讀者意見的基礎上,已決定從即將出版的新一期報紙起,在報頭上恢復高爾基的頭像。于是,從4月27日出版的《文學報》(第16期)開始,高爾基頭像在“退隱”了14年后又重新出現,繼續和詩人普希金的頭像并列;波里亞科夫本人為此而寫的專論《高爾基的回歸》也在頭版頭條發表。
值得注意的是,當時還健在,一向對高爾基持否定態度的著名作家索爾仁尼琴并沒有反對《文學報》的這一舉措。但假若編輯部要來我國征求意見,一定有人不同意,這么一個“沒有人性的御用作家”(金雁:《倒轉“紅輪”》(注:金雁為秦暉筆名),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109頁;以下引文僅注明頁碼),怎么還讓他和普希金一起,作為俄羅斯文學的象征,每周出現在報頭上?俄羅斯廣大讀者、文學界乃至“整個知識界”的良心到哪里去了?
如果真的能夠依據作家作品和文學史實,破解高爾基的生活、思想和創作之謎,使人們認識真正的高爾基,那無疑是《破解“高爾基之謎”》(《倒轉“紅輪”》第二章,以下簡稱《破解》)的一大貢獻。然而我們現在所看到的,不過是歷來歪曲、貶損、詆毀高爾基的種種言論的大匯集,當然還加上了作者的“合理”想象和發揮。人們不禁要問:這究竟是“破解”還是曲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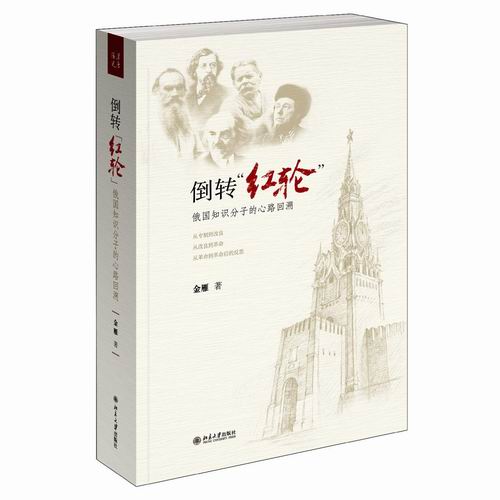
金雁著《倒轉“紅輪”:俄國知識分子的心路回溯》,2012年9月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一、1905年革命后,高爾基是否“迅速左傾化”?
《破解》斷言:1905年革命和1906年美國之行后,高爾基有一個明顯的“激進化”過程:他的創作方式和思想上發生了第一次突變——迅速左傾化,1907年以后“幾乎結束了文學創作”,成為“比列寧更為激進的‘極左’活動家之一”(69、73頁)。事實果真是如此嗎?
史料清楚地顯示,1905年革命失敗后,高爾基思索的重心是:作為一場重大的歷史事件,這場革命的發生、發展和結局,有無其內在的必然性?這一切同俄羅斯歷史文化傳統、民族性格之間是否有一種有機聯系?為了探明這些問題,他閱讀了一系列歷史和哲學著作,力求認識俄羅斯歷史發展的獨特性,捉摸到民族文化心理特點及其與民族命運之間的關系,探測未來歷史的動向。其中,克柳切夫斯基的《俄國歷史教程》關于俄羅斯民族和國家的特殊形態的描述,對于民族性格與民族歷史之關系的洞察,達尼列夫斯基的《俄羅斯與西方》一書關于俄羅斯與西方作為兩種不同的文化-歷史類型彼此之間存在著矛盾的論述,都對高爾基的社會-文化史觀的形成產生了直接影響。
通過閱讀和思考,高爾基開始感到研究民族文化心理的必要性,逐漸意識到民族精神特點和歷史進程之間的不可分割的聯系,提高民族精神文化素質是推動歷史前行的關鍵所在,而知識分子則是連接進步文化和人民群眾的紐帶。為著系統地認識俄羅斯歷史與民族文化特征,高爾基在1911年間曾籌劃出版“俄羅斯人民的歷史”叢書,嘗試以此提供俄羅斯人的處世態度和人生觀的歷史輪廓,顯示出民族性格形成與變化的歷史場景與條件。5月初,他曾寫信給俄國出版家伊·瑟京商談叢書的出版,后因種種外部條件的限制而未能實現這一構想。從對于沙皇專制社會的激烈批判轉向民族文化心理研究,這就是第一次俄國革命(1905-1907)后高爾基思想轉變的基本軌跡。這難道就表明他“迅速左傾化”?
《破解》斷言高爾基“迅速左傾化”的論據之一,是高爾基在卡普里期間與所謂“召回派”的接近。這是一種違背史實的曲解。當時俄國社會民主黨內部存在著列寧和波格丹諾夫等“前進派”之間的分歧和論爭,后者是1905年革命后布爾什維克隊伍中出現的一個人數極少的小派別,存在時間近5年(1909-1914),其本身又分為“馬赫主義”和“召回主義”。高爾基曾直言不諱地反對列寧和“前進派”之間的爭論,認為文化工作比政治斗爭更為迫切,后者應當讓位于前者,因此在1908年2月18日、1909年11月18日兩次給列寧寫信,對雙方都既有肯定又有批評,主張彼此團結一致,為推動俄國的發展盡力。基于同一心理動因,他還曾設想籌建一個介于右翼立憲民主黨人和左翼社會主義黨派之間的黨派,并與普列漢諾夫商討過此事。
當今俄羅斯研究者列維亞金娜正確地指出:高爾基的上述言論和活動表明,1905年革命失敗后,他在思想上“曾傾向于社會民主主義類型的社會主義,即社會主義與民主制的結合,重視社會主義理想在其發展過程中的歷史繼承性和人道主義化”(克爾德什主編:《不為人所能知的高爾基》,莫斯科,遺產出版社,1994年,第10頁)。高爾基的確曾與“前進派”成員有過不同程度的接近,但是,這就能說明他在1905年革命后“迅速左傾化”嗎?他究竟做了些什么,從而成了“比列寧更為激進的‘極左’活動家之一”呢?
《破解》還說高爾基在1907年以后“幾乎結束了文學創作而成為社會活動家”,這更是置文學史實于不顧,并為下一步斷言高爾基“不是知識分子”做鋪墊。文學史事實告訴我們:1907年之后,高爾基不間斷地完成了一系列作品。如果說,中篇小說《沒用人的一生》(1908)、《懺悔》(1908)和《夏天》(1909)顯示出他的創作從社會批判向民族文化批判的過渡,那么,包括中篇《奧庫羅夫鎮》(1910)、長篇《馬特維·科熱米亞金的一生》(1911)和未完成的《崇高的愛》(1912)在內的“奧庫羅夫三部曲”,則成為作家系統考察民族文化心理特征的最初藝術成果。作品揭示了外省小市民的生活秩序和傳統怎樣經由一代代人而繁衍和延續,觸及本民族歷史發展滯緩的某些基本根由。完成于這一時期的自傳體三部曲的前兩部《童年》(1913)和《在人間》(1916),不僅是作家本人早年生活的形象化錄影,更成為表現俄羅斯民族風情和文化心理的藝術長卷。含有29個短篇的《羅斯記游》(1912-1917),著力勾畫俄羅斯心理的若干特征和俄羅斯人的某些最典型的情緒。
由16篇故事構成的《俄羅斯童話》(1911-1917)則為國民劣根性及其在斯托雷平年代的顯現,提供了一組絕妙的寫照,正如這部作品的中譯者魯迅所說:“雖說童話,其實是從各方面描寫俄羅斯國民性的種種相”(《魯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第399頁);“短短的十六篇,用漫畫的筆法,寫出了老俄國人的生態與病情。”(《魯迅全集》,第8卷,第457頁)高爾基的《日記片斷》(1924)更是對于民族生活和文化心理特征的直接研究和如實寫生;《1922-1924年短篇小說集》(1925)及寫于20年代的多篇小說,已開始呈露出將民族文化心態同個人與民族的道路、命運結合起來思考的趨向。
以上六大系列作品,彼此連綴成民族風情、民族文化心理的生動藝術長卷,贏得了廣大讀者和無數批評家的好評,表明高爾基恰恰在此時進入了自己的創作高峰期。《破解》說高爾基在1907年以后“幾乎結束了文學創作”,根據究竟何在?
與上述形象化資料互為補充、彼此印證的,是高爾基在同一時期寫下的其他著述,如1908-1909年間于卡普里編撰的《俄國文學史》講稿,回國后陸續發表的《兩種靈魂》(1915)、《致讀者的信》(1916)等文章。從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作家思想和創作確實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決不是什么“迅速左傾化”。這位在20世紀初年曾以一曲《海燕之歌》熱情呼喚革命的作家,在第一次俄國革命后的暗淡年代里,并沒有繼續以高昂激越的旋律為另一場革命風暴的到來而吶喊,而是以清醒的寫實筆法繪制出一幅幅民族風情畫和民族心理素描。他在這一時期留下的文學批評和政論文字,同樣呈露出批判性地考察民族文化心理的傾向。1917年革命爆發后發表的《不合時宜的思想》,不過是1905年革命失敗以來作家的那些日漸成型的思想在歷史巨變時代的必然表現而已。
為了證明高爾基的“迅速左傾化”,《破解》還“杜撰”了俄國宗教哲學家別爾嘉耶夫“是1905年革命的參加者”、革命失敗后“高調懺悔”并“右轉”的“事實”,憑想象說什么高爾基的“左轉”和《路標》作者“右轉”成為“當時俄國思想界的兩件大事”,稱“已經出國的高爾基立即成為批判《路標文集》的第一人”,并“與知識界集體決裂”(72、73頁),用移花接木的手法把高爾基在1908年初寫成的《個人的毀滅》一文中的某些文字(引文錯誤甚多)說成是對1909年出版的《路標:關于俄國知識分子的論文集》的批判。
難道身在意大利的高爾基事先就看過了還未面世的《路標》全書?有意思的是,《個人的毀滅》中的一些批評象征主義作家、宗教哲學家梅列日科夫斯基等人的話語,竟被《破解》說成是對《路標》的抨擊;其實,梅列日科夫斯基本人就是最早批判《路標》的學者之一(寫有《七個被馴服的人》),另一宗教哲學家羅贊諾夫就寫過《梅列日科夫斯基反對〈路標〉》一文。還有,高爾基兩度撰文反對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群魔》搬上舞臺,不過是一位作家坦率地表達了自己的觀點,任何一位讀者或觀眾也有權這樣提出意見,而且高爾基一再聲明自己“不是反對陀思妥耶夫斯基,而是反對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長篇小說搬上舞臺”(高爾基:《論文學(續集)》,冰夷等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第185頁),怎么就成了“政治干預文學藝術”的事件呢?此事發生在1913年,作為流亡者的高爾基有可能在沙皇統治時代以此來“封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嗎?
請不要遮蔽以下史實:1935年1月20日《真理報》發表署名文章,指責蘇聯科學院出版社決定重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旨在反對革命的污穢的謗書”《群魔》具有某種政治目的,把大力支持這一出版計劃的高爾基稱為“文學的腐敗物”。高爾基隨即發表《關于〈群魔〉的出版》一文回擊該文的指責,重申堅決贊同再版《群魔》。《破解》怎么解釋這一現象?這是“左轉”還是“右轉”?
《破解》之所以做出上述種種判斷,原因之一在于作者所堅持的是以政治上的“左”和“右”來給所有人和事劃線的二元對立思維模式,無論什么社會、哲學、宗教、文學、藝術現象,統統都被放到在政治上“左”還是“右”的天平上去衡量。 二、高爾基是否是“賣身投靠權勢的看家犬”、“個人崇拜的奠基者”、“斯大林政治的傳聲筒”?
1928年以后,高爾基對斯大林、個人崇拜和極左政治的態度,是《破解》抨擊高爾基的主要著力點。該書說,高爾基“從海外歸來后就一頭扎進了肉麻吹捧斯大林體制的隊伍中”,成了“順從極權國家的衛道士”,“賣身投靠權勢的看家犬”,“斯大林制度的維護者”(65頁)。對極權體制、個人崇拜和極左政治深惡痛絕的善良讀者,如果不了解1928年以后高爾基做了些什么,看到這一頂頂拋給他的“桂冠”,怎能不恨透他、恨死他!
《破解》羅列了高爾基在1932-1934年間的一些文章和講話中有著“吹捧”斯大林之嫌的某些說法,緊接著寫道:“后來在1935年10月,季諾維也夫第一次把馬、恩、列、斯四個人的名字連在一起,從此產生了‘四大導師’的提法。所以說,高爾基是斯大林個人崇拜的奠基者一點也不過分。”(101頁)看到這段文字,人們不能不欽佩《破解》的超常推理能力;當然,這里的“季諾維也夫”如果能換成“高爾基”,那就更有說服力了。
事實告訴我們,1929年11月27日,亦即高爾基結束第二次回國訪問、返回意大利之后不久,便給斯大林寫了一封信,表達了自己對于國內正在發生的“大轉折”的看法。就在這一年,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等蘇聯領導人被打成“右傾投降主義集團”,不久后,布哈林便被開除出中央政治局,托姆斯基被解除了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主席的職務。所謂“反右傾斗爭”、“干部革命”等運動,也從這一年起開始席卷全蘇。針對這些現象,高爾基寫道:“在青年一代中間,遺憾的是,悲觀主義和懷疑主義情緒正在蔓延,而且那些最善于思考的青年也陷入這種情緒之中。
這些青年是從老布爾什維克的經驗、著作和言論中吸取營養的。現在他們卻看到自己的導師一個接著一個地脫離了黨,被宣布為異端分子———這不能不使他們感到不安……在對于青年的教育方面,黨的影響并不像它本來可以產生的那樣大,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黨內摩擦而造成的。”(《蘇共中央通報》,1989年第3期,第185頁)這里的“老布爾什維克”、“導師”和“老知識分子”,指的是那些在“干部革命”中被清洗的共產黨人。保存至今的高爾基檔案中,共留有這封信的4份草稿。在草稿之一中,高爾基這樣寫道:青年們把黨內矛盾“理解為兩個派別為了權力而進行的斗爭,甚至還理解為反對您的‘個人專制’的斗爭”(斯皮里東諾娃主編:《圍繞高爾基之死》,莫斯科,遺產出版社,2001年,第292頁)。由此不難看出,高爾基希望能夠阻止斯大林排除異己、迫害“敵對分子”的一系列行動。
一個無可回避的事實是:正是在30年代初,高爾基拒絕了給斯大林寫傳記。
1931年10月高爾基在蘇聯國內時,斯大林通過國家出版局局長哈拉托夫向高爾基轉達了自己的意愿,希望作家為他寫一部傳記。高爾基先是對此事采取了回避態度,后來則以缺少材料加以推脫。年底,哈拉托夫又寫信追問已回索倫托的高爾基:“我們已經給您寄去撰寫約(瑟夫)·維(薩里昂諾維奇)傳記的材料,請來信告知:您是否還需要什么材料,您打算何時將傳記交給我們。”(巴蘭諾夫:《火焰與灰燼》,伏爾加-維亞特卡書籍出版社,1990年,第307頁)高爾基立即就回了信,列舉出自己近期要盡快完成的十來件事情,唯獨避而不談為斯大林寫傳。
1932年,高爾基把給他寄來的有關斯大林的材料全部退回。高爾基為什么拒絕寫《斯大林傳》?《破解》沒有、按照其混亂的邏輯也無法做出任何解釋,僅僅用“意味著高爾基的利用價值已經完結了”(120頁;請讀者注意:這是在1931-1932年)搪塞過去。人們不禁要問:如果高爾基真的是“個人崇拜的奠基者”、“賣身投靠權勢的看家犬”,那么,為斯大林作傳,不正是“肉麻吹捧”、向領袖獻忠心的最好機會嗎?哪一個“仆人”會放棄這個求之不得的為“主人”效勞、歌功頌德的“天賜”良機呢?
《破解》還寫道:“斯大林想到了高爾基在《白海-波羅的海運河建筑史》中的‘創作’能力,便欽定由他來主編斯大林時代最重大的歷史學項目———多卷本的《蘇聯國內戰爭史》。”(115頁)這段話以及隨后的所謂“小說家編寫歷史”的說法,充滿著時序顛倒、概念錯誤和想當然的演繹。實際情況是,試圖利用高爾基的聲望,由他撰寫一部 《斯大林傳》,已經顯露出斯大林本人要掀起個人崇拜狂熱的端倪,當時蘇聯的一些趨炎附勢者對此心領神會,使盡渾身解數推波助瀾,以便讓斯大林如愿以償。《階級斗爭》一刊的主編波克洛夫斯基就是其中之一。此人曾約請高爾基為雜志創刊號寫一篇文章,強調斯大林在現代歷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以便為多卷本《國內戰爭史》定下基調。但是高爾基所寫的《人民應該知道自己的歷史!》(1931)一文,卻強調要讓勞動人民了解歷史真相,而且自始至終沒有一次提到斯大林的名字。
波克洛夫斯基抱怨此文缺乏與當代政治現實的聯系。這一事實,只是隨后不久圍繞《國內戰爭史》的編寫而發生的矛盾沖突的開端。高爾基明確主張,《國內戰爭史》叢書15卷的編寫,都應當從國內戰爭期間的歷史資料出發,尊重歷史真實,提供關于那一段歷史的真實圖景。但斯大林卻企圖利用該書的編寫夸大自己在國內戰爭中的作用,為自己樹碑立傳,這就難免使高爾基同那些力圖迎合斯大林意愿的編委們發生沖突。編委會成員布勃諾夫曾一再強調:講述斯大林在國內戰爭中的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高爾基卻堅定地重申:出版叢書的目的不是為了突出個人的作用,而是要展示歷史的進程。在考慮叢書各卷的具體內容時,高爾基指出:北方區、伏爾加河沿岸、頓巴斯、北高加索地區、西伯利亞和遠東等地區,都應當出分卷。但斯大林卻在高爾基的計劃外加上了外高加索、突厥斯坦、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等自己待過的地區,顯然是要突出和強調自己的地位。
高爾基一再提醒編委們不要“用我們的觀點強調”個人的作用(斯皮里東諾娃:《高爾基:與歷史對話》,莫斯科,遺產出版社,1994年,第263頁)。由于叢書主編高爾基的意圖和斯大林的意圖明顯地不一致,這套叢書的出版便受到了人為的阻遏。原定于1932年出版的《國內戰爭史》第1卷,一直拖延到高爾基去世后的1936年8月才得以問世。高爾基去世后,《國內戰爭史》叢書已無法繼續編輯出版,因為要按照尊重歷史真實的原則來編寫,就必然要提到“反對派”托洛斯基等人的名字,必然要提到后來被斯大林鎮壓的紅軍元帥和高級將領圖哈切夫斯基、艾德曼、布柳赫爾等人的名字,而這是斯大林絕對不能同意的。就這么一本集體編著,卻被《破解》說成“這部高爾基晚年嘔心瀝血的大部頭著作與《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齊名,成為斯大林時代兩大史學‘名著’”(116頁)。其捕風捉影的能力真令人驚嘆!稍有些俄國文學史常識的人都知道,高爾基晚年嘔心瀝血的著作是四卷本長篇小說《克里姆·薩姆金的一生》。
另一事實是,《白海-波羅的海運河建筑史》一書是原“拉普”要人阿維爾巴赫直接奉國家政治保衛總局頭目亞戈達之命組織編寫的。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強迫犯人在20個月內完成了這條運河的開挖。運河的每一公里、沿河的每一設施,都浸透了犯人的血汗。但亞戈達之流卻感到這正是炫耀自己功勞的好機會。1933年8月,他們組織了120多位作家參觀了剛剛建成開通的運河,并為《斯大林白海-波羅的海運河》一書寫稿。
高爾基并未去參觀,更未看到犯人開通運河的艱難過程,不了解強制性勞動的具體情景;即便是去參觀的作家們也未必都了解,因為他們到達時,運河已經疏通,死去的犯人已被掩埋。亞戈達一伙人一度成功地掩蓋了自己的罪行,造成了很大的欺騙性。去運河參觀并寫稿的作家們,有許多人本來是不愿意動筆的,只是亞戈達、阿維爾巴赫等人要用這些作家的名字來“裝飾”這本書,還一定要讓高爾基的名字出現在這本書的顯要位置上。亞戈達、阿維爾巴赫們策劃編寫這本書的目的,無疑是要為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功勛”樹碑立傳,為斯大林的極左政策唱贊歌,但是,高爾基卻沒有順從他們的意旨。
保存下來的編寫計劃表明,本來是指定高爾基撰寫一篇特寫“國家和國家之敵”的,但是他卻拒絕了,結果只為這本書寫了一篇序言,題為“社會主義的真理”。他在序言中肯定了被組織起來的人的精力戰勝了嚴酷的自然力量,稱贊那些參與修建運河的犯人們,并指出給他們恢復公民權利正是對于他們的有效勞動的一種報償。三個月前剛剛回國定居的高爾基,并無機會了解亞戈達一伙強迫犯人開挖運河的殘酷程度,并不知道這一工程實施過程中犯人的非人生活條件和工作條件。和參加撰寫本書的大部分作家一樣,他只看到了運河開通的奇跡般的結果,而未能看到達到這一結果的嚴酷過程,并在此種情況下對這種勞作方式進行了不無理想主義色彩的肯定與贊頌。他未能了解全部事實真相就寫出了這篇序言,當然不是無可非議的,但是他并沒有說違心的話。重要的是,這并不意味著高爾基對亞戈達一伙強制推行強迫性勞動的全部殘忍和反人道行徑表示認可,不能說明他認為當時的所有犯人在勞改營中所遭受的一切非人待遇都是他們應得的懲罰,更不意味著他贊同斯大林、亞戈達等人自20年代末期以來對于持不同政見者、知識分子和普通群眾施行的無情鎮壓。
此事發生在1933年8月之后,而《國內戰爭史》的編寫開始1931年,怎么可能是斯大林想到了高爾基編寫《白海-波羅的海運河建筑史》的“創作”能力,便欽定由他來主編《國內戰爭史》呢?明明是亞戈達、阿維爾巴赫之流組織作家去參觀運河的,怎么就成了“高爾基動員”的呢?“動員”之后他自己不去?
高爾基對待聯共(布)黨內“反對派”的態度,也表明他絕不是什么“斯大林制度的維護者”、“賣身投靠權勢的看家犬”。例如,1933年9月9日,在看過卡岡諾維奇寄來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之后,高爾基寫信給他說:“第57頁上稱托洛茨基為‘最可惡的孟什維克’。這很好,但是不是過早了?實際上不是過早,只是讀者可能會提出問題:‘最可惡的’怎么就不僅進入了黨內,而且還占據了黨的領導崗位呢?…… 我擔心,書中所提供的對于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布哈林及其他某些人的評價,同樣也會在讀者那里產生類似于關涉托洛茨基的問題。姑且不論,依我看來,這些評價其實是對以上諸人永遠關閉了黨的大門。”(斯皮里東諾娃主編:《圍繞高爾基之死》,第293頁)
緊接著基洛夫被暗殺之后出現的大逮捕,破除了高爾基的許多善良而脆弱的希望。他對于斯大林的個人專斷、極左政治的抵制,也不再像原先那樣一般采取勸導、調解、提意見的形式,而往往是直接表示抗議和反對。他并不隱瞞自己的思想情緒與斯大林的嚴重對立。他抗議對加米涅夫的逮捕和審訊,堅決反對并試圖阻止迅速蔓延全國的大逮捕、大處決,稱之為“國家恐怖”。據1934-1935年冬季和高爾基相見的莫羅茲回憶:“除了國民教育問題之外,高爾基對蘇聯政權的內外政策從沒有說過一句贊許的話。”(斯皮里東諾娃:《高爾基:與歷史對話》,第274頁)這一切同樣表明,高爾基從來就沒有成為“順從極權國家的衛道士”、“斯大林政治的傳聲筒”。
高爾基對“領袖至上主義”的抨擊,更有力地證明他不僅不是“個人崇拜的奠基者”,而且正是它的堅決反對者。
1933年,高爾基在一次談話中指出:“領袖至上主義是一種心理病癥,當自我中心主義擴展起來,它便像肉瘤一樣毒化、腐蝕著意識。患領袖至上主義疾病時,個人因素膨脹,集體因素衰竭。領袖至上主義無疑是一種慢性病,它會逐漸加劇……為領袖至上主義所困者,都患有好大狂,而在它背后便是如同黑色陰影般的迫害狂……”(巴蘭諾夫:《火焰與灰燼》,第327頁)曾在高爾基身邊工作的《我們的成就》雜志助理編輯伊·什卡帕回憶道,1934年間,有一次高爾基曾在自己家中談到普希金的小悲劇《莫扎特與沙萊里》,對其中的“天才和暴行,水火不相容”這句話十分贊賞。他說:“是的,天才和暴行是水火不相容的,因為天才是服務于集體的,他不會走罪惡之路!而暴行則是將自私自利奉為圭臬,是集體的不共戴天之敵。……真正的天才永遠是寬厚待人的!”(同上,第338-339頁)透過這些言論,不難看出高爾基對于個人崇拜和專制主義及其后果的警覺和反對。人類歷史上和現代社會中,哪一個“仆人”敢于針對正處于權力頂峰的“主人”發出這樣的聲音呢?
(未完待續)
相關文章
「 支持烏有之鄉!」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