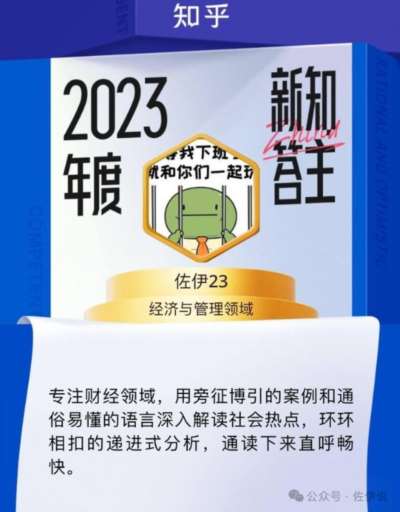非常開心能成為2023年知乎的新知答主。
感謝每一位陪伴的朋友!
我在知乎上面主要回答三類問題,經濟、歷史(社會)和哲學,這三類問題分別對應著政治經濟學、歷史唯物主義和唯物辯證法。2023年以來,這三類問題中,我回答最多的是經濟。并不是因為我最擅長經濟,而是我覺得經濟是最重要的。
很多關注社會的朋友,是從意識形態切入的,這誠然是一個好的切入點,但是,每一個意識形態的背后,都有它自身的經濟基礎。
80年代中前期,一位叫做張華的大學生因為救一名農民不幸身亡,此事被自由主義者抓住,引發了全社會的討論,“年輕大學生救一個農民值不值”。輿論一邊倒地認為,大學生的價值比農民的價值更高,不應該去救。無疑,這是一種扭曲的意識形態,但是這種扭曲的意識形態,恰恰是當時正在不斷瓦解的集體主義經濟的反映。
要理解這個社會,不能從這個社會的意識形態本身中去理解,而要從這個社會的一切經濟關系的總和中去理解。
辯證法告訴我們,任何一個運動過程,都有恰相對立的兩種趨勢。經濟運動也是一種運動,這種運動就是在恰相對立的兩種趨勢的對抗中得以前行的。集體的和個人的、資本的和勞動的、自由主義的和凱恩斯的等等,經濟之所以“動”,因為經濟本身就包含著促使其運動的矛盾。
以凱恩斯主義為例。
在自由競爭時期(1825-1870),市場體制的危機體現出明顯的周期性。這一時期的危機是典型的生產相對過剩的危機,資本無限擴張的欲望和有限的消費之間產生劇烈的沖突,資本自身有計劃的生產和全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呈現尖銳的對立。
1870年開始,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從自由競爭過渡到壟斷,危機的形態開始發生變化。從1866年開始,10年一次的危機規律就不復存在。一戰前德國展露出明顯的國家資本主義的萌芽。1929-1933年爆發的大危機,促使美國率先走上國家資本主義的干預道路。這表明生產力已經發展到這樣的程度,它激烈地反抗著“它的資本屬性”,要求資本的總代表(國家)“在資本關系內部可能的限度內”,最大限度地承認生產力的社會屬性,因此也要求資本的總代表直接干預資本再生產的整個過程。
二戰結束后,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紛紛進入了國家資本主義時期。自由競爭時期,國家不直接干預資本的再生產,僅僅作為資本的守夜人提供再生產所必須的外部條件。國家資本主義時期,生產力的發展在客觀上要求國家作為總的資本家,出面干預資本再生產的每一個環節,調節各部門比例。
國家壟斷時期,每一次出現相對過剩苗頭的時候,國家就通過積極財政和寬松貨幣相結合的方式,直接干預資本的再生產過程,進而干擾危機的展開。但是,它用以解決矛盾的手段,卻為矛盾的進一步深化埋下種子。它一方面刺激生產畸形擴大,另一方面造成資產價格畸高,從根本上削弱了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
在這個過程中,整個經濟付出的代價越來越大。這首先就體現為債務規模越來越大。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是以積極財政和寬松貨幣為主要手段的,也就是以公私債務不斷攀升為代價的。債務不斷攀升,還本付息的壓力日益增加,整個經濟中一個越來越大的部分被生息資本無償占有,企業和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日趨減少。通過凱恩斯主義進一步刺激經濟的余地不斷縮小。相互作用之下形成螺旋下降的惡性循環。
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凱恩斯主義有兩個明顯恰相對立的傾向,一方面,凱恩斯主義能夠緩和危機,另一方面,凱恩斯主義卻導致不斷攀升的債務、不斷高企的房價和不斷擴大而無處消耗的產能。這兩個趨勢的反復對抗,構成了凱恩斯主義本身的運動。
在這個運動的初期,負面的作用是次要的,但是隨著凱恩斯主義的深入,負面的作用不斷發生著量變,房價越來越高,產能越來越大,債務越來越多,一旦量的變化越過了某個臨界點,就會引發質的變化,之前共生的矛盾體就不能再按照既有的方式運行了。這就是凱恩斯主義的邊界。
列寧說過,理論工作的一個重點,就是具體地研究經濟中的一切對抗形式(即矛盾),研究它們的聯系和發展,“凡是這種對抗被政治史、法制特點和傳統理論偏見所掩蓋的地方,都應把它揭示出來。”
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真正地理解經濟,也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在理解經濟的基礎上真正地理解我們生活的社會。
知乎將我歸為經濟類答主,我覺得這是很恰當的。
感謝每一位陪伴的朋友,我會更加努力,為朋友們提供更多的優質文章。
「 支持烏有之鄉!」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