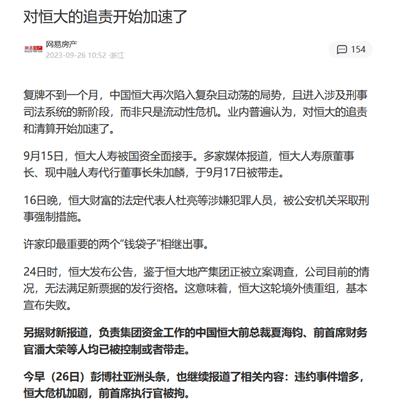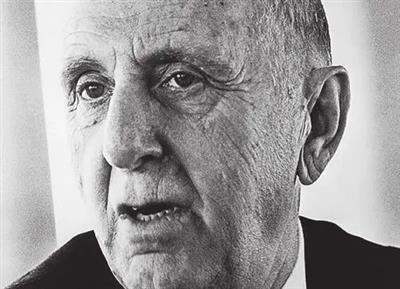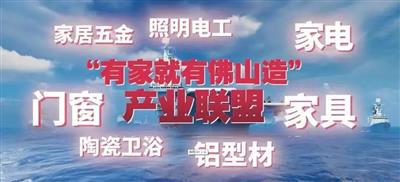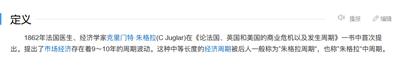從2021年下半年起,我們很多熟知房地產企業不少債務違約,股票腰斬或斬到了腳踝,破產或進入破產邊緣。拉開綿亙的暴雷名單,有藍光、新力、陽光城、奧園、富力、金科、世茂、遠洋集團……當然最重量級的還是昔日的民企地產行業的三巨頭:恒大,融創,碧桂園,他們帶著天量的債務規模躺平,最后讓全民為其買單。
遙想17-18年這些地產企業扶搖直上,正是風光無限時,頭部企業老板輪流做首富,股東也賺的盆滿缽滿,沒幾年就落了個轟然倒地的結局。
辯證法告訴我們,事物都不可能朝著一個方向永遠發展下去,遲早要遭遇來自對立面的否定,月盈則虧,蕭條的唯一原因就是繁榮;任何一個階段都不可能長期存在,到達某個臨界點之后就會朝著下一個階段的演進——人類階級社會的歷史隱匿于周期律的背后,大如國家都未必能跳出歷史周期,更何況是房地產企業了。
知所從來,方明所去。讓我們來經歷一遍98年到18年的周期,乃至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谷底,方能知道接下來要往何處去。
作為周期之母的房地產
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認,只要利用了資本,就不可避免的要面對資本的負效應,即我們必然要面對一個一個經濟周期。提出“庫茲涅茨周期”理論的經濟學家庫茲涅茨認為,現代經濟體系是一種持續,不可逆轉的變動,即“長期運動”。
而房地產就是“長期運動”的他媽(非罵人),從邏輯上,資本主義的長周期(康德拉季耶夫周期)開啟的根源是由技術革命帶動新一波的擴散,催動著廠房與設備更新,現實增長除了作為技術革命的主導產業外,其增長的最核心載體還是房地產周期(也叫庫茲涅茨周期)。
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
庫茲涅茨
為什么是康波里的核心載體呢?這里可以聯動一下政治經濟學,在所謂的上升期將剩余價值投入到基建和地產為代表的固定資產中是常見的修復手段——把工廠、住宅、交通網連接起來,使城市不斷延伸,農業人口不斷轉移,商品消費普及化,資本才得以再生產。
房地產最初的本質是制造業。它的產業鏈、供應鏈非常綿長,上游到水泥、鋼材、玻璃、化工、木材、工程機械,下游到地板、瓷磚、涂料、門窗、潔具、裝修、家電、家居等共計500個行業。舉個例子,我國東部和沿海一些鼎鼎有名的制造業城市,這么多年產業結構和房地產都有密切的關系,能拿的出手的制造企業基本都參與了房地產上下游。
這些制造業的產能隨著買房需求暴增,一榮俱榮,反過來也會吸引大量資本進駐房地產,然而房地產是一個時間周期很長的行業,開發商從買地,到開發,到在所有新的房地產項目竣工,進入銷售市場之前,要再經歷十年時間,這個時候往往會借助虛擬資本,當流程全部完成的時候,市場供給可能已經過剩了,普遍出現過度投資這一現象。
經濟波動的風險以及建筑環境內過度積累的資本問題會變得十分突出。資本往往通過全球不斷占領新的空間和人口市場,緩解自身過度積累的危機。這樣,危機就會向全球結構加深和擴大。
主流經濟學框架(新古典、新自由主義)很難解釋周期更迭而導致世界結構變動,相反人們發現周期運動和傳遞,與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論十分契合(見我們以前相關文章《美國工廠》)。在世界體系里,房地產周期會從中心國家—中心附屬國—半邊緣追趕國—邊緣資源國家依次傳遞,以我們身處的時代來說,自上世紀90年代初,中心國家—美國開啟資本主義長周期第二輪的房地產周期,到90年代末擴散到了作為追趕國的中國。
沃勒斯坦
中國從1998年啟動了房地產貨幣化改革,有了商品房的概念,這是一個周期的開始,是為復蘇期。前面我們提到了,房地產周期是其他周期他媽,這一波地產投資+城市化大躍進孕育出了一個產能周期(朱格拉周期),持續七八年之久,期間出口規模增加(彼時美國進入了房地產繁榮期,這是對當時美國互聯網股市泡沫危機的轉移),制造業投資擴張,設備加速更新換代,也就是所謂入世的“黃金年代”。
直到07年泡沫徹底破滅,次貸危機席卷全球。為了應對這次資本主義危機,中國08年開啟了全國范圍的棚改,開啟了大規模的基建投資浪潮,通過消耗全球60%的銅礦和一半的鐵礦石和水泥,挽救了大宗商品價格,將眾多的邊緣資源國拉出了經濟崩潰的局面。在國內,此舉試圖將東部沿海的工業區與內地建立交通網,把高速路修進西南大山,同時加強了南方與北方消費市場的關聯,房地產周期進入繁榮期。
從房價上,從08年以來就一路高歌猛進,在13年達到小高峰,房屋新開工面積年度累計值在2013年底達到峰值,到達了繁榮的頂部,但到了2014-2015年卻逐漸下落,也就是在這時候我國房地產周期進入了衰退期。
14年后,資本過剩,新增GDP的多數是固定資本,結果卻導致增長率下滑,土木人、冶金人、機械工程人的日子從這一年開始逐漸不好過了,隨著14年中國經濟增長的放緩,大眾商品價格下跌,巴西、智利、厄瓜多爾等眾多邊緣資源國的經濟也產生了混亂。
回過頭來看,08-13是房地產最火的五年,但為什么是15-16年反而給人感覺房價還在大漲,地產商仍舊風風光光,看得人牙癢癢?那會房價增速加快,與去庫存大政策以及棚改貨幣化直接創造了大量二三四線城市購房需求有關,兩套操作導致二三四線城市普遍上漲,影響傳導到了占多數的中國人,給人房價永遠漲的錯覺。但實際上16年開始的房地產,出現了大量炒家,同時金融機構大范圍收購不良資產并全面進場。也正是在房地產周期衰退期,金融機構主要盯上了居民的六個錢包和負債能力。
這時候,上面還布局了“去杠桿”,對地產這種資金密集型企業來說,去杠桿=蕭條。等2017年末宣布去杠桿接近尾聲時,中小房企已經出清的差不多了。17年底實際已經進入房地產周期的蕭條期。
當周期落幕之時
按照庫茨涅茲周期的規律,一開始是從房租上漲開始,帶動了房價上漲,貸款意愿增加,信貸反過來刺激了新建房屋數量增加,新建房屋便又吸收了閑置的土地。經濟熱度與人的情緒相互作用,消費者往往高估了自己的還款能力,急著貸款上車。開發商因為房價上漲,提升風險偏好,不再滿足于搞幾個精品樓盤,于是開始向多業態,更多的一線房企進入二三線城市大量囤地,像碧桂園與綠地就在這些城市極速擴張,各個新城區拔地而起,“高周轉”就是這會玩出來的。
這個時期房價上升,城市人口也在上漲,于是資方和管理者都建立了樂觀的人口預測。工業生產的產能正在努力跟上需求的增長又建設了新的產能,這里又不得不說,既然明白凡是皆有周期,如果在固定資產欣欣向榮,高速增長的時候推出財政換錨、分配的改革,那么未來的增長預期也許很大程度抵消轉軌的波動——然而現實則是,沒有幾個經濟體在景氣周期能做到未雨綢繆的,能不寅吃卯糧就不錯了。
當房價過高,超出了大家的承受能力,房子也就達到頂峰(13、14年),需求降低,購買力下降,導致房屋滯銷。這個時候政策相應推出了去庫存和棚改貨幣化安置,本身是可以為地產業開了一個逃生通道,但很不幸,仍然很多資本想投機,把這個逃生通道當成了舞臺。
也就是說16年之后,頭部房企們杠桿一路不停拿地、蓋房,維系虛假繁榮,按照以往的庫茨涅茲周期,衰退期加杠桿,當十幾萬億的債務資金堆砌起來的泡沫,無監管地走向蕭條期,絕不是溫柔地走入良夜,會從國有銀行開始,最終給社會帶來系統性金融風險。
不過此之后樓市依然堅挺,并不像很多典型資本主義經濟體那樣走過了一個完整的庫茲涅茨周期(對比加息背景下的香港、韓國、東南亞諸國的樓市)。很大原因在于19年中央出臺的“三道紅線”,此時危機就像“無痛人流”般,在人為控制下進行“衰退”。
周期確實落下來了,很多房地產商在紅線下被嚴控貸款,后續資金乏力,走向低迷,為房地產配套的建筑材料、裝飾裝修、白色家電、五金交電、運輸物流、機械制造、鋼材木材、鋁合金等就一起低迷。
當然,這里不是在復讀“房地產壓艙石、大不能倒”這種陳詞濫調,真正的的問題往往在于周期早期,在繁榮期,資本積累導致了資產和收入不平等的擴大,伴隨著房地產市場的活躍和房價上漲,富人能夠通過投資房地產獲得更多的收益(我國收入基尼系數的高峰出現在房地產進入繁榮期08、09年),故而分配不均在經濟周期的頂峰階段是十分顯著的。后來人看到的是地產以及起上下游的生死,看到發財機遇,卻難看到財富分配格局和房地產周期興衰是高度相關。
周期是無法回避的現實,在繁榮期,我們往往逃避面對的問題,而到了蕭條期,則終以危機消滅資本。眼下恰逢“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即一個康波周期的谷底(互聯網等新技術紅利消失),再加上全球霸權更替,我們沒有時間沉浸在對高速增長逝去的緬懷中,而是應該努力擺脫這一看似“必然”的歷史周期。
「 支持烏有之鄉!」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