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問題的由來
被尊奉為“日本理論經濟學第一人”的宇澤弘文,在其著作《像經濟學家一樣思考》中,提出了一個奇葩觀點:不是“勞動決定價格(價值)”,而是“價格(價值)決定勞動”。這個觀點之所以奇葩,就在于這位日本教授的論證過程和論證邏輯,很奇葩:
“在亞當·斯密所著的《國富論》中曾舉過一個著名的例子說明價格形成的原理。假設獵人射殺一只鹿需要4個小時,而射殺一只海貍需要8個小時。這時一只海貍的價值就是一只鹿的兩倍,海貍的自然價格就是鹿的兩倍。這是斯密所謂的生產費用論(cost of production theory)。我們需要注意的是,為什么獵人會選擇付出捕獵鹿兩倍的時間去捕獵海貍呢?原因就是海貍的價格是鹿的兩倍。如果海貍的價格低于鹿的兩倍,獵人們就會放棄捕獵海貍而選擇獵鹿;相反,如果海貍的價格高于鹿的兩倍,那么獵人們會放棄獵鹿而選擇捕獵海貍。因此,不是勞動投入量決定價格,而是價格體系會決定勞動的投入量。一只海貍的價格可以匹敵兩只鹿,難道不是因為一只海貍的價值相當于兩只鹿的價值嗎?”【1】
這個出自于《像經濟學家一樣思考》的“獵人故事”,引起了馬政經專業某博士的極大興趣。在轉發了宇澤的這段奇葩語錄之后,他附上了一句評語:“宇澤的問題問得好,但回答得不好。”老師問:“你知不知道他錯在哪里嗎?”回答:“老師,他把本質的東西和表象的搞反了,有一定迷惑性,沒把我迷惑住[捂臉][捂臉]” 老師說:“你沒被迷惑,值得點贊。用‘本質和現象’回答固然沒錯,但只具有抽象的‘政治正確性’。你并沒有講清楚其中的道理,所以什么都沒有回答。”
為了搞清問題,趙磊老師召集馬政經專業的同學進行了線上討論,于是有了下面的發言【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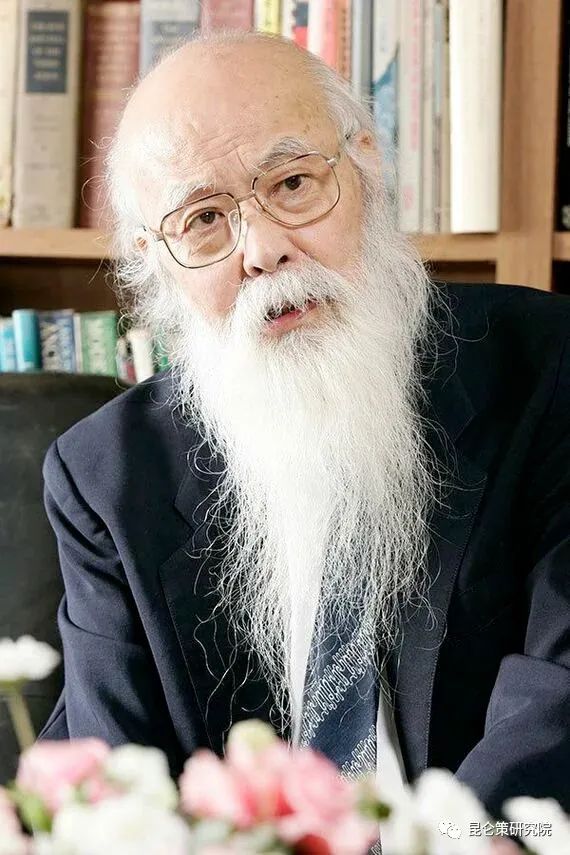
【宇澤弘文(1928-2014)】
一、肖華堂:獵人為什么愿意捕獵海貍?
宇澤的觀點是我推薦的,我先談談自己的看法。
宇澤弘文說,“我們需要注意的是,為什么獵人會選擇付出捕獵鹿兩倍的時間去捕獵海貍呢?”價格是給定的,獵人選擇捕獵鹿抑或是海貍,主要根據“價格”來進行選擇,否定了勞動價值論。
但宇澤同時追問:“難道不是因為一只海貍的價值相當于兩只鹿的價值嗎?”結合上下文,作者又似乎是承認勞動價值論的科學性的。
宇澤引用亞當·斯密的舉例,指出“獵人射殺一只鹿需要4個小時,而射殺一只海貍需要8個小時。這時一只海貍的價值就是一只鹿的兩倍。”因而,這里,作者首先將價值(本質)和價格(表象)混淆,同時在闡述自己的觀點上也前后矛盾。
關于“為什么獵人會選擇付出捕獵鹿兩倍的時間去捕獵海貍呢?”我的理解是,其一,鹿和海貍對人們來講都有需求,都能滿足人們的某種需要,即有用,人們才會花時間去捕獵,這一點說明獵人為什么要去捕獵鹿或者海貍。
其二,從事實上看,獵人捕獵海貍和捕獵鹿需要的技能、付出的體力等不同,獵人自身捕獵技能等方面也不同(捕獵海貍和捕獵鹿的能力不同,或者說是偏好不同)。
其三,約束條件,從人的因素來看,每個獵人的時間都一樣(24小時),捕獵海貍和捕獵鹿需要的時間不同,需要付出努力不同,不同獵人根據個人能力他們會進行選擇;從自然因素來看,當捕獵鹿的人增加,鹿的數量就會減少,捕獵鹿的難度會增加,部分獵人會轉而捕獵海貍,反之同理,這里也有機會成本的問題。
其四,價格的問題,從某個固定時間來看,鹿和海貍呈現出特定的價格,某種意義上會引導新的潛在獵人在捕獵海貍和捕獵鹿之間進行選擇,當然,如果海貍的價格高(高出鹿的價格的2倍),會有更多的人去捕獵海貍,這樣自然中海貍的數量會減少,市場上的數量會增加,同時人們消費海貍的數量會減少(海貍價格高了),但與此同時,捕獵海貍的難度會增加,幾種因素相結合,捕獵海貍的人就會減少,反之同理。
綜上,“獵人會選擇付出捕獵鹿兩倍的時間去捕獵海貍”,不僅是“價格”的因素,價格只是最終呈現出的某種結果,不是原因,價格更不等于價值,呈現出的“獵人選擇付出捕獵鹿兩倍的時間去捕獵海貍”是一種自然選擇的過程。
二、趙磊:宇澤設下了一個陷阱
我點評一下肖博士的發言。
肖博士始終被一個問題所困擾:為什么獵人愿意多花時間去捕獵海貍?一番琢磨之后,他的答案一言以蔽之(也就是他的第四點):因為必須多捕海貍,供求才能實現平衡。
如果肖博士的任務,是在論證價格機制的調節作用,那么他的回答沒錯。然而肖博士面臨的任務,本來應當去分析宇澤的奇葩邏輯究竟錯在什么地方,而不是去重復斯密的“分工理論”。盡管肖博士提到了“本質與現象”,并在最后蜻蜓點水地說“價格更不等于價值”,可是他所花的功夫,幾乎全部都用來證明宇澤的“獵人故事”中隱含著斯密“分工理論”的正確性。
很遺憾,肖博士被宇澤的奇葩邏輯帶進溝里去了。
我要告訴大家,宇澤的這個“獵人故事”,它的要害是“價格變動在先”。根據“價格變動在先”的原則,宇澤得出結論:因為“價格變動決定了勞動量變動”,所以不是“勞動決定價格(價值)”,而是“價格(價值)決定勞動” 。
——我還要提醒大家注意,宇澤把價格與價值攪拌成了一鍋漿糊。在他的“獵人故事”里面,一會兒“價格”,一會兒“自然價格”,一會兒“價值”,其“翻臉不認人”的速度,比川劇“變臉”還要驚悚。經過這番“變臉”,價值和價格黏在一起,成了一個東東。這種“變臉”加上“攪拌”,歷來是西方經濟學酷愛的烹飪技術。如無特別說明,我在下面討論中所使用的也是“變臉”之后的價格和價值。
宇澤憑什么被尊奉為“日本理論經濟學第一人”?我不知道,但他搗糨糊的水平確實是超一流的。有“獵人故事”做先鋒,宇澤信心爆棚地以為自己輕而易舉地駁倒了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
可惜我們的肖博士,卻被宇澤的“獵人故事”牽著鼻子走,從此樂此不疲地陷入“為什么獵人愿意多花時間去跟海貍較勁”之類的偽問題中,冥思苦想而難以自拔。
為啥“獵人愿意多花時間捕獵海貍”?這是宇澤給肖博士挖的大坑,設下的陷阱!宇澤想用“價格變動”引起“供給增加”的邏輯,來否定勞動價值論。可是“日本理論經濟學第一人”又遮遮掩掩,說半句留半句,還故作“神龍見首不見尾”的神秘狀——貌似喝了幾瓶清酒,最后假裝醉醺醺地問“一只海貍的價值相當于兩只鹿的價值嗎?”
宇澤的整個心思,就是西方經濟學慣用的搗糨糊邏輯,是典型的胡攪蠻纏。
搗糨糊有個好處:既然端上桌的是一鍋漿糊,那就讓讀者自己去猜漿糊里面是什么。讀者越猜就越糊涂,越是糊里糊涂,就越能說明搗糨糊的人有水平,是“日本理論經濟學第一人”。
宇澤教授要的就是這個效果。
可是,你一個馬政經博士怎么能跟在這個日本人的屁股后面轉圈圈呢?你的問題導向,不應該是論證“獵人的選擇完全符合斯密的分工理論”;你的問題導向應該是,這個“日本理論經濟學第一人”得出的奇葩結論,究竟錯在哪里?
很遺憾,雖然你在發言中象征性地點了一下“本質與現象”,最后還給出了“綜上”的總結,但基本上是“王顧左右而言他”,并沒有回答“究竟錯在哪兒”這個要害問題。
恕我直言,如果你對《資本論》的興趣也能像對宇澤的“獵人故事”這么強烈,或許就不會跳進日本人設下的陷阱,更不會在掉進陷阱之后,還無比興奮地轉圈圈了。
三、趙磊:價值是不是“先驗”的東東?
我接下來討論宇澤邏輯的錯誤所在。
在宇澤的“獵人故事”中,獵人在作出打海貍還是打鹿的決定之前,先要看這些動物的價格(價值)高低。如果鹿的價格高,就打鹿;如果海貍的價格高,就打海貍。
宇澤用“獵人故事”告訴大家:看見沒?勞動投入跟著價格走,價格機制調節著我們的勞動,所以并不是“勞動決定價格(價值)”。
宇澤的這個邏輯,看起來好像是那么回事,其實荒謬絕倫。那么,這位“日本理論經濟學第一人”的邏輯錯在哪兒呢?
現在我劃重點:宇澤的邏輯錯誤,就在于他把價格(價值)當作了一個“先驗存在”的東東了!
什么叫“先驗”?所謂先驗,就是宇宙大爆炸伊始,隨著“轟”的一聲巨響,價格(價值)就從天降臨。換言之,在商品交換尚未發生之前,就有一個被稱作“價格”(價值)的黑洞事先矗在那里了。換言之,價格(價值)先于交換過程,先于交換實踐。一言以蔽之,價格(價值)先于人類的一切交換實踐和交換經驗。
從“獵人故事”中,這位日本學者炮制出一個神邏輯:在交換發生之前,價格(價值)就已經被事先規定好了,是事先計算出來的寶貝兒——至于誰計算出來的,那是上帝的工作,爾等沒資格過問。
總之,在交換關系尚未出現之前,價格(價值)事先就威嚴地矗在那兒,早就等著獵人們去跪拜了。
同學們看看宇澤的邏輯:自從盤古祖爺爺開天辟地以來,價格(價值)就已經供在神龕上了:海貍每公斤100元,梅花鹿每公斤50元……。根據這個盤古祖爺爺傳下來的寶貝兒,獵人們才能決定自己該捕獵什么,不該捕獵什么。這不就是把價格(價值)當做一個先于交換就存在的東東了嗎?也就是說,在交換過程進行之前,在交換實踐展開之前,有一個先在的、先驗的價格(價值)在天空中飄啊飄……如同上帝一樣向各位招手。
那么,價格是不是“先驗的東東”呢?同學們,對不起,NO!NO!NO!
我寫過一篇文章,不知道同學們讀過沒有?這篇文章的題目是:《馬克思的價值范疇何以客觀?》(載《社會科學輯刊》2020年第3期)。
在這篇文章中,我對于那些把價值當作先驗存在的謬論,進行了批判。這個批判不是我的“首創”,馬克思之前就已經做過這樣的批判。
宇澤把價格(價值)當做先驗存在的東東,先于交換就存在的東東,這不過是他的幻覺罷了。這不僅是他的幻覺,而且是很多庸俗經濟學家頭腦里的幻覺。你們聽聽著名海龜某某教授的高論(高論內容省略),就有這類強烈的幻覺。其實在高校,但凡是信奉西方經濟學的教師大都有這樣的幻覺——雖然他們嘴巴上不說,甚至在文章里邊也不這樣寫。
所以,我建議同學們好好讀讀《馬克思的價值范疇何以客觀?》。在這篇文章中,我批判了把價格(價值)當作“先驗東東”的觀點,結論是:價值不是先驗的,它是在交換過程中,在交換實踐中,即馬克思說的“社會過程”中形成的,它不可能先于交換實踐和交換過程。
我曾經遇到過這樣的經濟學教授,他們堅信,價格(價值)之所以是先驗的東東,是因為它可以用數學模型在書房里面事先計算出來。因此,對于馬克思的“價值”不能用數學模型事先計算出來這件事情,他們非常非常生氣,從此以后就跟馬克思拉下了仇恨,并宣布與勞動價值論不共戴天。
這種堅信價值可以用模型計算出來的“信仰”,比起那些把價值視為上帝決定的觀點,其實也好不到哪兒去。關于這類“信仰”的荒謬之處,我不展開分析了。如果哪位同學也有這樣的“信仰”,建議他去讀讀《馬克思的價值范疇何以客觀?》(載《社會科學輯刊》2020年第3期)。
那么價格(價值)為啥不是先驗的東東?我在下面著重討論幾個與此相關的問題。這些問題涉及理論分析可能會多一些,希望能促使大家做一些認真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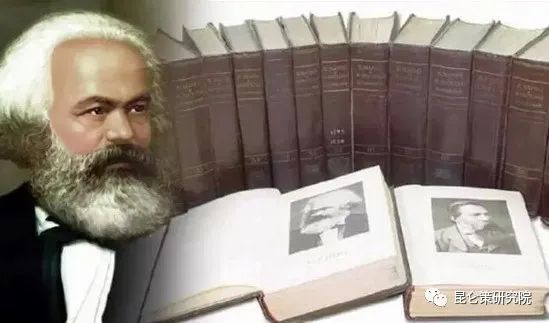
四、趙磊:“價值決定”是否真實?
在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中,價值是由勞動決定的。馬克思把“勞動決定價值”的過程簡稱為“價值決定”。在馬克思看來,價值之所以不是什么“先驗的”東東,就在于“價值決定”的過程是一個離不開經驗的和實踐的過程。
“價值決定”并不是馬克思臆想出來的過程,而是一個真實的過程。既然是一個真實過程,那么它就是一個“先于”理論描述的客觀過程。事實正是這樣:“價值決定”的真實過程先于“價值決定”的理論分析,馬克思把“價值決定”的真實過程定義為“社會過程”。對于“價值決定”的“社會過程”,馬克思用科學語言進行了這樣的描述:
“商品的價值量與實現在商品中的勞動的量成正比地變動,與這一勞動的生產力成反比地變動。”
雖然人們直觀看見的,只是“價格計量”的具體過程(即市場供求變化引起商品價格漲落),而并不是“價值決定”的具體過程;但是,馬克思從交換實踐中抽象出來的“價值決定”的“社會過程”,是一個遠比現實經濟活動中“價格計量”更為本質的,且完全真實的歷史過程。
“價值決定”的“社會過程”的真實性和客觀性在于:雖然“社會勞動時間決定商品價值”與價格漲落不可能一一對應,但是,“價值決定”的內在法則(即“勞動決定價值”)規定了價格漲落(即“價格量化”)的比例原則。
簡而言之,價格量化的“比例”(也就是宇澤“獵人故事”里面海貍和鹿的價格波動)并不是人們頭腦里事先設計并計算出來的某種先驗的比例,而是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貫徹“價值決定”的客觀結果。
五、趙磊:“價值決定”先于商品經濟活動嗎?
對于“價值決定”的客觀性,庸俗經濟學搗糨糊的思維方式壓根兒就不能理解。
“價值決定”不是經濟學的計算題,不是數理模型的主觀構想,而只能是“社會過程”的實踐結果;“價值決定”以及簡單勞動與復雜勞動的換算比例,絕不可能 “先于”商品經濟活動和實踐而存在。
換言之,商品生產、市場交換的實踐活動與“價值決定”是同一過程的兩個方面,“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商品價值”絕不可能先于簡單勞動與復雜勞動的換算比例而存在。馬克思說得好:
“首先很清楚,對商品價值的估計,例如,用貨幣來估計,只能是商品交換的結果,因此,如果我們把這種估計作為前提,我們就必須把這種估計看做商品價值同商品價值實際交換的結果。”
為什么有人會把“價值決定”誤解為經濟學的計算題?因為從“邏輯先在”的角度講,“價值決定”似乎應當是一切商品交換的前提——價值確定好了之后,再進行商品交換。但是從實際過程看,或者從“事實先在”的角度看,“價值決定”的真實過程則是這樣的情形:(1)“價值決定” 必須借助于價值形式(比如貨幣)才能實現;(2)“價值決定”是商品交換的結果,而不是商品交換的前提。
事實很清楚,“社會過程”與“價值決定”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對于“價值決定”的“社會過程”,馬克思有過極為深刻的論述:
“比較復雜的勞動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說多倍的簡單勞動,因此,少量的復雜勞動等于多量的簡單勞動。經驗證明,這種簡化是經常進行的。”“各種勞動化為當做它們的計量單位的簡單勞動的不同比例,是在生產者背后由社會過程決定的,因而在他們看來,似乎是由習慣確定的。”
馬克思這里強調的“經驗證明” “經常進行”“習慣決定”,其實就是億萬次商品 生產與交換的經驗過程。馬克思所說的“社會過程”絕不是憑空虛構的“先驗”過程,而是一個有億萬人參與其中,并經過億萬次生產與交換的實踐過程,因而是一個具有客觀實在性的過程。
可見,雖然“價值決定”是馬克思作出的理論抽象 但是“社會過程”卻為馬克思的理論抽象提供了真實的客觀依據。正因為“價值決定”是一個有著充分的實證依據和可重復的經驗證明的“社會過程”,所以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絕不是沒有客觀依據的臆想,而是科學的理論。
六、趙磊:有沒有“先驗”的價格?
有人不干了:
“趙老師,你說價值或價格不是先驗的東東。可是我到超市去買商品,價值或價格事先就擺在那里了。對我來說,價值或價格就是先驗的存在嘛!”
沒錯,在絕大多數具體的交換過程中,的確是有個價格先放在那里,而不是你先去跟商家博弈出一個價格,然后再去交換。對此,我在《馬克思的價值范疇何以客觀》那篇文章里,專門做了分析。
總體上講,“價值決定”(包括簡單勞動復雜勞動的換算過程),只能在商品經濟生產和交換的實踐過程中實現。但是對于個人的具體交換行為而言,“價值決定”卻往往先于個人的經驗而存在。比如說你去買方便面,康師傅五塊錢一包,價格事先就掛在那兒了。對于你個人而言,“價值決定”似乎具有先在性或者先驗性。
然而,你不能拿這個所謂的“先在性”來否定“價值決定”的經驗性和實踐性。你在超市面對的康師傅價格(價值),是經過了億萬次商品生產、億萬次商品交換的實踐檢驗,最后才被大家確定下來,才具有了“公理性”(先驗性)。
對個人而言,對于肖博士而言,對于趙老師而言,在交換之前,康師傅的價格(價值)似乎是一個先驗的存在。但是,你不能用價值的這個所謂“先驗性”,來證明價值就是先驗的東東。為什么呢?因為任何商品的“價值決定”,包括你買的康師傅方便面,都是通過千萬、上億次的商品生產實踐和商品交換實踐,通過比較、碰撞、檢驗、博弈、反復,然后才形成了所謂的“先驗性”。何況這個“先驗性”并不是固定不變的,還在不斷的變動之中。
總之,對于個人的具體交換行為而言,“價值決定”往往會先于個人的經驗而存在,似乎具有“先驗性”。但是,任何商品的“價值決定”以及簡單勞動與復雜勞動的換算比例,是不可能先于商品經濟的生產和交換實踐的。
所以我有必要強調,“價值決定”對于個人而言看似具有“先驗性”,但是這樣的“先驗性”仍然離不開生產和交換的經驗過程,它是經過了億萬次商品生產和交換實踐的檢驗,從而獲得的“公理性”。正如列寧所說:
“人的實踐經過億萬次的重復,在人的意識中以邏輯的式固定下來。這些式正是(而且只是)由于億萬次的重復才有著先入之見的鞏固性和公理的性質。”
無論如何,“價值決定”必須形成于人的社會實踐過程之中。人的社會實踐不僅僅是某些人或者某個人的實踐,而是人類的總體實踐,是億萬次實踐反復驗證的結果。“價值決定”背后的社會過程和社會實踐,就是價值以及勞動價值論的客觀依據之所在。
七、趙磊:桑巴特的評價
最后我再補充一下。庸俗經濟學的前人以及傳人,一邊指責馬克思的價值范疇是“主觀臆想”,一邊卻無視“價值決定”的客觀依據。這恰恰證明他們根本不懂得唯物辯證法。
這讓我想起了恩格斯的一段論述。針對以價值與價格“不一致”來否定勞動價值論的觀點,恩格斯正面引述了桑巴特對勞動價值論的評價:
“價值在按資本主義方式生產出來的商品的交換關系中不會表現出來;價值在資本主義生產當事人的意識中是不存在的;它不是經驗上的事實,而是思想上、邏輯上的事實,在馬克思那里,價值概念按其物質規定性來說,不外是勞動的社會生產力構成經濟存在的基礎這樣一個事實的經濟表現;價值規律最終支配著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下的經濟過程,并且對這種經濟制度來說普遍具有這樣的內容:商品價值是最終支配著一切經濟過程的勞動生產力借以發揮決定性作用的一種特有的歷史形式。——以上就是桑巴特的說法。”
桑巴特說,“價值在按資本主義方式生產出來的商品的交換關系中不會表現出來”,這并不符合馬克思的原意(此處不展開討論)。但是,與那些把“價值決定”等同于“價格量化” 的庸俗經濟學家相比,桑巴特對價值的理解已然非常深刻。
注意,所謂價值“不是經驗上的事實,而是思想上、邏輯上的事實”,是指人們不能一目了然地直接看到價值,人們直接看到的只是價值的表現形式(或者價格)。然而,價值“不是經驗上的事實”,并不意味著價值不能在經驗上得到證明,更不意味著價值是馬克思虛構出來的范疇。
只有理解了馬克思“價值決定”的邏輯,你才能看見宇澤的“獵人故事”的邏輯究竟錯在哪里。
八、張國毅:宇澤的結論是“倒果為因”
宇澤的假設是“倒果為因”的一個很好的例子。
獵人得到一只鹿需要勞動4小時,同樣地,得到一只海貍需要勞動8小時。此時,作者也承認,一只海貍的價值是一只鹿的價值的兩倍,所以一只海貍的價格也是一只鹿的價格的兩倍。作者說這是斯密的生產費用論,這里的費用應該是勞動時間的耗費。前面說的應該就是較為樸素的勞動價值論的思想。
這里說一句題外話:斯密是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代表,他的思想其實就體現了一定程度的勞動創造價值的思想。只是后來的新古典綜合派用“邊際革命”取代了勞動價值論,然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脫胎于古典政治經濟學,繼承和發展了勞動價值論。說這句題外話的目的就是想表明,勞動創造價值思想的源頭不是馬克思,至少在被稱為現代經濟學之父的亞當·斯密那就已經有了。
接著前面的說,一只海貍的價值是一只鹿的價值的兩倍,進而一只海貍的價格是一只鹿的兩倍,這是結果。其原因在是,得到一只海貍需要付出的勞動時間是得到一只鹿的勞動時間的兩倍,此時,一只海貍的交換價值就表現為兩只鹿。
文中問道:“為什么獵人會選擇付出捕獵鹿兩倍的時間去捕獵海貍呢?”不是因為“海貍的價格是鹿的兩倍”,而是因為,在現有的生產力水平下,海貍比鹿難對付,需要耗費兩倍的勞動時間。“如果海貍的價格低于鹿的兩倍,獵人們就會放棄捕獵海貍而選擇獵鹿。”確實是這樣。但是這里有一個前提條件:人們得到一只鹿的勞動時間是不變的(此時的鹿就有充當一般等價物的潛力),但是人們獵殺海貍的技術水平提高了,用不了原來的勞動時間就可以得到一只海貍。也就是說,海貍和鹿相交換的標準、依據依舊是勞動時間的耗費。
因此,是勞動投入量決定價格。我們把視野從海貍和鹿的例子中放寬到所有商品中,所有的商品的交換價值構成價格體系。這個價格體系的形成和發展(變化)的標準依舊是勞動時間的耗費,是勞動投入量決定價格體系,而不是相反。因此,一只海貍的價格可以匹敵兩只鹿,其原因確實是一只海貍的價值相當于兩只鹿的價值,更進一步的討論是得到一只海貍的勞動時間是得到一只鹿的勞動時間的兩倍。
另外想要說明一點:用一只海貍可以交換兩只鹿,這種交換比例關系是人們在千百萬次的交換中逐漸穩定下來的,并不是一開始就是如此,也不會永遠如此。
九、趙磊:宇澤的假設很陰險
我點評一下國毅的發言。
國毅說得對,宇澤的邏輯是“倒果為因”。你從宇澤的假設出發,闡述了射殺鹿、射殺海貍都要花費勞動。但是我想提醒大家,宇澤的“獵人故事”的問題導向,并不是國毅說的這么敞亮,而是很陰險。宇澤“獵人故事”的邏輯有兩個環節:
第一個環節,是假定海貍和鹿的價格(價值)可以隨意變動。這個假定非常隨心所欲。是啊,假如海貍的價格高于鹿的兩倍,那獵人肯定會去捕獵海貍呀。問題在于,在宇澤的故事里面,價格(價值)變動的依據(勞動)其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價格(價值)變動的后果(勞動投入量發生了變動)。
我不知道大家意識到沒有,這種假定的隨意性非常陰險。之所以陰險,就在于它把“價格(價值)變動”定義成了“主角”,而“勞動”卻成了“價格(價值)變動”的馬仔。這是我想說的第一點。
第二個環節,宇澤這種隨心所欲的假定既不科學,也隱藏著一個陷阱(這個陷阱我在前面第二節已經作了分析)。我在前面說過,價格(價值)并不是先在的、先驗的東西。不明白這一點,那你就被宇澤給蒙了——至于價值形成與價格形成的區別,另說。
國毅說,宇澤把“邏輯因果關系搞顛倒了”。如果追問一下,為什么“日本理論經濟學第一人”要這樣干呢?他為啥要用搗糨糊的方式來“顛倒因果”呢?動機何在?這個追問也許能讓你意識到這里面有陷阱。很好,請大家繼續討論。
十、彭卓:宇澤的邏輯有迷惑性
亞當·斯密在分析射殺鹿和海貍時用的是勞動時間來衡量價值,進而決定價格,這是斯密的勞動價值論。他在《國富論》第六章“論商品價格的組成部分”中是這樣說的:“在資本累積和土地私有尚未發生以前的初期野蠻社會,獲得各種物品所需的勞動數量之間的比例,似乎是各種物品相互交換的唯一標準。”
接著,斯密就舉了這個鹿和海貍的例子。這其實是斯密在論述他的勞動價值論:勞動創造價值,價值是由勞動量決定的,至少在“資本累積和土地私有尚未發生以前”是這樣的。
所以這一點我比較疑惑,為什么這本書的作者把斯密的這個勞動價值論叫做“生產費用論”,認為各種成本或要素都創造價值,能夠參與分配,這肯定是不對的。我個人以為,他在這里閉口不談“勞動價值論”,只說“生產費用論”,是為他后面的理論做鋪墊。
斯密明明白白地說了,是由于射殺海貍的時間是射殺鹿的兩倍,才導致海貍的價格是鹿的兩倍。但是,這本書的作者卻認為,射殺海貍的時間之所以是射殺鹿的兩倍,是因為海貍的價格是鹿的兩倍,是由價格決定勞動。這里,他首先拋棄了價值,其次顛倒了本質與表象,這也是肖師兄說的“他把本質的東西和表象的搞反了”,本質的東西應該是指勞動價值論,表象是價格,他把“勞動”這一本質內容和“價格”這一表象給顛倒了,具有很強的迷惑性,如果沒學過勞動價值論的,第一反應肯定覺得他說的很有道理。
“為什么獵人會選擇付出捕獵鹿兩倍的時間去捕獵海貍呢?”不是因為前者的價格是后者的兩倍,而是因為獵殺前者確實需要花費獵殺鹿的時間的兩倍,付出了那么多的勞動,在交換的時候必然要交換足夠的獵殺鹿的勞動時間,相等的勞動時間才能完成交換,否則交換就很難實現。
按照他的邏輯走下去,“如果海貍的價格低于鹿的兩倍,獵人們就會放棄捕獵海貍而選擇獵鹿;相反,如果海貍的價格高于鹿的兩倍,那么獵人們會放棄獵鹿而選擇捕獵海貍”,那么如何確定價格和勞動量呢,或者說,如何實現“均衡”呢?按照他們的邏輯,如果海貍的價格高于鹿的兩倍,那就增加射殺海貍的勞動投入量,如果鹿的價格高于海貍的一半,那就增加射殺鹿的勞動投入量,直到改變最后一個單位的勞動量,使得海貍的價格恰好等于鹿的兩倍,就達到了“均衡”。
進一步地講,那就是最后一個單位勞動的投入,獲得的邊際產出(或邊際效用或邊際價值)相等時,那就達到了“均衡”,這就是邊際效用價值論。原文里講的這三位經濟學家的理論應該就是這個邊際效用價值論,這三位經濟學家應該就是瓦爾拉斯、門格爾和杰文斯,他們三位一同創立了邊際效用價值論,成為他們所說的“現代經濟學”的重要理論基礎。
亞當·斯密的勞動價值論本身是否全面,這里不做討論;這三位經濟學家,在這種斯密的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發展出了邊際效用價值論;這本書的作者又把這種邊際效用價值論當作真理來宣揚。可見,“現代經濟學”的錯誤有多離譜,而且是越來越離譜。
十一、趙磊:彭卓的溯源很給力
彭卓追根溯源,挖到《國富論》的原文中的例子——鹿和海貍的例子。宇澤為了構造神邏輯,為了否定勞動價值論,為了給邊際效用價值論做鋪墊,他不惜用搗糨糊的方式來對待斯密的案例。彭卓追到“根”上去了,而且把這個問題展開,一直追問到邊際效用價值論。
十二、陳雨森:宇澤的結論有點繞
宇澤這段話前半部分的例子出自于斯密的《國富論》,文中提到的“自然價格”其實指的是“價值”,捕獵海貍花費8小時而捕獵鹿花費4小時,這里說的8小時和4小時的勞動是同質。因此,我們才可以說海貍的價值是鹿的價值的兩倍。
我認為前半段這個例子及其所論證的觀點沒有問題,即人們進行交換的標準是各種物品所需勞動量之間的比例。問題在于后面這段,文中指出“如果海貍價格低于鹿的兩倍,獵人則會放棄捕獵海貍而選擇獵鹿”,反之亦然。我認為這是得不出“不是勞動投入量決定價格,而是價格體系會決定勞動的投入量”這個結論的。
這個結論有些繞。主要是因為,一方面,就單個獵人而言,如果某種獵物價格上漲,那么個人愿意捕獵這種獵物,因為他付出相同的勞動能夠得到更多的回報,但此時捕獵單個目標獵物的時間并未發生變化。而就全體獵人來說,當這個價格上漲,有更多的獵人去捕獵目標獵物的時候,整個社會投入捕獵目標獵物的“勞動投入量”增加了,使得社會上這種商品的總供給增加。
所以,我認為價格是作為一個信號在配置整個社會的勞動,確定整個社會勞動在不同領域的分配比例。但是,價格的變動并沒有影響獵人捕殺目標獵物所需要的時間。因此,可以說價格體系影響社會勞動量在不同領域的分配,但是,不能說“不是勞動投入量決定價格”。
十三、趙磊:是真糊涂,還是裝糊涂?
陳雨森做了比較全面的功課,最后得出結論:“不能說‘不是勞動投入量決定價格’”。這個結論是正確的。關鍵在于,這里的“勞動投入”指的是什么?
宇澤用的“勞動投入量”這個概念,就是一個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裝。他這個“勞動投入量”的概念,一會兒指的是社會供求相等時需要投入的勞動量,也即需要在某個部門投入的“勞動總量”。一會兒又指的是生產某種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我不知道他是滑頭,還是真沒搞懂?要不他干嘛這么喜歡搗糨糊?
換句話說,這位日本學者的“勞動投入量”是一個含糊其詞的東東。它既可以指社會應當分配給某一部門的勞動量,比如說生產糧食的部門或者生產啤酒的部門,又可以指生產某個商品的勞動耗費(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馬克思用兩種“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明確作了界定。但是宇澤的“勞動投入量”,一會是總的、宏觀的勞動投入量,一會兒又變成了決定價值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他是故意混淆,渾水摸魚,把讀者帶進溝里。陳雨森同學,你注意到了沒有?(陳雨森:“老師,我注意到了。這個概念一會兒是就個人而言的,一會兒又是就整個社會而言的。它不是一定確定的概念。”)
這就是日本學者給大家挖的一個大大的坑,等著你們跳進去。我們討論問題,邏輯和概念都要嚴謹。日本人挖的大坑,八路軍是不會上當的。
十四、咖婭:不能混淆價值與價格
首先,宇澤沒有提到交換過程,那么這里的價格從何而來呢?如果海貍的價格高于鹿的兩倍,然后,獵人就會放棄鹿而去捕獵海貍。為什么這個獵人就會放棄呢?
另外,趙磊老師在《不能量化證偽了勞動價值論嗎?》這篇文章中談到,價值形式和價值是有區別的。價值只有在商品交換的過程中才能夠表現出來,并且這個價值是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但是價格只是價值的表現形式,它的本質仍然是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價值,必須將兩者區分開來。
十五、趙磊:討論推動進步
GAIA(咖婭)講了她的學習體會。我覺得有兩點很有意義。
第一,因為Gaia是意大利人,那么中文的表達相對而言沒有那么流暢。GAIA的論述的大意是,價值是本質,價格是現象,價值是作為本質隱藏在現象當中,這兩者一定要區分開來,不能因為現象的表現就否定“價格是由價值決定的”以及“勞動決定價值”。這個論點是非常明確的,是馬克思主義的。
第二,GAIA正在閱讀《資本論》,她自己也坦誠地說在讀的過程中,對交換價值和貨幣之間的區別和關聯,有很多困惑。我看到前段時間同學們自發地在組織一些讀書會,搞得有聲有色,其中就涉及到交換價值,涉及到貨幣。我建議你們將來討論基本問題的時候,特別是在搞《資本論》學習會時,也讓GAIA參與進來,大家一起討論,這樣就能推動進步。
十六、張湘婕:宇澤假設符合實際嗎?
捕獵海貍在客觀上就是需要付出兩倍的時間,這不會因為市場價格的變動而改變,即使強行規定海貍不花錢而鹿要花大價錢,捕獲海貍也還是需要兩倍的時間。
宇澤把獵人付出兩倍的時間去抓海貍的原因歸結為價格,我認為是屬于因果倒置了,是捕獵在前,價格形成在后。這里的這句話給我的感覺就是,他在進行西方經濟學的數學建模,強行把價格設為自變量,與實際完全不符。
后面的“如果海貍的價格低于鹿的兩倍,獵人就會放棄捕獵海貍而選擇獵鹿;相反,如果海貍的價格高于鹿的兩倍,那么獵人們會放棄獵鹿而選擇捕獵海貍。”這里似乎體現的是價格波動,海貍的價格不可能永遠正好等于鹿的兩倍。
但是我覺得真實的過程應該是:先是一群獵人追捕海貍和鹿,即投入了勞動量,才會造成價格波動,才會有這個“如果”。
最后這句話又提到了“價值”,我理解的意思是價值決定了價格,而價格又決定了勞動投入量,所以他得出的結論似乎是價值決定勞動,那就還是一樣的問題,沒有勞動是不存在“價值”這個概念的。
十七、趙磊:現代經濟學,“開倒車的經濟學”
張湘婕和張國毅一樣,都看到宇澤的論證是“因果倒置”。能看到“因果倒置”,說明你們接受了勞動價值論。
你提出了一個問題,說宇澤一會兒說價值,一會兒又說價格。我補充一點,現代經濟學連價值范疇都不再認可了。為什么呢?他們原來有價值范疇。在古典經濟學中,哪怕后來的一些庸俗經濟學家,他們有價值范疇。但是進入20世紀以后,現代經濟學干脆連價值這個范疇也不提了。這是為什么呢?因為他們說:“價值在哪兒呢?我看不見啊!價值是什么東西呢?我看不見啊!”現代經濟學后來只敢理直氣壯的說“價格”,就是那把偉大的“叉子”——均衡價格,他們說“均衡價格”這東西看得見,摸得著,才是宇宙真理。
那么價值在哪兒呢?現代經濟學告訴你:“不知道”。如果非要問價值在哪兒,那么價值是“薛定諤的貓”:“價值就是價格,價格就是價值”。所以,現代經濟學從此不再說價值了。在他們看來,價值這個東西看不見,那就不存在。馬克思說商品價值是“人類抽象勞動”,可是我們看不見商品“花費了多少勞動”,我們看得見的只是商品“賣了多少錢”,看到的是“價格”。他們不認可價值的原因就在這里。
可是現象未必是真相。古典經濟學至少還承認部分真相,可是今天的經濟學,所謂“現代經濟學”連古典經濟學承認的真相都給否定了。恕我直言,現代經濟學已經成為“開倒車的經濟學”。
張湘婕的功課做得認真,也看到了問題。我還要強調一點,宇澤把價值或者價格當作一個先在的東西,把價值的形成、價格的形成當成一個先驗的東西。所以,我建議你看看我剛才提到我寫的那篇文章。
十八、陳鴻池:宇澤的邏輯很混亂
我認為宇澤的這段話有兩個問題。
一是作者的提問令人不可思議。宇澤問道,為什么捕獵鹿的時間會是捕獵海貍的兩倍呢?其實,歸根結底,這自然是由捕獵鹿和捕獵海貍的勞動過程所決定的。在這之外再做出怎樣的回答,不過是作者為了引出其后續理論的操作罷了。
二是作者的形式邏輯。宇澤指出,勞動時間取決于價格,他又指出,價格取決于價值。如果我們問什么又決定價值呢?按照他的邏輯,恐怕又要出現一個新的概念用于解釋價值了。可見,宇澤不過是在用新的概念覆蓋舊的概念,他從未對每個概念做出完整的解釋,不過是在玩弄概念的邏輯游戲罷了。
十九、趙磊:陳鴻池的揭露很到位
陳鴻池同學的揭露很到位。他指出這位日本學者的邏輯問題:“為什么獵人會選擇付出捕獵鹿兩倍的時間去捕獵海貍呢?原因就是海貍的價格是鹿的兩倍”,“一只海貍的價格可以匹敵兩只鹿,難道不是因為一只海貍的價值相當于兩只鹿的價值嗎”。
宇澤的這兩句話的確存在著形式邏輯的矛盾。比較一下形式邏輯當中的矛盾律。宇澤前一句話講的是“價格決定勞動投入”,他的話語很含糊,甚至也可以理解為“價格決定價值”。如果把勞動投入時間理解為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話,那么前一句話實際上講的就是“價值是由價格決定的”。
但是后一句話他又明確講,“價格由價值決定”(雖然宇澤用的是問號)。前面講“價格決定價值”,后面又講“價格被價值決定”,這樣的自相矛盾顯然存在邏輯上的問題。這位日本學者怎么會犯這樣的錯誤呢?換言之,為什么“日本理論經濟學第一人”會如此地搗糨糊呢?
所以,起碼在面上看起來這是一個明顯的矛盾。陳鴻池同學揭露了這個矛盾,確實是這樣。不錯,這樣的思考很深入。
二十、陸茸:價格成了先驗的東西
在看到“不是勞動投入量決定價格,而是價格體系會決定勞動的投入量”這個地方時,我就產生了一個疑問。我想他的表述里面并沒有說這個“價格體系”是如何決定的,即缺少了對價格如何決定的闡釋。所以,我認為他在這里確實把價格當做一個先驗的東西。后面的思路就是趙老師指出的他假設上的一些問題。
二十一、趙磊:言簡意賅
陸茸的回答,說明她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里面受過嚴格訓練。她言簡意賅地表達了馬克思主義的看法,點到了要害。宇澤講到“價格決定勞動”,但這個“價格”再找它的因,在哪兒呢?宇澤“王顧左右而言他”。于是,價格(價值)就變成宇宙大爆炸的時候就存在的一個先驗的東西了。
二十二、侯夢瑩:奇怪的結論
看了宇澤的文本后,我就在思考,如果一個完全沒有接觸過政治經濟學的人,他肯定會覺得捕獵海貍和鹿分別需要花費8小時和4小時,勞動時間投入不一樣就決定了它帶來的收獲是不同的。這里用數字來舉例,假設單位時間價值量是10,那么捕獵海貍就能獲得80,捕獵鹿則獲得40。它其實是根據投入的勞動時間來決定的。如果你說海貍的價格低于鹿的兩倍,假設海貍變成70。勞動者認為我付出與回報不成正比,就不會選擇去捕獵海貍了。
所以,我覺得歸根到底還是勞動投入決定了價值量。文章的結論“價格決定勞動投入量”,這里讓人感覺有些奇怪。
二十三、趙磊:討論還可以深入
侯夢瑩在這里提出了很好的問題,但是你沒有再展開討論。這里似乎涉及到了“兩種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一個就是單個商品來看,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商品價值;還有就是是否需要考慮到整個社會總勞動時間在部門之間的份額,即學界定義的馬克思“第二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不論哪種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都是在講價值是由人類抽象勞動決定的。我在這里提一下,沒時間展開說了。
最后我簡單總結一下。今天的討論非常好。很多問題可能我想到了,同學們不一定想到了;同學們想到了,我也許沒有想到。尤其是同學們對于文本的溯源和分析,不乏閃光的、有啟發的思考。討論不僅僅是老師引導學生,學生反過來也會給老師啟發。
基于今天的討論,我們總結出宇澤的幾個問題,第一,是“因果倒置”。第二,宇澤的假設非常隨意。第三,宇澤把價格看做先驗的、先在的東東。第四,陳鴻池發現宇澤文本中存在形式邏輯問題。第五,很多同學指出了宇澤文本中存在概念含混不清的問題,等等。
注釋:
【1】[日]宇澤弘文著,李博,尹芷汐譯:《像經濟學家一樣思考》第39-40頁,北京聯合出版社公司2022年。
【2】這是發言的錄音整理,發表時個別地方作了補充修改。
「 支持烏有之鄉!」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