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高中班草,前任單位行草,金雞湖霍建華之托,決定憑淺薄的認知來扯一扯對房地產稅的看法。之前在談恒大時提到評論中國房地產大約是最容易翻車的行為,可以參考前CCB董事長,現銀保監會郭主席十多年來的唱空言論,可見此言還需慎重。由于這個命題實在太大,主要講一點可以看懂的底層邏輯和老百姓最關心的房價走勢問題。
“為積極穩妥推進房地產稅立法與改革,引導住房合理消費和土地資源節約集約利用,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2021年10月23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一次會議決定:授權國務院在部分地區開展房地產稅改革試點工作。
要注意,這次依然是試點,離全面征收房地產稅還差一個立法階段,一般認為立法將是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我卻認為按我黨的辦事效率,立法這種活也就是想不想的事情,不存在能不能或者難不難的問題。廣義的房地產稅包括了從土地出讓到房產開發、銷售、持有、流通等各個環節所產生的所有稅收,這次改革和試點的應該是持有環節的房產稅。其實上海和重慶已經試點過十年了,所以也不算新鮮事。那么遲遲不立法的原因是,需要統籌權衡經濟增速、地方債務、金融風險、公眾情緒等各方面的因素,確實是一件道阻且長的事情。
房產稅試點是可以繞開人大直接開干的,意義在于為將來全面開征提供幾個抗壓測試的樣本,據說這次深圳、浙江和海南在名單內。其實老百姓最關心的不是房產稅怎么收、收多少,大多數人關心的是征稅后房價的走勢問題,畢竟跟一年多交幾萬塊稅金相比,房子縮水幾百萬是一件更加令人心碎的事情。如果以上海和重慶兩個樣本來看,應該說都沒多大參考意義,甚至走向了兩個極端。
首先要明白一個原則,國家出臺房產稅的根本目的在于增加地方財政收入,而不是為了降低房價。就像上海一樣,跟人口流入與貨幣超發產生的動能相比,房產稅對房價的影響幾乎可以忽略,當然也跟十年前試點政策存在許多稅率和征收范圍的不足有關。然后看重慶,作為直轄市,目前房價13000+在全國僅排40位開外,從絕對價格和十年漲幅來看,重慶在控制房價方面絕對是獨樹一幟的典型,但這跟房產稅的關聯也不大,根源還是黃奇帆市長堅持充分保證土地供應的方針政策。所以,對各地政府來講,要控制房價并不缺辦法,最終也只是想不想的問題。
雖然房產稅對于房價的影響最終要經過市場來驗證,但是老百姓的心理往往是脆弱的。在今年接近冰封的市場環境下,連北京有兩套房子的老阿姨都覺得現在出政策不妥,國家卻偏要這個時候試點房產稅,回過頭來說明了通過房產稅來增加地方財政收入實在是形勢所迫。為什么這么說,可以從1994年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朱镕基和財政部副部長項懷誠共同操盤的分稅制改革說起。
當年的背景是中央財政窮得揭不開鍋,而有些地方政府富得流油,有些也窮得叮當響。為了重新平衡這塊稅收蛋糕的切分,分稅制應運而生,由此國庫得到大幅充盈,窮地方通過轉移支付也得到了實惠,而幾個富地方就變得捉襟見肘,因為原來已經習慣花錢大手大腳,再讓他們節衣縮食是不可能的。到1998年商品房改革后,地方政府開始靠賣地增加財政收入,特別本世紀以來,土地出讓金占財政收入的比重從14%一路上升至42%。這還是全國平均水平,各地差異更是大得驚人。杭州、廣州、武漢、南京這些大城市的土地財政依賴度甚至超過了100%,我們蘇州大約55%。
由此可見,如果沒有這塊賣地收入,地方政府的日子是要過不下去了。那繼續靠賣地過日子行嗎?可以這么說,不管在中央還是地方層面,土地財政不可持續早就是共識。而新冠疫情、貿易摩擦和生育率斷崖等因素,加速了這一趨勢的提早到來。雖然中國經濟在新冠籠罩下表現出了極大的韌性,但疫情是全球事件,在全球化年代,即便中國有基礎實現內循環,仍然不可能獨善其身,新冠帶來的深遠影響可能還要數年后才會越發體現。加上貿易摩擦帶來的被動局面,深刻警示著我們國家的經濟應當盡早從自娛自樂的房地產迷局里掙脫出來,回歸實體制造,重視科技創新。
生育率的影響可以結合房地產長期看人口的論斷來看,這里的人口指人口流入,但前提是要維持人口的基本盤,如果基本盤不增甚至萎縮,那即便幾個一二線城市中短期內人口不出現問題,剩下的城市將不可避免地進一步空心化,莫非未來中國人要全部擠在珠三角和長三角。之前在談俞敏洪的文章里提到國家已經鐵了心整治住房、教育、醫療這三個阻礙生娃的重大民生問題,一個文件就團滅了幾千億產值的教培行業,對性質嚴重十倍的住房問題更加不會心慈手軟,不要低估國家堅持“房住不炒”的決心。房子要是沒有人住,在上海還是在鶴崗其實區別不大,房子太貴嚴重擠壓了消費能力,讓人不再生小孩,但是沒有人不會死去,這就是一個死循環。去年我國出生率跌破1%,人口自然增長率1.45‰,創43年來新低,再下去就是負增長。這個問題解決不好,就不是民生問題,而是事關民族存亡的大問題。
今年下半年各大城市的土地一級市場幾乎熔斷,說明市場行情已無比蕭條,開發商流動性接近枯竭。這個行業走到今天,衍生開來累積的可能是幾十萬億的雷,在這鏈條里所有獲益的各方應該說都有責任,包括地方、開發商、金融機構和部分購房者,那大家都獲益,誰吃虧了呢?主要是剛需部分的購房者,簡稱為韭菜。國際上有個說法,十次危機九次地產,房地產作為周期之母,催動經濟增長的功能并非中國一家特色,二十年來國人對房子深信不疑的信仰,恰恰說明了我們并沒有穿越過一個完整地產周期。
網上有一個靈魂拷問,中國房地產紅紅火火二十年,看上去大家都賺得盆滿缽滿,結果玩到現在是地方政府、開發商、老百姓全都欠了一屁股債,那么錢都去哪里了?大多人會覺得這是個段子,其實能回答這個問題,也就可以解開中國房地產游戲的本質。有句話叫要致富先修路,基礎設施建設完善是一個城市或國家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前提條件。賣了地去修路,有了路才會有工廠和稅收,才會有就業和人口,然后繼續賣地賣房,繼續修公路,形成良性循環。但是政府賣地給開發商,開發商沒錢怎么辦,去跟銀行借錢。造了房子賣給老百姓,沒錢的老百姓也去跟銀行借錢。很多地方修路修上癮發現賣地的錢還是不夠,或者一些窮地方也學人家去修路,于是政府也開始去跟銀行借錢,也就是地方債的由來。所以,所有的錢都通過土地這個融資載體,最終都變成了全國各地的基礎設施。土地出讓金和地方債務一路伴隨中國房地產行業蓬勃發展,本質上看,也為中國經濟實現騰飛提供了充足的彈藥糧餉。后來有些政府發現跟銀行借錢比賣地更容易,于是開始先跟銀行借錢,并承諾未來幾年賣了土地來還錢,結果土地是賣了,銀行的錢一分也沒還,雪球越滾越大,到今天地方債余額攢到了幾十萬億,因某些不可言說的因素,具體數據無從考證,40萬億應該有。
眼下的局面是,部分極端房產公司的債務問題是一個不得不暴的雷,至少目前為止,我看不到靠譜的解決方案,風險傳導到銀行及供應商那里形成的陣痛會持續很久。不過中國的銀行全都家大業大,消化起來并不難,過去賺到錢現在吐掉一點也正常,供應商反而是比較受傷的群體。相對而言,居民債務的安全邊際還算比較高,因為房貸的集中度非常低,大面積違約的概率不大,而且房貸都有抵押,即使斷供銀行也能收回大部分本金,價格足夠便宜房子總歸賣得掉。中國人的房子情結決定了不到萬不得已不會放棄房子,所以吃苦耐勞兢兢業業的中國老百姓是房地產市場實現軟著陸的最大仰仗,這在全球也是沒有先例可循的。
所以地方債務的問題,就是所有問題的癥結所在,因為這個雷不能暴,國企央企已經暴過雷,城投債的剛兌信仰再要被打破,那可是不得了的事情,結果就是大家都玩不下去。雖然很多地方政府實質上早已破產,但真的冒出一家說要破產了不還錢,可以想象會是一個什么局面嗎?土地出讓金是房地產增量盤里最大的一塊收入來源,可以預知的是,未來將以肉眼可見的速度萎縮,要實現收支平衡,方法無非是開源節流。而房產稅作為存量盤里新開辟的稅源,當仁不讓成為最佳第六人,也是最重要的開源項目。從節流角度,前兩年提出的“新基建”無非是在原先老基建框架上的升級改造,成本和投入相對較低,釋放的信號就是未來一段時期內應該不會再有過去那種基建規模,可以看作一種節流的表現吧。也就是說,中國勢必會走上縮表的道路。
最近胡亂猜測一下房產稅對房價的影響。要說影響房價,不如說影響房子的流動性。一旦房產稅率高于租金收益率,或者房價持續上漲預期不再,不具備某些功能的房產就會失去投資屬性,海量的存量房將會進入市場,在接盤俠增量不足的情況下,供需嚴重失衡勢必導致剛需房的流動性進入冰河時期,對房價的打擊可想而知。而最優質的房產資源應當不受多大影響,因為優質資源永遠稀缺,也沒人在乎多納稅,納稅也是光榮的嘛,就像買賓利的沒有人會問油耗一樣。而且這些資源很可能會越來越貴,城市的規劃局限決定了優質資源的增量有限,而貨幣越來越多,有錢人也會越來越多,這里的供需關系也會逐漸失衡。所以,分化一定在所難免。不過,房產稅可能也只是加速了分化的提早到來,沒有房產稅,分化一樣會出現,這個是全世界都適用的規律。當然,要是把時間維度拉長到十年二十年,就很難講了,通貨膨脹是必然的,那時的人民幣也不再是現在的人民幣了。
LCGG
2021/11/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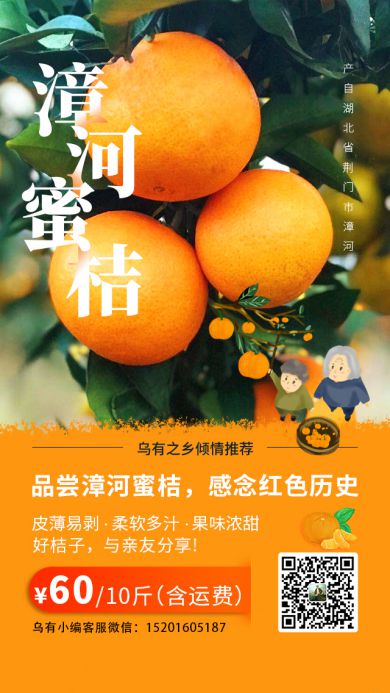
「 支持烏有之鄉!」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