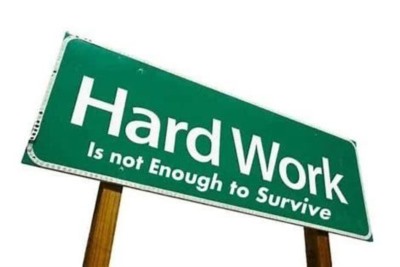“競業協議”無疑是2024年春天勞動領域的關鍵詞。
今年2月,11位某頭部互聯網企業的離職員工通過一位名為“碼代碼的喵2018”的微博用戶進行實名舉報,稱前司涉嫌濫用競業限制協議,將幾乎所有互聯網企業都列入競業禁止的范圍之內。有員工在離職后即便是從事與之前的工作并不相關的領域,仍然被起訴要求高額競業賠償金(數十萬至數百萬元不等)。
最近,微博用戶“洋洋要活下去”即一位工作4個月被競業索賠45萬元的當事人,與網友分享了這一事件的最新進展(現已被屏蔽刪帖),稱該互聯網企業通過長寧仲裁委聯系到ta,表示愿意撤回仲裁,前提是要求離職員工返還已經收到的競業補償金。然而該用戶基于“被前司跟蹤、被偷拍、被曝光微信、被微博大V抹黑、身邊人員被騷擾”的經歷最終選擇了拒絕,請求仲裁庭正常出具仲裁結果。
關于競業禁止或曰競業限制協議的規定,主要是在《勞動合同法》的第二十三、第二十四和第二十五條中。其中第二十四條第一款規定,“競業限制的人員限于用人單位的高級管理人員、高級技術人員和其他負有保密義務的人員。競業限制的范圍、地域、期限由用人單位與勞動者約定,競業限制的約定不得違反法律、法規的規定。”
這一規定是關于競業限制協議的適用范圍,看似明確具體,然而在實踐中“負有保密義務的人員”卻顯得撲朔迷離。這是因為企業經常會在與勞動者簽訂競業限制協議的同時也簽訂一份《保密協議》,從而為勞動者賦予了保密的義務,即便該勞動者本身幾乎沒有接觸到公司核心技術或商業秘密的可能性。
更有“精明”的企業直接以“保密協議”取代“競業協議”,不但可以不發競業限制期間的補償,而且仍然能夠在勞動者跳槽之后主張其“違反保密協議,給企業造成了損失(乃至巨大損失)。”
不難看出,在與相對更為有錢有勢的一方——企業/公司的較量中,勞動者往往處于喪失話語權和博弈能力的不利地位。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回應事件相關評論區里不時出現的質疑:
“如果不想簽就別簽。”
“這種協議員工簽之前肯定知道,公司這么做合理合法。”
“違約了還能這么理直氣壯?”
誠然,“自愿原則”即意思自治與尊重意愿是《民法典》的核心基石,“誠實信用原則”即重合同守信用被稱為是《民法典》的“帝王條款”。然而這二者的共同前提是“平等原則”即雙方法律地位以及權利義務的平等,至少不能懸殊到“顯失公平”的地步。
而在勞動領域,用人單位和勞動者的地位是明顯不平等的,這既是制定《勞動法》及《勞動合同法》等法律法規的基本前提,也是其與《民法典》最主要、最根本的區別。無論是主張“單保護”(旨在保護勞動者權益)還是“傾斜保護”(以顯性的方式提出保護勞動者,以隱性的方式提出保護用人單位)的學者,都認可“現代勞動法緣起于勞資關系不平等”的觀點以及“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的立法宗旨。
當然,具體問題應具體分析,這種“地位的不平等”也不能一概而論。例如羅永浩(錘子科技創始人、交個朋友直播間首席好物推薦官)曾在直播間里提到董宇輝的競業禁止協議時道出了競業協議的關鍵:競業禁止協議并不是不能違約,而是違約要承擔責任。對于違約金金額,羅永浩稱,“傳聞是5個億,5億又怎么樣,我今天下午其實就已經問了一圈,他們覺得以董宇輝的價值,賠5個億也愿意干,這是普遍狀態,沒有信口開河。”
可見即便同為職場打工人,高級打工人董宇輝和基層打工人在面對競業協議時的處境并不相同。企業為了挖走競爭對手的高級管理人員、高級技術人員或其他重要人員,往往會在談判中提出“愿意代為賠付高額違約金”等豐厚條件。
在實踐中,甚至無需如此破費。企業更傾向于選擇讓高管在競業限制期限屆滿后入職;或者直接把ta調到公司的總部(在國外)或者海外事業部,工作一段時間之后再調回來——此時前司試圖取得當事人違反競業禁止協議的證據便極為困難了。
另一方面,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一)》第三十六條之規定,競業限制補償金的標準大致是勞動者在勞動合同解除或者終止前十二個月平均工資的30%(或勞動合同履行地最低工資標準)。就高級管理人員和高級技術人員等而言,由于競業限制補償金過于高昂,且高管跳槽一般都是和公司鬧僵了,公司方通常并不愿意支付高額補償金,從而就沒辦法啟動競業禁止協議。
所以從根本上說,競業協議有著多重面孔:在面對基層打工人比如初入職場的應屆生時,其能夠起到強有力的約束作用,斷送了他們成功跳槽的機會甚至是整個職業前景。若是家境殷實,離職后在家里做一年左右的“全職兒女”來挺過競業限制期,或是轉換賽道、從零開始倒也并非難事;相反的是在本文開頭提到的實名舉報事件中,不少舉報人都提到“出生農村”、“小鎮做題家”、“父母生病”、“急需用錢”等現實困難,此時的競業限制協議無疑是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在面對高級管理人員、高級技術人員等這些競業協議本來意圖限制的群體時,則顯得綿軟無力、可以從各處突破。這個機制顯然是極其不公平的。
也有人會指出,針對這個機制是存在相對應的防御方式的,比如違約金的司法酌減制度。簡而言之,被索賠數十萬至數百萬元,并不必然意味著需要賠償這么多錢,當事人可以主張約定的違約金數額過分高于造成的損失,向法院或仲裁機構請求予以適當減少。畢竟如學者覃榆翔(2023)所言,競業限制違約金雖然名曰“競業限制”,但并非限制勞動者的人身自由,而是起到彌補用人單位受有損失的效果,因此競業限制違約金應當認定為補償功能的違約金,而非懲罰功能的違約金。在司法實踐中,的確也不乏成功的例子。
然而在涉及某頭部互聯網企業的案例中,事情卻呈現出了另一番圖景。根據微博用戶“菜姐在線”的描述,其在該企業工作五年之后離職,被競業索賠150萬元,法院最終在缺席判決的情況下支持了企方的索賠主張。除此之外,仍有不少被裁定賠償數十萬元的案例。
可見“高額違約金是否能夠酌減”以及“可以酌減多少”都是具有不確定性的,與雙方當事人的法律認知水平、舉證能力、論證能力、法律資源等可能都有一定關系。面對行業頭部企業強勢的法務團隊及其所聘請的外部律師團隊時,當事人的防御之路也變得異常艱難。
那么,我們是不是應該重新審視競業禁止協議的合法性、正當性以及必要性?
在比較法上,歐盟遵循人員自由流動的原則,通常認為競業禁止條款是不合法的,即合法屬于例外。在英國,現代勞動判例法認為,雇員和雇主訂立的競業限制條款并不因為訂立行為而自動生效,雇主必須舉證該條款的訂立具有必要性。而就在今年的4月24日,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發布了關于競業禁止條款的最終規定,禁止未來的幾乎所有競業禁止協議。
在我國,最高法院亦發布了涉競業限制勞動爭議指導性案例,與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聯合發布的案例中也包括涉競業限制案,旗幟鮮明地否定侵害勞動者擇業權的違法競業限制行為。在未來,最高法院將堅決依法糾正競業限制條款適用主體過寬、限制范圍不合理、權利義務不對等等違法行為,暢通勞動力資源的社會性流動渠道。
希望上述法治精神能落實到地方,在優化營商環境的同時,嚴格限制競業協議的適用對象,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這并非依賴于個人內心的許愿,而是持續不斷的公共討論、發聲與為權利而斗爭。
參考資料
[1] 王天玉:《對幾個勞動法學理基本命題的反思》。
[2] 覃榆翔:《〈民法典〉視閾下違約金司法酌減規則的區分適用論》。
[3] Spafax Limited v.Harrison[1980]IRLR 442. 轉引自鄭愛青:《從英法勞動法判例看勞動法上的忠實義務與競業限制條款——對我國<勞動合同法>規范競業限制行為的思考和建議》。
[4] 證券時報e公司:《羅永浩直播談董宇輝:以他的價值,競業賠5個億也有機構愿意干》。
[5] 財經E法:《最高法法官詳解競業限制濫用癥結》。
「 支持烏有之鄉!」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