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人大代表建議取消“農(nóng)民工”稱謂,認為該詞帶有歧視性。深圳市人社局在9月17日答復稱,“我市雖不能要求本地媒體不使用‘農(nóng)民工’表述,但也將結(jié)合深圳實際,引導新聞媒體多使用‘來深建設者’表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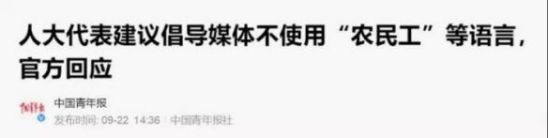
給農(nóng)民工正名的消息不是什么新聞,在2007年和2012年都有人大代表提出過相關建議,并引起了媒體關注,其中最積極的正是吸納農(nóng)民工最多的廣東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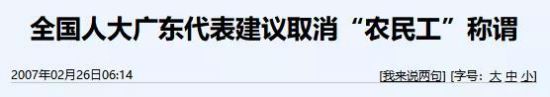
“農(nóng)民工”這個詞誕生于1984年,一般指在異鄉(xiāng)務工或從事個體經(jīng)營的農(nóng)村居民,并非天生就帶有歧視性味道。
在“農(nóng)民工”之前,形容農(nóng)民工的有“盲流”、“打工仔”、“打工妹”等詞,由于歧視意味強烈,雖然也流行過一段時間,但并未得到官方承認。
中國人講究名正言順,相比于“進城務工人員”、“農(nóng)村外出勞動力”等詞,農(nóng)民工一詞顯得簡潔生動準確,“農(nóng)民工”這個詞就流行起來了,并且得到了官方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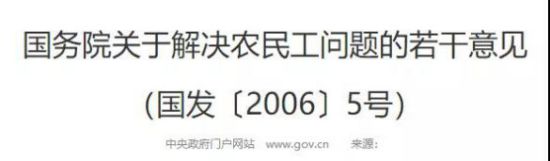
那為何在一些代表眼里該詞又帶有“歧視性”了呢?
說到歧視,站在鄙視鏈最頂端的應該是京城的“正黃旗大媽”了,在她老人家眼里,不僅僅是內(nèi)蒙古,只要沒有北京戶口,在她眼里都是“臭外地的,來要飯的”。除了她引以為傲的封建貴族血統(tǒng),她歧視外地人的底氣來自她的京城戶籍。
農(nóng)民工被被歧視,原因之一也是戶籍。由于農(nóng)村戶籍,農(nóng)民工在工作地的就業(yè)、醫(yī)療、子女教育等一系列問題上受到限制,城里人便有了高人一等的優(yōu)越感。
農(nóng)民工被歧視的第二個原因是他們是工人,而且從事的是最苦最累最臟最要命的工作。雖然名義上工人和農(nóng)民者是國家的主人,鐮刀錘子是他們的象征,但他們早已淪為社會底層,成為了“弱勢'群體”。

由于農(nóng)民工出身于經(jīng)濟落后的農(nóng)村,又從事最艱苦的工作,沒有機會接受多少教育,又沒有多余時間和金錢來為自己精心打扮一番,便成了城市中臟亂差的代表。在城市里的老板、房東、達官貴人、明星大腕等人看來,這些農(nóng)民工便是礙眼而多余的了,甚至成了要被清理的“D端人口”。

所以“農(nóng)民工”一詞雖然本身并無貶義,但農(nóng)民和工人本身就受歧視,正所謂“不好好讀書就去種地,要不就去打工”,兩者的結(jié)合體農(nóng)民工則更是低人一等了。在一些人看來,“農(nóng)民工”這個詞也就是罵人的話了。
于是有些代表就對農(nóng)民工的現(xiàn)實遭遇視而不見,腦回路一轉(zhuǎn)打起了“農(nóng)民工”這個詞的主意,似乎把它改成什么“城市建設者”、“新產(chǎn)業(yè)工人”、“城市新公民”就可以使他們擺脫被歧視、被“惡意討薪”、被……

如果你們真為農(nóng)民工著想,為什么不去嚴厲打擊拖欠農(nóng)民工薪資等問題或者切實提高農(nóng)民工待遇呢?
難道把名字一改,農(nóng)民工就可以和企業(yè)家、達官貴人等平起平坐一起成為“城市建設者”了嗎?就像有些人實為老爺而名曰“公仆”,但誰敢對人家低看一眼呢?
“農(nóng)民工”這個詞,有些人看它不順眼,實際是擔心人們一看到這個詞就想到那諸多的不和諧,便要把這個名詞和諧掉。雖然看上去腦回路有些簡單,但還真有些效果,比如說把資本家稱為“企業(yè)家”,資本家的形象不就一下子高大上起來了嗎?
中國語言博大精深,不缺美好的詞匯,也因此有了不少說的比唱的好聽的家伙,但希望我們今天還是少一些這樣的家伙吧。
紅色衛(wèi)士
2021年9月22日
「 支持烏有之鄉(xiāng)!」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wǎng)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wǎng)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xiāng)網(wǎng)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