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過去的兩會上,李克強總理在回答記者問時提到,我國零工經(jīng)濟就業(yè)達2億多人。我們應該如何理解“零工”這一用工形式近年來在國內的迅速崛起?
另一方面,零工經(jīng)濟從業(yè)者權益保障問題也日益為媒體、公眾、學者和政策界熱議,相關討論主要集中在是否應該承認其在《勞動法》上的勞動者地位,即與用工方是否構成實質上的雇傭關系,這牽涉到國家、企業(yè)和勞動者之間的權利、責任和義務的重新劃分及一系列相關的制度安排。我們追問,現(xiàn)有的立法實踐對保護零工的利益而言足夠嗎?應該如何理解這一立法爭論和動向?我們又應該期待或爭取一個怎樣的立法?
多數(shù)派認為,這些問題對理解走上了零工化快車道的中國勞動力市場至關重要。未來幾天里,我們將刊發(fā)相關文章,對這些問題進行探討。我們也期待您加入討論。
本文中,我們追問,零工經(jīng)濟何以迅速崛起?主流媒體和學界已經(jīng)對平臺資本和政府的角色多有著墨,本文嘗試從零工自身的角度出發(fā),解構零工經(jīng)濟“自由”、“靈活”的迷思。零工勞動者們如何理解和體驗零工經(jīng)濟的“自由”、“靈活”?這與他們投入零工經(jīng)濟之間的關系如何?自由的背后又隱含著怎樣的困境?
01
零工是誰?
“零工”在中國已經(jīng)不是什么新鮮語匯,但“零工”的真實面貌則相對模糊。不同的調查報告統(tǒng)計口徑五花八門,這部分是因為政府希望提高自己的就業(yè)數(shù)字,而大平臺公司的公關又極力想要急于擺脫“低端勞動密集型產(chǎn)業(yè)”的形象,以至于美團公關部門放出有7萬碩士以送外賣為生的新聞。
一般而言,很多人提到“零工”,首先想到的是平臺經(jīng)濟從業(yè)人員,或是所謂的“新業(yè)態(tài)”。零工的提法確實是從滴滴、美團、餓了么等平臺主流化開始流行起來,而這部分零工數(shù)量也不可謂不龐大。根據(jù)《中國共享經(jīng)濟發(fā)展報告》,2020年我國共享經(jīng)濟從業(yè)者人數(shù)達到8400萬,這一數(shù)字自2015年以來一直保持著近10%的年增長率,阿里研究院報告的數(shù)據(jù)則是1.1億。
平臺經(jīng)濟從業(yè)人員之外,還有很多其他的零工形式,如傳統(tǒng)的臨時工,小時工,短工等。根據(jù)李克強總理在剛剛過去的兩會記者會上給出的數(shù)字,中國零工經(jīng)濟就業(yè)者目前有2億多人,而同期我國勞動力總數(shù)為8億人左右。
阿里的報告進一步指出,靈活就業(yè)勞動者多是低技能的勞動工人[1],而最近清華大學的調查[2]也也印證了這一發(fā)現(xiàn),縣域零工從業(yè)者超過90%是本科以下學歷,其中90%是21-50歲的中青年人。他們中大多數(shù)人原本有自己的工作,以滴滴和美團為例,大部分來自產(chǎn)業(yè)工人和低技能服務業(yè)。
至于他們勞動狀況,多數(shù)派和其他平臺一直以來都跟蹤報道。一方面,每天12-16個小時的超長工作時間已經(jīng)成為常態(tài),很多勞動者(如騎手)在工作過程中面臨著甚至是生命的威脅,闖紅燈出車禍、猝死并不罕見;另一方面,因為多被認定為法律意義上的“自雇者”,與用人單位簽訂勞務合同而非勞動合同(很多人甚至干脆連勞務合同都沒有),他們無法享受“五險一金”和包括教育、醫(yī)療在內的基本的公共服務,辛辛苦苦工作半年之后發(fā)現(xiàn)自己還倒欠用人單位上萬元的荒謬情況也時有發(fā)生。

數(shù)據(jù)來源:國際勞工組織《中國數(shù)字勞工平臺和工人權益保障》,2020年11月
02
“自由”的零工
吊詭的是,在今天的中國,零工經(jīng)濟的崛起和工作普遍“零工化”的危機正被“自由”、“靈活”和“參與”等玫瑰色、充滿解放性的字眼所包裹。一方面,對一些主流經(jīng)濟學家來說,零工經(jīng)濟優(yōu)化了用工方和勞動力提供方的配對,從而提高了全社會勞動力配置的效率,對企業(yè)和求職者而言是雙贏;在政府那里,零工平臺和更廣泛的零工經(jīng)濟為經(jīng)濟轉型提供了就業(yè)蓄水池,互聯(lián)網(wǎng)平臺被認為是有助于人們– 特別是低技能勞動者 - 獲得工作機會的“參與性基礎設施” [3](participatory infrastructures for new jobs),被認為是穩(wěn)定經(jīng)濟、保護就業(yè)和保護民生的大功臣[4]。
在零工平臺公司的描述中,“工作自由,收入穩(wěn)定”常常被當成口號吸引潛在零工勞動群體。主流媒體上,類似《別再找全職工作了,自由職業(yè)者在零工時代更加獨立靈活》的標題比比皆是,“零工經(jīng)濟讓求職者更自由、自主、獨立,更有安全感”[5]的說法不絕于耳,媒體們爭相宣布穩(wěn)定的全職工作已經(jīng)過時,雀躍地迎接著一個人們可以主導自己為誰工作、工作多長時間以及生活和工作的平衡的“零工時代”的到來。
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勞動者不斷地加入零工隊伍。在偶有的媒體采訪中,當他們被問到為什么選擇靈活就業(yè)時,很多人脫口而出的答案也是“自由”。政府、學者、資本和主流媒體掌握著社會主要話語權、決策權和經(jīng)濟資源,他們與勞動者自身對“零工經(jīng)濟是自由”的理解這種表面上的一致性,部分地解釋了零工經(jīng)濟短時間內的迅速崛起;同時,這種玫瑰色的理解也不斷地被各種力量采納,成為勞動力市場進一步零工化和非正規(guī)化的話語動力之一。
疫情以來,諸如“特殊工時制度”的地方性法規(guī)為靈活用工大放綠燈;政府對用人單位用以規(guī)避雇主責任、降低雇傭成本的“共享員工”的實踐冠以“創(chuàng)新”之名;最近,作為工人組織的中華全國總工會下屬中工網(wǎng)發(fā)表了一系列報道和評論文章,試圖推動“共享崗位走向常態(tài)化”;而在剛剛過去的兩會上,“零工市場”更是被提升到了與傳統(tǒng)“勞動力市場”和“人才市場”同等的地位,成為我國就業(yè)政策的重要一環(huán)。有論者據(jù)此認為,未來,中國的勞動力市場將全面零工化。

問題是,如果這種玫瑰色的理解充分反映了勞動力市場的狀況和勞動者的真實處境,那么為什么這幾年伴隨著零工經(jīng)濟崛起的,還有各行各業(yè)、大大小小、遍布全國、頻頻發(fā)生的罷工呢?一些同情底層勞工的媒體人和學者很快注意到了這個悖論,他們給出的解釋是零工們被“困在系統(tǒng)里”。通過對平臺工人勞動過程中受到的來自算法和管理人員的控制的分析,他們敏銳地指出平臺所謂“自由”的虛偽性和迷惑性,揭示了零工經(jīng)濟中勞動者面臨的嚴重剝削和極其不穩(wěn)定的勞動狀況。在他們看來,零工經(jīng)濟給普通勞動者帶來的挑戰(zhàn),相較傳統(tǒng)的生產(chǎn)組織方式(如工廠)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這種解釋觸及到了問題很重要的一個方面,但也帶來了一個新的問題,即如果零工工作比工廠工作的剝削程度更深刻,為什么越來越多的人反而要加入這個龐大的隊伍呢?這個問題可以從很多方面回答。在本文中,我們想再次回到自由的問題上:當勞動者們說零工是“自由的”的時候,他們指的究竟是什么?這個自由對他們而言的重要性體現(xiàn)在哪里?為什么?進一步的,如果我們同意沒有人會在有其他選擇時忍受如此艱苦的勞動條件,那么他們又為什么選擇忍受呢?這些問題為我們真正理解零工們的處境,以及勞動力市場零工化及其可能的社會后果提供了另一個起點,也為無論是通過政策制定和立法解決零工困境,還是自下而上地推動改變提供一個思路和參考。
當然,中國的零工群體數(shù)量非常龐大,內部構成非常復雜,一篇文章不可能面面俱到。本文中,筆者引述的大部分資料來自網(wǎng)約車司機、外賣員、快遞員和產(chǎn)業(yè)工人,以此達到拋磚引玉的效果。其他靈活用工現(xiàn)象比較普遍的行業(yè)如游戲代練、主播、電商、網(wǎng)絡文學等文化產(chǎn)業(yè)等,則有待進一步挖掘。

03
當零工們說自由,是在說什么?
前面說到,“自由”是很多零工經(jīng)濟中的勞動者談論自己的工作選擇和經(jīng)驗時使用的高頻詞匯。這并不是簡單的對媒體或平臺、企業(yè)宣傳的內化。當被問到為什么覺得零工經(jīng)濟是“自由的”的時候,大家給出的答案五花八門,但總結下來基本上有如下幾點。
首先,平臺的工作讓他們不用再面對原本工作環(huán)境中管理人員專制式的管理和訓導,讓他們可以免受工作場所種種人情關系組成的利益網(wǎng)絡的困擾。如果在辦公室的情境下,這些表現(xiàn)得更為隱蔽的“辦公室政治”,對員工也會多一些面子上的尊重,那么構成零工主體的產(chǎn)業(yè)工人和其他低技能的服務業(yè)勞動者則沒有那么幸運。我們走訪的絕大多數(shù)人都有被當眾辱罵和訓斥的經(jīng)歷,這讓很多人覺得很沒有面子和尊嚴。如果你去珠三角的工廠做一天日結工,你很有可能被好心的工友提醒不要做錯事,“否則會被屌死”。“屌”在珠三角的工廠里幾乎已經(jīng)成為管理文化的代名詞:無論是沒有完成指定的任務,還是做的方式不對,或是上廁所時間長了一點次數(shù)多了一點,都有可能被當著工友們的面被屌,甚至在第二天晨會上繼續(xù)被屌。除了“屌”文化以外,傳統(tǒng)工作環(huán)境中的專制式管理還體現(xiàn)在對勞動者勞動的不合理侵占和罰款,在我們受訪者的經(jīng)歷中,常見的做法包括懲罰性加班(無加班工資)和懲罰性請假(罰款、扣工資),或是即便批準也對其進行罰款。
相比之下,平臺/零工的模式下,決定自己當天是否工作、工作多久、在什么時段工作對他們來說成為可能:不想或無法工作只需要關閉軟件即可,不需要看管理人員的臉色、被罵、被懲罰,這對經(jīng)受過嚴苛工作環(huán)境規(guī)訓的勞動者來說十分重要。比如一位女騎手表示自己加入平臺經(jīng)濟的原因之一便是為了“自由”,“不想再去開會”,或“聽從別人的安排”;為此,她甚至愿意放棄跑單價更高的團隊單,而自己跑眾包。在她本人的敘述中,這種“自由”是一種離開工廠環(huán)境自己“單干”后的“自己做主的習慣”。
需要強調的是,這絕不意味著他們在決定與自己工作相關的事情上有絕對的自由,否則也很難解釋為什么有那么多人會工作每天超過12小時。事實上,出于收入等的考量,這種自由更多的是在他們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的時候,可以停止工作而無需被限制和侮辱的自由。這種對自己工作和生活的掌控感,和由此帶來的尊嚴感在這里至關重要。
除了對自己生活的掌控感和尊嚴感外,對很多人來說,這種自由之所以彌足珍貴,僅僅是因為這讓他們可以“兼顧家庭”。用來自湖南、在深圳開滴滴的老王來說,“像我們這樣的年紀,上有老下有小,家里總有些事情是需要你去處理的,老人的身體啊,孩子上學啊,村里的事情啊等等,都需要人的”。在我們訪談的結尾,他無不感慨的說:“我兒子女兒都上高中了,我還是去年開了滴滴之后第一次去給他倆開家長會,感覺自己缺席太多”。
這種可以“兼顧”(哪怕是短暫的)勞動以外的身份,義務和責任的“自由”對于女性而言意義更甚。傳統(tǒng)的性別分工中,女性往往承擔了更多的家庭責任和無償勞動。尤其在生育期間,退出穩(wěn)定就業(yè)市場,走入零工經(jīng)濟為家庭提供部分生計,是母職重擔下一些基層女性左右權衡、甚至不得已的選擇。家庭責任之外,還有一些人會提到平臺工作讓他們終于有了社交自由,可以跟老朋友隔三差五一起吃個燒烤喝個酒,放松身心,雖然這意味著他們需要在之后的時間里補上相應的時長,以保證可以賺到足夠的錢。
還有一種反復被提到的“自由”與空間和身體感受有關。很多零工工作,尤其是平臺工作,不會將工作者局限在特定空間里,這一點對很多工廠工人極具吸引力。去過工廠的人都知道,一個典型的工廠車間里通常擺放著各種物料和機器,日常工作過程中往往是伴隨著機器發(fā)出的巨大噪音和加工生產(chǎn)過程中物料經(jīng)過高溫散發(fā)出的刺鼻氣味的,而工人在工作時則被限制在自己的工位上,好幾個小時重復相同的動作,甚至講講話、伸個懶腰都會被訓斥,無論在屋里空間還是工作安排上,身體和生理感受都非常壓抑。

與此形成強烈反差的是,如女騎手阿英所言,“送外賣可以呼吸新鮮空氣,到處走走,看到花,看到樹,看到不同的人,很自由的感覺”。對王大哥來說,開滴滴讓他可以邊開車邊跟乘客聊天,等待客人的時候可以伸伸懶腰。有一些人理解的“自由”是對未來的自主把握。我們曾遇到的一位滴滴司機曾經(jīng)在一家本地的小公司做程序員,收入不高而工作強度很大,在他的敘述中,他覺得自己的程序員工作有很高的被替代性,有很大的被裁員的風險,他說與其35歲被裁了去送快遞不如早點出來開滴滴,至少車是自己的。
對于很多曾在工廠工作的年輕人,雖然工廠穩(wěn)定,有的工廠甚至有五險一金和其他保障,但沒有前途。一些男性受訪者表示自己進廠唯一的理由是找個對象,他們認為呆在工廠干太久人腦子就不靈光了,更無法獲得潛在的發(fā)展機會。而平臺工作或是其他零工,至少能讓他們接觸到更多的人、新鮮事物和機會,與社會接觸,保持活絡;如果能吃苦,還可以給他們更高的收入,留著以后在家開個小店。像他們父母輩一樣,這是很多已經(jīng)成家立業(yè)的工友理想的生活狀態(tài)和出路。
當然,以上論述多僅適用于“眾包”的零工群體。“分包”模式下工人與分包商形成法律關系,直接受分包商管理,他們同時受到傳統(tǒng)工作組織模式下“專制式管理”的限制,能感受到的“自由”則大打折扣。
平臺經(jīng)濟之外,另一個同樣常常被認為是“靈活用工”群體的是活躍在傳統(tǒng)制造業(yè)中的臨時工或日結工,如年初鳳凰網(wǎng)、新華網(wǎng)等媒體報道的廣州康樂村的老板排隊招工中的制衣熟練工。他們之所以不做長期工而做臨時工(即成為“零工”),是因為工廠的訂單太不穩(wěn)定,而底薪又低到不足以養(yǎng)家糊口。如果選擇做長期工,則只能在旺季靠加班(每天13-16、7個小時)拿到較高工資,淡季在除去五險一金后,只能拿到2000元左右的底薪。而做臨時工,一方面時薪會高一些,可以在不同工廠做臨時工以避免淡旺季的影響,另一方面,也可以在過度疲勞時自由地選擇修整幾天,即便這樣的自由是以失去基本的保障和一直處于找工作的焦慮狀態(tài)中為代價的。
04
自由有多重要?在自由、收入與穩(wěn)定之間
所以靈活用工即便對零工們自己而言也是自由的,這個自由是真實的,也是靈活用工的吸引力所在。但對他們而言,“自由”并不是用工方、政府和主流媒體所承諾的勞動自主的烏托邦(free to),而僅僅是讓他們可以擺脫(free from)既有束縛和不合理對待。需要指出的是,這些既有的束縛和不合理對待是國家和資本的共謀下,勞動法規(guī)和勞動者利益和尊嚴被公然踐踏的表現(xiàn)和結果;另一方面,擁抱零工絕不意味著他們可以永遠免去不合理的束縛和對待,事實恰好相反。
由此,廣州康樂村所謂“工人挑老板”的現(xiàn)象,表面上看是媒體描述的老板和工人權力關系的反轉,實則是勞動者在惡劣的用工環(huán)境,和動蕩的經(jīng)濟環(huán)境中改善自身狀況的努力。也就是說,底層勞動者主動擁抱靈活用工,并不是因為它是勞動自主的天堂,也不是因為他們真的不在意社會保障和福利,而只是“兩害相權取其輕”的無奈選擇。這背后是政府在維護勞動者權益上由來已久的失靈和缺席,是資本不斷發(fā)明新的剝削方式,是后2008年代“產(chǎn)業(yè)結構升級”的大背景下勞動力市場結構的變化,是政府和企業(yè)在推動產(chǎn)業(yè)結構升級過程中在勞動者技能升級方面的缺席,是自下而上推動變革的受限和被打壓。在這樣的情況下,擁抱靈活用工這一資本發(fā)明、國家支持的最新的剝削方式,吊詭地成了他們?yōu)閿?shù)不多的、現(xiàn)實的選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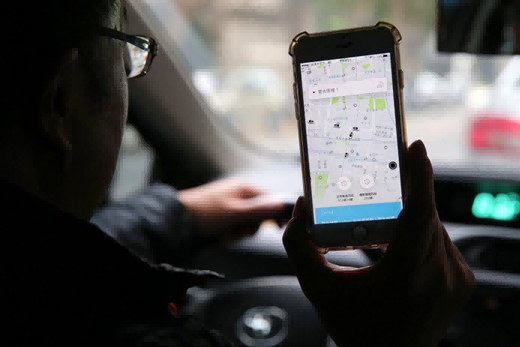
底層勞動者在擁抱靈活用工時對收入的要求也佐證了這一點。在我們的受訪者中,有很多人在工廠工作十幾年,好不容易在2012年左右獲得了工廠補繳的社保,本打算繳滿15年就回家,但是15、16年紛紛因為工廠工作太過不穩(wěn)定、因加班太少而導致收入過低而不得不離開,社保也因為沒有掛靠單位要么斷了要么只能遷回老家。他們告訴我們,他們之所以會選擇靈活就業(yè)的形式,一是因為自由,二是因為收入高,兩者對他們而言同樣重要。如果靈活就業(yè)的收入比工廠工作還要低的話,他們一定會選擇回到工廠。
今年40歲的老王在2016年年底選擇離開深圳一家工廠的之前已經(jīng)買了十年的社保了,這意味著如果他再在深圳工作5年,就可以拿深圳的社保養(yǎng)老金回江西老家養(yǎng)老了,但是整個2016年,他月薪超過3500塊的就只有三個月,其他大部分時候沒有加班,實在沒辦法,他只能選擇去開滴滴,用他自己的話說:“工廠穩(wěn)定,有社保,開滴滴賺得多,但對我們來說沒魚和熊掌不可兼得啊。家里壓力那么大,我們只能選擇錢” 。
當我們問他如果當初在工廠里每天工作8小時可以賺到足夠他養(yǎng)家的錢,他還會離開工廠、放棄社保和福利,而選擇滴滴的自由嗎?
“不會”,像很多其他我們訪談的工友一樣,他絲毫沒有猶豫地回答。
那么,究竟為什么老王沒有辦法賺取到足夠養(yǎng)家的錢而不得不投身零工經(jīng)濟呢?為什么底層勞動者如此依賴平臺和零工經(jīng)濟?被“困在系統(tǒng)”中的勞動者又需要怎樣的保護?我們將在下篇中嘗試展現(xiàn)這些復雜而重要的問題。
「 支持烏有之鄉(xiāng)!」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wǎng)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wǎng)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xiāng)網(wǎng)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