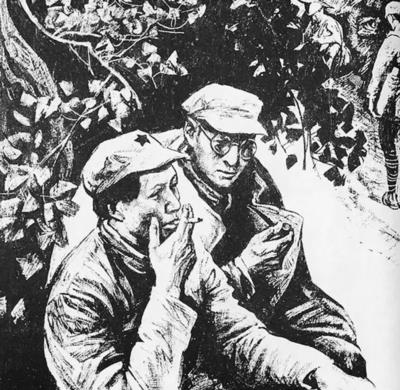1
教員和洛甫的緣分非常早。
1919年7月1日,少年中國學會在北京成立,初衷是集結有志趣的青年同志,切磋歷練,以便將來救國和建國,創始人之一便是李大釗先生。
此后少年中國學會引入各種歐美雜志書籍,并且推動了工讀互助團、新村運動等社會實踐,王光祈、左舜生、陳啟天陸續被選為執行部主任。
1919年12月,在南京讀書的洛甫加入少年中國學會,次年1月,在北京“請愿驅張”的教員經李大釗介紹,也加入少年中國學會。他們兩人入會的消息,被發表在《少年中國》第1卷第8期的版面上。
這是教員和洛甫第一次同框,也是他們第一次知道對方的名字,不過他們第一次見面,要到14年后了。
1933年1月,洛甫進入中央蘇區。
那時的洛甫已在美國和蘇聯留學8年,并且成為以王明為首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之一,所以剛回國便躋身中國革命的最高領導層,這次進入中央蘇區,也是做蘇區中央局宣傳部長,可謂是少年得志。
而教員卻在不久前的“寧都會議”上,被剝奪軍權,開始人生最慘淡黑暗的日子。
洛甫是少年得志了,但他也有自己的苦惱。
那時王明已經離開中國,在莫斯科做駐共產國際代表,國內的一切事務交給博古負責。
博古和洛甫都出自莫斯科,有這層關系,博古便把洛甫引為戰友,用蘇聯的教條指導中國革命,但偏偏洛甫不是個迷信教條的人,在實際工作中逐漸發現蘇聯的教條不符合中國實際。
于是博古和洛甫做為中國革命的二三號人物,不可避免的發生路線分歧,主要有三點:
關于抗日統戰問題,博古認為,統戰對象只包括國民黨士兵和下級軍官,洛甫則認為國民黨上級軍官也是統戰對象。
關于資本問題,博古要求嚴格限制資本主義剝削,洛甫要求利用私人資本發展蘇維埃經濟。
關于福建事變的問題,洛甫建議聯合蔡廷鍇、李濟深等將領共同反蔣抗日,博古卻把談判當成兒戲,對聯合福建一點都不上心。
如此種種分歧,博古看洛甫越來越不順眼。
1934年1月的六屆五中全會上,博古重新給洛甫安排工作,讓他做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人民委員會主席,這么做的好處是把洛甫逐漸排擠出決策層,又可以借洛甫排擠政府的教員。
一石二鳥,博古玩的溜溜的。
數月后的廣昌戰役結束,洛甫和博古大吵一架,博古大怒,命令洛甫巡視閩贛的工作,徹底剝奪了他參與最高決策的權力。
后來洛甫回憶說:“當時感覺自己已處于無權的地位,心里很不滿意。”
和博古交惡,恰恰是洛甫和教員關系升溫的契機,他們開始利用同在政府工作的機會頻繁接觸,經常在一起聊工作方法、聊革命前途,順便一起吐槽博古。
1934年8月,瑞金的沙洲壩遭到轟炸,教員和洛甫都搬到“云山古寺”居住,兩人做了鄰居,關系更好了。以至于教員得了惡性瘧疾,洛甫擔心的不行,趕緊打電話給傅連瞕,命令他來治療。
因為交流逐漸深入,洛甫還學習教員調研基層的風格,調研整理了很多第一手資料,兩人一起寫了《區鄉蘇維埃怎樣工作》一書。
這本書,可以看做是兩人合作的標志。
也就是說在長征前夕,洛甫已經從留蘇派中分化出來,和本土出身的教員開始密切的政治合作。
這次合作,說明洛甫走到教員的路線上來,教員得到留蘇派人員的支持,這對洛甫擺脫留蘇派的打擊非常重要,對教員觸底翻盤也非常重要。
2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開始長征。
剛出發的時候,各種事情一團亂麻,博古、李德、周先生組成的三人團忙著處理事情,基本沒時間管其他瑣事,于是教員、洛甫、王稼祥便申請一起行動,被編入軍委第二縱隊。
三人在長征初期的共同行動,給不久后的“遵義會議”定下基調。
因為他們都沒有具體工作,在一起的主要任務是反思分析。
洛甫講了自己和博古的種種爭論,王稼祥詳細講了第五次反圍剿的過程,教員則根據兩人的講述,把第五次反圍剿和前幾次反圍剿進行對比,給兩人分析了博古和李德的軍事路線,到底錯在什么地方,該怎么做才能贏。
經過教員的分析,洛甫點頭稱是,王稼祥拍案而起,從此以后他們都明白了,教員名不虛傳,我們這些書生啥也不是,軍事問題還得聽他的。
于是在損失慘重的湘江戰役之后,三人開始反對博古和李德的斗爭,這事在哈里森·索爾茲伯里寫的《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里,被說成是“擔架上的陰謀。”
說陰謀,有些過了。
任何錯誤的東西,不到生死關頭都可以勉強糊弄過去,一旦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大家為了革命的前途以及個人的性命,肯定不能容忍錯誤的東西繼續存在,那么便會起來反抗錯誤。
與其說教員、洛甫、王稼祥的交流是陰謀,不如說博古和李德的錯誤,把所有人都推向自己的對立面。
到了這個時候,博古和李德的失敗就是必然的,無非是同志們用開會來終結,還是蔣介石用機槍大炮來終結。
幸運的是,教員等人先蔣介石一步,用開會的方式終結了博古和李德的錯誤。
12月4日,中央紅軍進入越城嶺的苗族聚居區,教員、洛甫、王稼祥開始正面批評博古和李德的軍事錯誤。
12月11日的通道會議,李德要去湘西和賀龍會師,教員建議向貴州進軍,洛甫、王稼祥和周先生同意。
12月15日的黎平會議,教員再次否定李德去湘西的計劃,建議去貴州遵義,洛甫、王稼祥、周先生支持,并且決定到遵義以后,開會總結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教訓。
博古和李德的路線一次次被否定,教員的路線一次次被肯定,此消彼長之下,博古和李德的地位便直線下降,教員的地位直線上升。
緊接著便是遵義會議了。
1935年1月15日,中央ZZ局在遵義召開擴大會議,中國革命史上的猛人們基本上都到了。
博古先做了主報告,說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主要是敵人力量太強、紅軍各部隊配合不夠緊密、蘇區的經濟不行等等,總之就是甩鍋,用客觀因素掩蓋主觀的錯誤。
周先生做了副報告,他沒有找客觀原因,而是承擔了自己應該承擔的責任,承認第五次反圍剿是徹底的軍事指揮錯誤。
隨后洛甫也做了報告,因為是反對博古的報告,后來便稱為“反報告。”
他用種種事實舉例說明,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路上的失敗,都是博古和李德的軍事指揮錯誤,這口鍋你們別想甩,老實背著吧。
當時中央書記處有4人——博古、洛甫、周先生、項英,因為項英留守蘇區,所以在遵義開會的便只有3人,雖然洛甫沒有實際決策權,但地位是僅次于博古的。
洛甫實名反對博古,一方面說明兩人的分歧不可調和,另一方面是二號向一號開炮,其分量比邊緣化的教員更重。
而緊接著作報告的教員,用長達一小時的發言,詳細分析了博古和李德的軍事路線錯在什么地方、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應該如何做等等。
這份的報告,徹底夯實了洛甫的結論。
隨后便是王稼祥發言,表示支持洛甫和教員的報告,并建議教員出來指揮軍事。
回顧遵義會議的過程,可以說是節奏分明步步推進,在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的基礎上,一次性推翻了博古和李德的錯誤軍事路線,一步步把教員的正確軍事路線推上前臺,非常精彩。
而其中的關鍵人物便是洛甫。
博古和李德不會主動認錯,以周先生的性格不會挑頭打先鋒,如果沒有洛甫炮轟博古,遵義會議是開不起來的,沒有洛甫的支持,教員也不可能立刻回到決策層。
在長征路上,教員是扭轉中國革命走向的偉人,洛甫就是“為王前驅”的人。
雖然遵義會議后,最高軍事指揮者是周先生和朱老總,教員只是協助周先生指揮軍事,但從政治的角度來說,職位的高低并不重要,自己主導的政策路線能不能得到大多數人的支持,才是最重要的。
只要自己主導的政策路線,能得到大多數人的支持,那么在實際運作中,自己就是當之無愧的第一號人物,即便是名義地位最高的人,也得服從于政策路線,那么也就間接服從于自己。
政策路線決定了政治地位。
正因為如此,遵義會議以后的教員上升猛烈,很快便把周先生和朱老總甩在身后,從建議者成為指揮者。
此后幾十年,他對職位什么的并不在意,國家主席可以給別人做,自己也可以退居二線,都無所謂。相反,他對政策路線問題看的非常重,不管是多么親密的戰友,政策路線都是不能碰的紅線。
具體原因,也能在遵義會議上找到答案。
而洛甫也在遵義會議以后,晉升為黨內“負總的責任”的總書記,至此,洛甫管黨,教員管軍,中國革命開始了“洛毛合作”的時期。
3
洛甫因“遵義會議”成為名義上的最高領導,但如果因此說他支持教員是為了奪權,那就錯了。
事實上,“遵義會議”以后常委重新分工的時候,洛甫拒絕過出任最高領導的提議,推舉教員做,教員沒有接受。
3月份中央開會,準備派人到白區恢復工作,洛甫準備卸下職務去白區,大家都不同意,尤其是教員不同意,最后決定派陳云去白區。
6月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張國燾伸手要權,洛甫為了滿足張國燾的野心,想把職務讓給張國燾,教員極力反對,說張國燾志不在此,但要是讓他得到這個職位反而麻煩了,便提議把周先生的總政委讓給張國燾。
可以肯定的說,對于那個職位,洛甫的態度是無所謂,教員的態度是一定要他做。
也就是說,遵義會議后的教員,需要洛甫來遮風擋雨。
因為那時黨組織是共產國際的支部,最高領導必須和共產國際有直接關系,得到共產國際的信任。那么從莫斯科回國的洛甫,在這方面有得天獨厚的優勢。
而且遵義會議只是解決了軍事路線的錯誤,留蘇派的勢力依然強大,教員貿然做了最高領導,面對的壓力也非常大,不利于革命工作。
此外就和教員個人有關系了。
他的個性強硬,對自己的政策路線極其自信,從來都是他指揮別人的份,絕對不會心甘情愿的受別人指揮。
如果換上張國燾這樣的強硬人物,二人必起爭端,可如果是洛甫這種沒有政策路線的人,工作起來必須要依賴教員,那他也會工作的非常順心。
再加上洛甫原本就是排名第二的常委,所以遵義會議后的最高領導人選,非他莫屬。
遵義會議前,洛甫鼎力推薦教員,遵義會議后,教員鼎力支持洛甫。
事情基本就是這樣。
當然了,教員和洛甫合作的很好。
對抗張國燾的時候他們在一起,進軍陜北的時候他們在一起,西安事變的時候他們在一起,甚至論述抗日持久戰的時候,洛甫寫了《論抗日革命戰爭的持久性》,教員寫了《論持久戰》的雄文。
到了延安斗王明,他們還在一起。
據統計,從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到1938年9月的六屆六中全會,洛甫署名的電報有451件,其中“洛毛”或“毛洛”聯名的就有286件,占總數的64%。
可以說,兩人合作的親密無間。
工作上的順利合作,讓教員和洛甫的私人關系,也進一步升溫。
到陜北以后,洛甫和劉英結婚,沒有舉行任何儀式,也沒有請客,只是請熟悉的同志來家里坐坐。
大家都知道洛甫的性格,來了也是客客氣氣的說話,不做出格的事。
但教員喜歡開玩笑,剛進窯洞就起哄:“你們要請客啊,結婚不請客,不承認,不算數。”
這一鬧把洛甫給搞蒙了,怎么回答???
倒是劉英很潑辣,直接和教員說:“你說請客就請客啊,沒有錢又沒有東西,拿什么請客啊?”
毛澤東大手一揮:“那,不承認。”
最后還是他掏出寫好的賀詩念了一遍,才結束了自己的起哄,給洛甫的婚禮收了尾。
能讓教員這么鬧婚的人,當時可沒幾個。
4
洛甫卸任職務,向教員逐步移交工作,是從六屆六中全會開始的。
1938年8月,王稼祥從莫斯科返回延安,帶回共產國際關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指示,以及季米特洛夫關于中國黨領導人的建議:
“應該承認毛澤東同志是中國革命實際斗爭中產生出來的領袖,告訴王明,不要競爭了。”
做為共產國際的支部,中央根據這兩條指示,在9月召開六屆六中全會。
共產國際和六屆六中全會,不僅承認了教員的政治路線,也承認了教員的革命領導地位,于是會后洛甫便提議,最高領導職務應該由教員來做。
但教員經過慎重考慮,覺得現在還不是提這個問題的時候,讓洛甫繼續做下去。而洛甫既然決定讓位,便聽了教員的話,覺得教員讓他做,那就繼續做下去吧。
不過洛甫陸續向教員移交工作,在事實上退出核心決策層。
到了1943年,書記處和ZZ局設立主席,教員親自擔任這一職務,洛甫才在名義上退出核心決策層,完成“過渡”的歷史使命。
從1935年到1943年,教員和洛甫的合作全始全終。
教員多次贊嘆:“洛甫這個同志是不爭權的”,對兩人的合作過程非常滿意,而洛甫卸任以后,主要負責宣傳教育工作,偶爾去晉陜兩省搞調研,學習教員的工作方法,補上基層的課。
然而,他們能親密合作8年,不代表能親密合作一輩子。
地位翻轉之后,教員和洛甫有過兩次大沖突。
一次是整風時期。
整風是通過批判王明的思想路線,重新梳理黨組織的機構部門、思想作風以及政策路線,在這樣的背景下,文藝宣傳是重要的一環。
落到洛甫的身上,便有了兩個關鍵詞——王明、文藝宣傳。
做為曾經以王明為首的留蘇派成員,整風的大勢造起來以后,不可避免的要敲打一下洛甫,讓他反思過去的教條主義錯誤,保證以后實事求是。
整風要求宣傳教育要接地氣、和中國實際相結合,做為宣傳教育方面的領導人,洛甫以前的工作風格,也必然有不符合整風運動的地方,那么被教育一番也在情理之中。
例如教員談到延安的教育問題:
“教哲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革命的邏輯,教經濟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經濟的特點,教政治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革命的策略,教軍事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適合中國特點的戰略戰術,諸如此類,其結果謬種流傳,誤人不淺。”
這口鍋,洛甫得背。
其實教員做事很理性,他批評洛甫不是針對個人,而是通過批評洛甫,為整風服務。
如果他真的針對洛甫,七大后洛甫就應該銷聲匿跡了,但就是在1945年的七大上,洛甫當選為ZZ局委員,和陳云、彭真、高崗并列。
以他的能力和成就來說,這個地位不低了。
真正讓教員和洛甫決裂的是另一次——廬山會議。
洛甫這個人比較直,在延安時期就經常到馬列學院講:“黨員干部應該敢說話敢做事,不要怕承擔責任。”
這是高尚的道德品質,人類歷史的進步離不開這些高尚道德品質,但問題是,只講道德不講工作方法,往往會壞了事情,也害了自己。
1959年,國內出現嚴重的經濟問題,教員在廬山召開會議,提交了19個問題請同志們討論,他原本的想法是“糾左”,總結成績發現問題,保證三面紅旗不變,穩健的改善經濟環境。
但是會議的進程越來越偏離他的計劃。
先是彭大將軍寫了萬言書,緊接著黃克誠和周小舟發言支持,洛甫更是用三小時發言,在理論層面上批評了三面紅旗。
原本彭大將軍的意見也沒什么,請他們來就是討論問題么,但是經過洛甫等人的發言,討論問題,逐漸演變成對三面紅旗的批評。
更嚴重的是,彭大將軍戰功赫赫,洛甫曾經主管黨務政務,他們兩個出來批評三面紅旗,教員難免會想,這背后到底是什么意思,有沒有私下串聯?
路線是政治家的生命,尤其對于開國領袖來說,路線也可以是國家的生命。
廬山出現種種批評,那么教員就必須重新鞏固三面紅旗的路線,必須重塑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權。
他給洛甫寫的一封信,很能說明問題:
“你把馬克思主義的要言秒道通通忘記了,于是乎跑進了軍事俱樂部,真是文武合璧,相得益彰,現在有什么辦法呢?愿借你同志之箸為同志籌之,兩個字曰:痛改。”
意思就是——不懂馬克思主義所以看不懂國家的政策路線,文武聯手對國家危害極大,以后要多讀書多調研多思考,痛改前非。
彭大將軍、洛甫等四人,就此退出歷史舞臺。
5
洛甫是書生型革命家,楊尚昆也說過,洛甫太天真了。
革命年代的時候,他能看懂教員的雄才大略,到了和平建設年代,他就不能理解教員的理想抱負。而且因為天真的性格,洛甫也不太懂斗爭的殘酷性,只顧著直來直去的說話。
這樣的人,在遵義會議后是教員非常好的合作者。
當走過這個特殊階段以后,不管他們曾經合作的多么好,私人關系多么親密,他們的緣分也都結束了。
「 支持烏有之鄉!」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